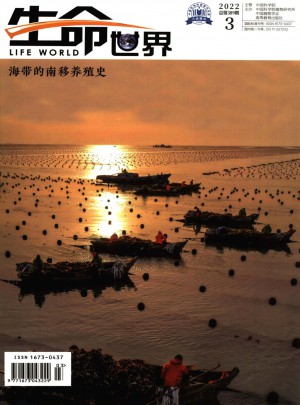生命现象的含义篇1
(一)层次思路分析题。这主要考查学生把握段落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以及文段内部结构层次的能力。这一题型江苏似乎是年年都考,是相当成熟又具有价值的题型,出题的形式有两种:局部段落论述层次概括和整体文章论述层次概括。
如2014年《乾坤草亭》第17题“请简要分析文章第四段的论述层次(6分)”,答案是“首先,提出人的境界分三层次;其次,阐述了中国画中的小亭或小舟所体现的‘台上玩月’这一境界的心灵特点;最后,指出中国画家都想达到‘高台玩月’的境界。”此段的思路很是清晰,不存在阅读障碍;层次分明,不存在理不清的问题。另外还有2016年《成人不自在》的第17题“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6分)”答案是“文章首先以孙悟空的经历为例,提出中心论点‘成人不自在’;接着写孙悟空成长,发觉自己空间险隘、生命有限从而反抗,奋斗,接受约束,戴上‘金箍儿’,阐述‘不自在’的原因;然后写‘西天取经’经历磨难,对自我进行磨砺、修心境,最后成为‘斗战圣佛’,阐述‘不自在’的意义;最后写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在’和‘成人’的两难处。”
(二)语句含义理解题。这主要考查理解文中重要概念含义和重要句子含意的能力。
重要概念指准确把握文意时必须理解的概念,要注意这些概念在文中的具体含义。如2014年《乾坤草亭》第16题,“请简要说明第三段中‘个’的含义。(6分)”答案为“‘个’从具体物象到抽象观念,形成了三个层面:竹,点,圆满具足的生命。”此题比较容易,但是此题亦有想不到的地方,即是“从具体物象到抽象观念”,再说,这也不是“个”的含义,如果这句话设分的话,考生就吃亏不小了。
重要句子指对理解文章起重要作用的句子,考点是内涵较为丰富的句子,富有表现力的句子或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如2015年《罗丹的雕刻》的第18题,“请结合文章,阐释文末‘开向生命的窗子’的内涵。(6分)”答案是“雕刻开启了以生命为表现内容的历史;雕刻成为人们思考生命的载体;雕刻呈现了罗丹对生命的思考与想象;雕刻带给艺术家们以创作的启示。”解答此题,先要弄清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一个比喻句,联系上下文完整表述应为:“‘那些青铜和大理石’是‘开向生命的窗子’”。“那些青铜和大理石”代指罗丹的雕刻作品,“窗子”比喻观察外界的通道;同时这一“窗子”是开向“生命”的,则说明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生命”。
(三)概括整合内容题。这主要考查辨别、筛选并整合重要信息的能力。重要信息包括文章的基本观点,以及最能表达文章主旨和作者写作意图的语句等。如2015年的《罗丹的雕刻》第17题“罗丹给雕刻带来的‘根本性的变革’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6分)”答案是“在雕刻观念上,罗丹是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为出发点进行创作;在雕刻内容上,罗丹的雕刻体现人的生命全景;在雕刻形式上,突破具体形象的表现手段,大胆改造人体,恣意表现生命,自由表达想象中的诡奇形象。”这也是一道传统题型,通观全文,“根本性的变革”主要在第2至第4段中。分别找出其中的观点句、概括句、评价句、总结句等,如第2段中的“他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作为创造的出发点”,第3段中的“欣赏罗丹毕生的作品,我们也就鸟瞰了人的生命的全景”,第4段中的“在他之后的雕刻家可以更大胆地改造人体,更自由地探索尝试,更痛快地设计想象世界中诡奇的形象”等。我们可以找出这些关键性语句,再将它们分门别类加以整合。难点主要是在“观念”、“内容”、“形式”这三个“类”的关键词的提炼上。
通过各个学习小班的认真研究,大家发现从命题角度看,近年来江苏省对论述类文本的考查,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套路,文本的选择,甚至每道题的赋分,都有固定的套路。“分析文章思路”与“概括作者观点”是命题的两个基本考点;“理解重要句子含义”与“概括归纳内容要点”是两个基础考点;“分析写作手法”和“语言特色”是容易忽略的潜在考点。同时第1学习小班的周童士同学还发现《考试说明》中“论述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阅读考查能力点“理解(B)”――“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用的是“含义”,而“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用的是“含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是如此解释的:[含义](词句等)所包含的意义:含义深奥。也作涵义。[含意](诗文、说话等)含有的意思。用“涵意”的句子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而用“含义”的句子,我们能理解其包含的意义就行了,不知这样解释是否合理。
二、通过实战训练,共同分析答题失误类型与原因,内化规范
在这一阶段,我们遵循大家在复习前期总结的命题规律,紧扣训练点,精做了学校备课组选出的10篇结构典范、思路清晰、命题规范的论述类文本阅读题。结合标准答案,我们分小班进行互批细批,并进行辨误归类,引导大家形成规范,举一反三。
各小班归纳出来的答题失误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点:
1、概念与文本脱离,答非所问
2、答案繁简失当,要点不全
3、逻辑性不强,表述缺乏连贯性
失误原因主要是:审题不仔细,浮躁盲目,急于求成,分析概括能力薄弱,答题习惯较差。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让各学习小班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
以下是第3学习小班提出的总体解决对策:
1、把握论述类文本的关键词句时,要注意整体把握与局部切入的关系。
2、在归纳文本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观点态度时可以由标题着手,也可以关注文本的开头与结尾,同时还要结合文体特征,从目的、启示处着手。
3、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时要注意文章结构与文章思路的关系。
4、明确论述类文本的考点要求和命题特点,探索适合自己的解题方法。
5、学会仔细审题,规范答题,准确表述。
以下是第4学习小班对“分析归纳中心意思”考点的解决对策。
1、摘句法:寻找中心句(段),有的标题即是中心,有的开头点明中心,有的结尾揭示中心。
2、合并法:ふ腋鞫沃行木洌合并后提炼概括。
3、提炼法,有的文章没有主旨句,须将全文各段大意综合起来,加以提炼。
三、进行小班化合作命题,促进学生对考点的融会贯通
笔者的小班化目前选择的是小班与小班之间定期变换组员,一般是半个学期根据考试成绩重新分班,或者在某一特定语文主题学习时安排学生自由分班,比如高一课本剧表演,高二唐诗宋词、史记选读等资料搜集,高二升高三暑假附加题复习,高三作文专题分享式复习等。
进入论述类文本复习的后期,笔者给7个学习小班分别指定了篇目,让每个小班按照江苏高考要求对此文本命制三道题目,要求考点明确,有清晰的答案解说,小班内所有成员共同参与讨论命制,各学习小班班长负责本班篇目的课上演示说明。因为在前阶段,学生经过实战训练对论述类文本的命题规律和题型已经比较清楚,所以合作命题这一环节还进行得比较顺利。
以下是第5学习小班对朱光潜《诗与直觉》(原文略)命制的题目:
1、请简要概括本文作者的论述思路。
(能力层级为C,本题考查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参考答案:首先,引出话题并引起思考:“见”如何才能升华为“诗的境界”;接着通过分析“直觉的知”和“知觉的知”几组概念的区别亮出观点,集中论述诗与直觉的关系;最后,指出思考、联想对于诗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诗的境界是直觉中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
2、诗的境界的形成与哪些方面有关?
(能力层级为C,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
参考答案:直觉,思考,灵感。诗的境界的形成必须起于直觉,但通过艰苦的思索,会产生灵感,使诗的境界得以突现而出。
3、如何理解第三段中“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这句话?
(能力层级为B和C,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理解句子的含意和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参考答案:诗的境界是指诗所写的情境,即一种完整的独立自足的境界。直觉的“知”是指通过将全副精神专注于对象本身而见出形象本身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名理的“知”是指借助思考、联想而见出事物的意义或事物之间的关系。本句是作者的观点,指出“直觉”与“诗”的关系,并以崔诗为例,表明读诗时必须要聚精会神地专注于对象本身,才能直觉出诗所写的情境(即诗的境界)。
市教研专项课题《以小班化组织形式承载“积极语用”教学的实践研究》论文。
参考文献:
[1]王兆平,胥照方.近年江苏卷高考论述类文本阅读的命题格局及应对策略[J].语文教学通讯・a刊,2016,(10).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2
一.胡塞尔:“我们要将表情和手势排除在表述之外……”
胡塞尔对手势的探讨是在他的符号现象学理论中进行的。在《逻辑研究》之“第一研究”中,他一开始便把符号(Zeichen)这个概念划分为不对称的两块:表述(Ausdruck)和指号(Anzeichen)。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含义”(Bedeutung),如表达观念或一般对象的词语或名称,而后者则没有“含义”,如钮扣、纪念碑、红绿灯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指号没有意义,而是说,指号虽然向我们指示了什么、指明了什么,或者说让我们联想起什么,但它并没有与“含义”即观念对象建立起一种单义的、明见性的关系。
在胡塞尔的体系之内,这样的本质性区分是显而易见的,但随之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在表述时常常伴有表情和手势,它们是表述还是指号?它们有含义吗?胡塞尔明确地把它们排除在表述之外,概括起来,原因有下列几点[1]:第一,我在说话时所伴随的表情和手势是无意中进行的,它们并不带有告知的意向;第二,当然,如果停止说话,单单使用表情和手势,似乎也可以使周围人理解我,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也像话语那样具有“含义”,因为“在表示者的意识中与被表示的体验”不“是同一个现象”,就是说,我想借表情和手势进行表达的东西与对周围人来说已经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不一致的,——这里的“不一致”,是指必然的模棱两可,是含义或观念对象的不透明性,它不能通过在日常交往中偶然达成的一致而被否定;第三,即使周围的人能够对我的表情和手势进行解释并藉此了解了我内心的思想和感情活动,即使它们“意味着”某些东西,它们也仍然不具有含义,就是说,它们不具有确切的语言符号意义上的含义,而只具有指号意义上的含义。
总而言之,手势和表情充其量是对心理体验的“传诉”,而心理体验,如果我们认为它就是指表述的意义或者表述的含义,那就错了。实际上,具有意指功能和含义意向的符号是词语或名称,手势和表情总是指示性的、联想的和模棱两可的。因此,胡塞尔坚定地指出,“我们要将表情和手势排除在表述之外”[2]。于是,手势和表情被胡塞尔从表述中分离出来归入到指号之中。
二.德里达:“它们的交错是原初的……”
无独有偶,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也对胡塞尔的符号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本著作的副标题上可以看出来:《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但他的理论旨趣与胡塞尔的是根本异质的,如上所述,胡塞尔以“含义”作为界标把表述与指号(包括手势和表情)区分开来,而德里达则倾全力证明这种区分是非法的,表述与指号是原初地交织在一起的。
德里达思考的起点正是胡塞尔的“第一研究”。他正确地指出[3],在胡塞尔看来,手势和表情是一种非意识、非志愿的指号,它是一种窃窃私语、一种含糊不清的嘟嘟囔囔,它不符合语言的最终目标(telos):意指(bedeuten)或“想说”(vouloir- dire)[4]。
“意指”或“想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最终目标?为什么恰恰是含义而不是其它的东西成为指号与表述之间的分界线?对于这样的课题,德里达认为[5],胡塞尔一直都是进行正面的推演和证明,但他从未对它提出过质疑。如何质疑这种分界线及其对指号与表述的划分呢?德里达采取了欲取先与的策略,他首先肯定了胡塞尔的思路,即[6]:
语言的原初职责在于完成交往的功能,但人们在交往中遇到诸多障碍,比如他们相互之间的物理体验和心理体验及其在这两种体验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的“话语的物理方面”。如何克服这种不透明性和障碍而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呢?只有当说者在说话时进行了赋予意义的行为,而听者也理解说者的意向时,交流才能发生。
然后,德里达把胡塞尔的这一思路推向极端,意向或意指之所以成为表述与指号之间的分界线,是因为意向永远对自身在场,换言之,
“每当赋予意义的行为、激活性的意向、‘想说’的活的精神性并不完全在场的时候,指示都会存在”[7]
这样,德里达便认为自己找到了胡塞尔思考的隐秘构架。那么,如何解构这一构架呢?德里达一方面从符号学出发进行解构,其主要思路如下[8]:既然胡塞尔认为符号的本质在于含义,含义就是一般对象或观念,而观念是无限可重复的,这也就是说,自身的当下在场是一种永恒在场、重复在场、同一在场、原感知的在场或体现的在场,想象、再现和当下化(Vergegenwaertigung)与它们相比是一种第二性的东西,德里达问道,在当下和永恒之间难道不是已经插入了某种非在场吗?如果重复和永恒依赖于想象和当下化,那么可不可以说,非在场的东西不仅嵌入到在场之中,甚至还是在场的前提?
另一方面,德里达从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内容出发对“自身的当下在场”这一表述中的“当下”(Gegenwart)进行解构[9]:由于胡塞尔承认当下只有与滞留(Retention)和前摄(Protention)在一起才能构造一个完整的现在,而滞留或前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下,因为滞留已经离开当下,虽然在瞬间之前还在当下中进行,而前摄也不在当下之中,尽管它在瞬间之后就能成为当下[10]。
这样,德里达通过符号学和时间性两个进路便完成了对自身在场这一构架的解构。在这之后,下面的结论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因此,表述并不作为一个层次补充到一个先表述意义的在场之中,同样,指示的外在也没有偶然地影响表述的内在。它们的交错是原初的,这种交错不是方法性的关注和耐心的还原能够摧毁的偶然性联想。”[11]
三.亨利:“一定存在另一种与世界语言不同的语言……”
在亨利(Michel Henry)这里,符号现象学或语言现象学不再像胡塞尔那样被看作是一种探究特定问题的方法,他根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七节“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中的思路首先把现象学的对象规定为现象性(phenomenali- ty):
“事实上,现象学首先并不是被规定为方法,而是通过其对象得到规定。这一对象所指的并不是一系列的现象,而是使每一个现象成其所是的东西,即被视为其本身的现象的现象性。”[12]
亨利认为,现象性是现象学的真正对象,因为只有现象学才构造起我们通达现象的道路。而胡塞尔对方法的强调,甚至使作为方法的现象学成为全部问题域的中心,这将会遇到现象性这一在先的问题。实际上,作为方法的现象学依赖于作为现象的现象性。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性呢?亨利指出,现象性一方面是指事物自身显现的特性,“正是由于它们向我们显示自身,我们才能言说它们、命名它们、在命名过程中指称它们并就此制作出许多判断,——我们的知识和话语就是由这些判断所同时组成的”[13],另一方面,现象性也指命题本身自身显现的特性,这种显现构成了语言原初的本质和逻各斯,这种逻各斯就是原始的言说,它的最重要的功能“不在于说出了什么,而在于显示了什么”[14]。亨利有时把这两种显现特性笼统地称之为现实性。实际上,我们看得出,亨利的这个概念就是现象学的“实事本身”。
“现象性”或“现实性”是亨利入思语言现象学的关键概念。亨利认为,长期以来,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和方法遮蔽了纯粹现象性的问题,使这一问题始终处于晦暗不清之中,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世界的显现与一切可想象的显现之本质之间的严重混淆”[15]。比如说胡塞尔的“原印象”,看似是一种真正的现象性或现实性,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意向性的影子:
“‘原初的’作为修饰语被胡塞尔赋予印象,它是指在经受了滞留的变更之前的印象,正是这种变更使它从其当下的或现实的状况过渡到‘在瞬间之内过去了的’状况即‘刚刚过去了的’状况。然而在滞留的变更之前,印象已经经受了意向性,已经摆脱了现实性。”[16]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胡塞尔所谓的“一切原则之原则”[17]:胡塞尔认为,认识的合法源泉在于原初给与的直观,但这种直观究竟是什么呢?从现象学上说,直观就是充实了的意向,因此,直观的现象学力量在于意向性,亨利进一步指出,原初给与的直观或如其所是的显现
“在于这样一种运动,意向性通过这种运动越过自身走向意向相关项(只要它是一个超越的对象)并因此而被抛到自身之外。这种进入到‘外面’的出离(distancing)——意向性正是在这里展开自身的——构造了其纯粹性中的现象性。”[18]
这种“出离”是现象性的“使-可见”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一过程,感知才是对某物的感知。但胡塞尔不止于此,他把语言也归于出离的过程,也就是说,归于意向性,这样便把语言与意向性概念联系在一起了:语言是对某物的意指,“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19]。亨利说,“这永远是胡塞尔的伟大发现”[20]。
然而这一伟大发现在亨利看来却充满着矛盾和不可能性:
“同一个术语——思维,cogitatio——不可能既指意向性的看(这种看从自身出发投身到超越的对象),同时又指这一思维在一切看的缺席中所进行的第一次自身开启(l’auto-révélation)。意识不可能一方面‘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具有对某物的意识’,——这个某物是我所认识的某物,或者是我所思考的、我所感觉到的或我所想望的某物,总之它总是具有‘其所思对象(cogitatum)’(《危机》,第20节,页96),另一方面同时又是纯粹的质料(hylé)、非意向性的材料(matière)、纯粹的和‘原初’的印象。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应该说,在这里如果还存在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存在的是一个展示的过程,这是对印象的展示,当它不再是意向性的事实时。”[21](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这里的矛盾和不可能性正是思维和意识也即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意向性的矛盾和不可能性。海德格尔对此抱有很大的警惕,特别是对“思维”和“意识”这两个概念心存戒心,但他在“出离”这一点上还是承继了胡塞尔的思想。亨利指出[22],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两个地方强化了显现与外在化或出离的关系。一处是在第七节中:海德格尔说希腊语“phainomenon”(现象)的前缀“pha”或“phos”是“光”,这就意味着,显现就是进入到世界的光中,换言之,显现就是外物(the outside)从“出离”(the Outside)出发而降临;另一处在第二篇中:海德格尔在这里谈到了时间性和世界与显现之间的关系: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23][24],而世界“在时间性中到时。世界随着诸绽出样式的‘出离自己’而‘在此’”[25][26]。海德格尔在这两处所指出的是同样的思路:显现在时间性中“出离自己”而进入到世界的光中,现象性就是作为纯粹外在性的绽出的时间性。
这种显现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在胡塞尔的伟大发现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把语言的言说解释为希腊文的显现,即世界的降临,并进一步把语言的原初本性与存在的绽出真理勾连到一起。海德格尔在《走向语言之途》中正确地指出,词不是命名的工具,它首先道说在场的来临。亨利指出[27],在《走向语言之途》中,Logos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去蔽的显现与被去蔽之物是不同的;第二,因此,去蔽的显现,即世界的绽-出状态(ec-stasis)把它的光芒一视同仁地撒在每一个存在者身上、撒在“正义以及不正义之物身上”;第三,世界显现的这种一视同仁(indifference)还导致一种更加具有决定性的状况:这种显现(appearing)没有能力设定(posit)它所揭示出来的现实。根据海德格尔的明确断言,这种显现化并不创造现实,它仅限于敞开而已。
胡塞尔的发现是伟大的,海德格尔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对胡塞尔的拒斥、继承和推进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这条道路在亨利看来是根本错误的[28],因为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看不到一个在现象学原则的心脏处搏动着的悖论。在这一原则看来,正是现象性给出了存在,正是通过显现且仅仅由于其显现,任一事物才能成为存在。可是在这里得到认可的却是,显现之物恰恰没有把它的存在归功于显现的力量,因为显现的力量被局限于对某个存在者的敞开,而这一存在者先行于它并因此而在真正存在论的意义上不会依赖于它。”[29]
简而言之,我们一方面看到,显现是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存在者先行于显现。显现怎么可能既先于又后于存在者呢?由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把显现与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语言观也无法摆脱上述悖论。亨利把这种与世界的显现密切勾连的语言称为“世界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它也具有与世界显现相类似的三个特征[30]:第一,构成这种语言的每一个词与其特定的现实(存在者)都是不同的;第二,语言对它的指称是一视同仁的(indifferent),因此,一个词能用于两个不同的现实,两个词也能用于同一个现实;第三,人类言说的世界语言、规定一切可想见的语言之原型的世界语言被包含在这样一种无能性(impotence)之中,这种无能性是对显现之无能性的直接复制。
亨利说[31],我们在在海德格尔对特拉克尔(Trakl)“冬夜”一诗的解读中可以清楚地看见这种无能性。诗中的“雪、铃声和夜”通过诗人的言说被带入存在,或者说,当我们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这些对象自身显示出来。但是,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物体中,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房间中也找不到它们。是的,它们的确通过诗人的话语而显现,但却是以缺席的方式而显现的,就像康德在批判本体论证明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口袋里有100泰勒”这句话并不表明我真有这么多的银币。
语言的这种无能性来自何处?既然现象学认为语言与其所仰仗的显现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关系,那么,语言的这种无能性必然来自显现的模式即“世界的显现”这一模式。这一模式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被发展到极致,他们把显现还原到对世界的某一原真的“出离”(outside),这样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亨利语),它直接导致显现的无能性并进而带来了语言的无能性。
为了解决现象学的矛盾和悖论以及语言的无能性,必须首先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颠倒了的思路再颠倒过来:
“于是,对现象学的颠倒可以描述如下:不是思维使我们抵达生命,而是生命使思维有可能抵达自身并进行自身认识以及最终成为它每一次之所是:‘思维活动(cogitatio)’的自身展示”[32](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我们不是先有思维、意识、意向性或出离,然后才有生命及其对自身的体验,它们之间的顺序恰恰应该颠倒过来!亨利据此提出了另一种显现的模式:“生命的开启”(the revelation of life)。与“世界的显现”不同,
“生命开启的首要特征在于,它作为自身开启(self-revelation)而完成……在自身开启中,可以说,同一之物不会被两次命名:第一次作为开启或触发之物(the affecting),第二次作为被开启之物;也不会带有这样的结果:触发之物和被触发之物(the affected)被表象为两种不同的实在,每一个由其功能而被定义。只有在世界的‘出离自身’中,生命的自身开启才通过摧毁自身而分裂自身。”[33]
世界的显现,在胡塞尔那里是触发和被触发的相关过程以及意向相关项的最终呈现,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世界的出离自身而到时;而生命的开启是一种绝对的自身同一,但亨利马上指出,这种同一不可被还原为同义反复,就是说,它不是形式的、空洞的“A=A”。恰恰相反,亨利说,“生命是一个内在的和永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命苏醒了;生命依靠自己把自己拉入进来并与自己嬉戏,同时产生出自己的本质——只要这一本质存在于并完成于这种自身享受(self-enjoyment)之中”[34]。
“自身享受”,在亨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自身体验,是生命与其自身的相互运动。这种运动不是单调、贫乏和机械重复的,它是活生生的生命过程,单数的自身(Self)就诞生于这一过程。随着单数自身的生成,生命便在自身体验的同时向自身开启。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自身开启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亨利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同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的:语言依赖于现象性或显现模式。他们的分歧在于显现的模式不同,即“世界的显现”模式与“生命的开启”模式的对立。这样,在亨利那里,语言当然奠基于生命的开启,正如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语言奠基于世界的显现一样。可是,以生命开启为依据的语言与以世界显现为依据的语言是一回事吗?亨利在此作出了大胆的推定:
“如果语言的本性确实依赖于它总是设为前提的显现的本性,那么,语言与显现之间的本质关联将会被揭示为一个决定性的主题。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另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正如我们所确定的那样,如果现象性根据一种与世界的现象化根本不同的现象化模式而原初地使自身成为现象,即,生命自身在其纯粹的现象学本质中被把握为自身-开启,那么也一定存在另一种与世界语言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与从意向相关项含义出发所建构的语言是不同的,后者外在于其现实的指称,换言之,这种语言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界定的语言);这种另类的语言将会依赖于为生命所固有的现象化模式——只要生命的显现在所有的特征上都与世界的显现相对立。”[35]
这种另类的语言是什么?它怎样言说?它说给谁听?它怎样区别于世界的语言? 四.亨利:“伸出的手和张开的双臂……”
这种另类的语言就是生命言说自身的语言,而生命言说自身的方式正是生命开显的方式。与世界的显现和世界的语言相反,生命的语言在自身中不包含任何意向性,它的言说不意向任何东西。一个没有意向性的言说不是凭空言说吗?它利用的是什么材料?它说出了什么内容?
生命的言说不是空穴来风,它出自生命的“感动”(pathos),这种感动所涉及的是“肉身(flesh)被充分地湮没到其痛苦(suffering)和欢乐的自身触发(self-affection)之中”[36]的状态,这种原初的感动(pathos)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痛苦,亨利说[37],它是一种更古老的痛苦(the older suffering),它先于爱、痛苦(suffering)和欢乐(enjoyment)。从现象学角度看,这种感动正是生命言说所利用的材料,
“在这种感动中,开启的‘如何’成为内容;它的‘如何’(Wie)就是它的‘什么’(Was)。如果生命所原初开启的不过是它自己的现实性,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它的开启模式是感动。”[38]
生命的言说言说着自身并向着自身而言说,它说出的是生命自身所原初开启的现实性(或现象性),这一点恰恰与世界的语言形成鲜明对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无能(impotence)的语言,它无力呈现它所言说的现实,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它只能让世界在缺席中显现;而生命的语言却是一种超能(hyper-potence)的语言,它不仅能让生命在在场中开显,而且还能生成(generate)它所言说的现实。只有生命的语言才是真正的“逻各斯”(Logos)。
生命的言说并不通过有声的词汇而说话,它是我们处于感动之中的肉身对自身的内在体验,正是在这种感动中,肉身实现了对其自身的最初的各种领悟(epiphanies),自身由此而得以开启和生成。以此为基础,世界的语言才得以开口说话。
生命的言说不是思辨的推理,也不是神秘的话语,“我们能够在每一个生物、每一种生命样式中发现这种语言”[39],只要我们转换我们的目光。下面是亨利给我们提供的例证:
例证1:痛苦的哭泣[40]
当生命处于痛苦这种感动(pathos)之中时,它并没有说,“我很痛苦,某人有罪”,它还没有与“我”发生关联,意向性在这里还没有构成含义,含义也还没有构成对“痛苦”的言说,言说本身还不是某种理想(ideal)之物。可是,一旦我们询问“痛苦如何言说?”时,我们便不可避免地感觉到,它在自己的痛苦肉身之外还对我们说了某种东西,因为任何痛苦都不会作为无人的痛苦而降临。实际上,痛苦在自身中(in itself)带有承受痛苦的自身(the Self)。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与世界语言根本不同的维度上重新思考‘如何’这一问题。
哭泣正是痛苦的言说方式,它是内在生命的表达,它完全不同于“我处于痛苦中”这样一个语言学命题。初看起来,哭泣具有现象学上的双重特征:哭泣一方面是外部空间中的回音(像老师对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发出的怒吼一样),另一方面是痛苦的原初开启,但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我们的身体对这种回音是开放的,但这种回音只不过是事后被加到这个开启之中。回音和开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说模式,虽然这两种语言都在同一种单纯的哭泣中言说,但只有后一种语言才是哭泣的真正的言说方式。
哭泣是身体语言,它是痛苦对自身的诉说,它诉说着肉身的痛苦,生命能够无比清晰地听见这种哭泣的声音,但不是通过回音。它哭泣着,同时它体验到这种无声的声音。这种无声之音就是生命的语言,“每一个生物在生命的第一次颤栗中都已经听见了这种生命的语言”,就像我,我总是能听见我出生时的声音,这种声音就是生命的声音,在这种无法打破的沉默中,生命的语言不断地向我诉说着我自己的生命。
例证2:伸出的手和张开的双臂[41]
一只伸出的手,一双张开的臂,意味着什么?它难道不像语词一样具有直接的和不言自明的含义?它难道不也是一种语言,甚至是一切语言中的语言?亨利说,“如果我们认为‘语言’这个术语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而已,那我们就错了”[42]。当然,恰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手势语言并不具有意向性,但亨利争辩道,这种语言在排除了所有智性的含义之后不是仍然具有直接明了的意义吗?不是仍能为交流提供可能性吗?亨利明确地指出,“当我们使用这种语言(这一语言排除了所有智性的含义)与动物进行交流时,我们的确能看出这一点” [43]。
随着手势语言的发现,一个在哲学上长期遭到忽略的巨大的语言领域展现在我们面前,如舞蹈语言、哑剧语言以及体育语言等等。这是一个身体语言的领域,这些身体语言不仅属于世界的显现(在世界中,身体是一个对象),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它们奠基于我们活生生的身体性(corporeality)之中,奠基于我们敏感易动或有感而动的(pathetic)肉身(flesh)之中。
从这两个例证出发,亨利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广袤无垠的生命语言的天地:“在做饭、劳动、休闲、性行为中,在与生者或死者的关系中,生命以某种方式言说着自己”[44],不仅如此,亨利还有一个宏大的抱负:从生命的开启和生命的言说模式出发对每一种文化形式,如绘画、诗歌、音乐等等,进行重新阐释(这种阐释甚至扩展到圣经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消除我们长期以来囿于普通语言观所产生的幻觉,“即在这种幻觉中,普通语言所表述的含义(不论它们是概念上的还是实践上的)似乎唯一地来源于世界并且在世界中找到充分的解释”[45]。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只伸出的手,一双张开的臂,其角色、地位、意义和作用在现象学运动中经历了奇特的变迁历程。在胡塞尔那里因其含义的模糊性而被排斥在表述之外,沦为第二性的、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德里达企图通过其独创的解构理论从现象学内部出发摧毁表述在语言符号中的主导地位,让不在场的指号(当然也包括手势)充替(suppléer)到在场的表述之中,从而形成表述与指号的延异运动。手势语言在这里摆脱了第二性的地位,它与表述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当然,德里达最后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痕迹而已;在亨利这里,他通过扭转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思路,使身体语言(当然包括手势)一跃而成为第一性之物,成为胡塞尔的“表述”、海德格尔的“道说”以及德里达的“痕迹”的基础[46]。这一历程值得我们深思。 注:
[1] [2]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33-34页、第33页
[3] [5] [7] [8] [9] [11]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译文据原文有改动。第44页、第46页、第46-47页、第四章、第五章、第110页。
[4] 关于“想说”(vouloir-dire)的意义,请参见拙文:“论德里达与胡塞尔的符号学之争”,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6] [19]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1999年,第35页、第26页。
[10]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论证,关于这一问题的详尽论述,参见,方向红:“论德里达对胡塞尔‘孤独的心灵生活’的解构”,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五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以下。
[12] [13] [14] [15] [18] [20] [22] [23] [25] [27] [29] [30] [31]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Michel Henry, “Material phenomenology and language (or, pathos and language)”,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1999, Vol. 32, transl. by Leonard Lawlor, p343、p.344、p.345、p.346、p.346、p.346 、p.347、p.347、p.347、pp. 348-349、pp. 349、pp. 349-350、p.350、p.351、p. 352、p. 35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p. 353、p. 356、p. 356(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p. 353、pp. 355-358、pp. 361-363、p. 361、p. 361、p. 363、p. 361.
[16] [21] [32]M. Henry, Incarnation: une philosophie de la chair,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2000, pp.81-82、pp.126-127 、p.129.
[17] 这一原则的完整表述为:“每一种原初给与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与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与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与的限度之内被理解”(着重号为胡塞尔所加)。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性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84。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3
一、罗素提出摹状词理论的动机
罗素为什么提出摹状词理论?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逻辑方面的,一个是哲学方面的。逻辑方面的动机是想用摹状词理论来消除某些含有摹状词的语句所可能导致的不合逻辑的现象。哲学方面的动机则是想把摹状词理论作为奥卡姆剃刀,以便剃掉人们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某些对象的不合理的本体论承诺。具体地说,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提出源于对所谓哲学三大难题的思考:同一性替代问题、排中律失效问题和存在悖论问题。
(一)同一替代问题
如果A =B,那么在命题中能否用A代替B而不改变命题的值?例如,“乔治四世想知道司各脱是否为《威弗利》的作者;而事实上司各脱是《威弗利》的作者。因而,我们可以以司各脱代入《威弗利》的作者,从而证明乔治四世想要知道的是,“司各脱是否是司各脱”。显然,专名和摹状词并非是等同的,尽管二者可能具有同一外延;含义与指称是一个统一体,分开使用会明显地不合直观。
(二)排中律失效问题
按照排中律,“A是B”与“A不是B”二者必有一真。可是,“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与“当今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头”都是假的命题,因为当今的法国国王并不存在。
(三)存在悖论问题
如果说“金山不存在”,就似乎意味着“金山”是一个东西,虽然它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在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称“摹述理论就是打算应付这种困难以及其他困难的”。
二、罗素摹状词的主要内容
罗素认为他的摹状词理论能够解决以上三个问题。实际上它也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
罗素将摹状词分为非限定摹状词(indefinite description)和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非限定摹状词所指称的对象不是确指一个明确的对象,例如“我遇见一个人” , “一个人”是任指的;限定摹状词所指称的对象确指一个确定的对象。罗素实际上主要讨论了限定摹状词,即形如“the so-and-so”的词组或短语,通常译为“一个如此这般者”。
摹状词理论的实质在于通过分析摹状词所要表达的实际含义,从而消除摹状词,得到一个准确的无歧义的联言命题作为包含这个摹状词的命题的成分。罗素认为一个单纯的摹状词没有独立的意义(真假值),只有在命题中才呈现出意义:“指称词组本身决不具有任何意义,但在语词表达式中出现指称词组的每个命题都有意义。”因而实际上这个意义是在对命题中的摹状词进行分析后得到的。罗素说:“一个摹状词由几个字组成,这些字的意义已经确定,摹状词所有的意义都是从这些意义而来。”因此摹状词实际上是“由我们已经亲知其意义的词构成的词组。”我们在具体语境中对组成摹状词的各部分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知道它的准确含义。例如,“查理二世的父亲被处以死刑”,正确的理解应当包含三个方面:(1)查理二世的父亲存在,即至少有一个个体存在。用变元x来表示这个个体,那么可以将其表示为“有一个x,他是查理二世的父亲”。但因为“查理二世的父亲”还表示“x生了查理二世”这种关系,因此准确地表示应该是“有一个x,这x生了查理二世”。用φx来表示“x生了查理二世”,则可以形式化为( x) φx。(2)查理二世只有一个父亲,即这个个体惟一。就是说,如果另有任何一个y也生了查理二世的话,那么y等于x是恒真的,其形式化为 (x) (φy y = x)。(3)这个个体被处以死刑,即这个摹状词满足所陈述的性质。可以用ψx来表示这个性质。
可以看到,原来包含摹状词的命题经过分析就成为“存在一个x, x生了查理二世,且x 被处以死刑;并且如果另有任何一个y也生了查理二世的话,那么y等于x总是成立。”实际上,任何具有“一个如此这般者具有某性质”的形式的命题,都可以将其形式化为“( x)( φx ( y)(φy y = x) ψx)”。这样,一个摹状词在经过具体分析之后就被分解成几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成分存在:“当出现我们没有直接亲知的、然而仅仅由指称词组定义而知的事物时,通过指称词组在其中引入这一事物的命题实际上不包含此事物作为它的一个部分,但包含由这个指称词组的几个词所表达的诸成分。”只有这个摹状词所包含各部分的意义都真时,这个包含摹状词的命题才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
经过如上分析,摹状词的含义就能够清晰地无歧义地显现出来了。摹状词理论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能够使我们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根据这种分析,前面提到的三个难题可以得到这样的解决:
(一)关于同一替代问题
摹状词在命题中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分存在,而是一个可以分成几个成分的指称词组。“指称词组本身并没有意义可言,因为有它出现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命题,如果完全加以表达,并不包含这个词组,它已经被分解掉了。”这个被分解掉的词组指向一个个体,在一个具体命题中这个摹状词所指称的个体才与专名相等同。所以,摹状词与专名是有区别的,也就不能进行同一替代。
(二)关于排中律失效问题
对于排中律失效的问题,罗素在摹状词理论中区别了摹状词的初现与再现。一个含有指称词组的命题总可以表述成“一个如此这般者具有某性质”,而“一个如此这般者”可以表示为“C 具有性质φ”,于是这个命题可以表示为“一个且仅有一个具有性质φ的项(C),它具有性质ψ”,这时摹状词是初现。如果这个“具有性质φ的项”或者不存在,或者不惟一,那么这个命题总是假的。如果这个命题作为另一命题的其中一个成分出现,例如出现在前一命题的否定命题“并非一个且仅有一个具有性质φ的项(C),它具有性质ψ”中,此时摹状词是再现。易知此时该命题真,排中律仍然有效。
(三)关于存在悖论问题
罗素对于自己运用摹状词理论解决存在悖论颇为自得。他宣称“这澄清了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开始的、两千年来关于‘存在’的思想混乱。”根据摹状词理论,“金山不存在”这一命题应该理解为:“并非有一个实体C,使得有一个x是C时,‘x是金的且是山’是真的,否则它就不是真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所指缺乏而又有意义的摹状词导致的思想混乱。但是,后来逻辑学家指出一个缺陷:由于对包含摹状词的命题的否定可以有两种形式化方式“-(( x)(φx ( y)(φy y=x) ψx)”和“( x)( φx ( y)(φy y = x) - ψx”,显然罗素忽略了第二个公式。
三、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缺点与不足
(一)罗素的数理逻辑分析方法的不足
罗素自认为数理逻辑的分析能够解决任何哲学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为例,按照罗素的分析,这个命题不能被证实,因为我们不能担保我们不忽略任何一个人,此外他认为,这不是对于人的命题,而是对于宇宙间一切东西的命题。他解释道,这一命题说的是:“对于任何x来说,如果x是人,那么x是有死的。”所谓任何x,说的似乎是宇宙中的一切。最后他认为,假如所谓的人根本不存在,这命题就是真的。
现在让我们来逐条加以批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这一命题是在历史上早就证实了的,现在还在不断地证实着,这里谈的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质,这和忽略了某些人与否根本不相干。其次,这个问题只对于人有所肯定,当断定这个命题时,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宇宙间的一切东西。原命题并不等于一个假言命题,并且这个假言命题也不考虑到宇宙间的一切。再次,将普通形式逻辑中的全称肯定命题解释成只要主语所表达的事物不存在,这一命题就是真的,这也是错误的。的确,鬼不存在,没有红头发的鬼也不存在,难道这就使得“所有的鬼都是有红头发的”为真了吗?显然这很荒谬。因此说罗素的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采用这种分析方法解释攀状词理论自然就不见得完全正确了。
(二)罗素摹状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
罗素的攀状词理论的基础是:意义即所指,孤立的攀状词没有意义,而包含攀状词在内的命题却是有意义的。但我们应有常识方面“攀状词有意义”这样一个事实不能抹杀的问题。
我们不承认孤立的摹状词没有意义,或单独地无所指示。以“《威弗利》的作者”为例,《威弗利》是一本书,《威弗利》的作者就是写《威弗利》这本书的人,我们对《威弗利》有概念,对作者有概念,为什么对《威弗利》的作者没有概念呢?应该承认,我们有这攀状词所表示的概念,有的攀状词可能需要在命题中才能得到明确的所指,有的攀状词不需要命题的帮助就有明确的意义或指示。《威弗利》的作者就是后一类的攀状词。同样“现在的法国国王”也是有意义的,一个概念既有意义,当然也有所指示,至于所指示的那东西不存在,则是另外一件事。摹状词有或没有所指示,并不依靠所指示的东西存在与否。如果我们指着一个说:“这张桌子是四方的”又说“这张桌子不是四方的”,我们就会有罗素的第三类难题,可见排中律失效并不是慕状词有无意义的问题。我们不否认包括摹状词的命题是有意义的,但是说摹状词单独地没有意义和指示,这是不正确的,也是我们不予以承认的。
(三)语法上的主词不能一律地转化为逻辑上的谓词
“摹状词理论的一个重要历史结果是,句子的语法形式和罗素所谓的逻辑形式之间的区别开始通行于世。可是这种区别由于罗素及其追随者未能完全清楚地阐明逻辑形式是什么而逊色不少。”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通过将一命题的语法上的主词转化为逻辑上的谓词而完成对三大难题的解决的,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将语法上的主词转化为逻辑上的谓词的方法是否正确。
以“这张桌子是四方的”为例,按照罗素的方法,该命题可分析成“x是桌子,并且x是四方的。”原来语法上的主词便转化为逻辑上的谓词了,这在习惯上是有些格格不入。固然从数理逻辑的角度来说,这样分析不无道理。但能否说将语法上的主词一律地转化为逻辑上的谓词就是完全合理的呢?原命题是否等于分析出来的联言命题。分析出来的联言命题“x是桌子”和“x是四方的”,一般来说是没有次序的,即两个支命题的先后次序与整个联言命题的真假值不相干。也就是说,“x是桌子并且x是四方的”和“x是四方的并且x是桌子”这两个联言命题是真假值相等的。由此我们可得出“这张桌子是四方的”等手“这个四方的东西是桌子”,虽然它们的真假值相等,而在日常生活中,在具体条件下二者并不相等,前一命题谈的是桌子,后一命题谈的是四方形。由此可见,这两个命题是有次序上的分别的,而且分别是很大的。原命题的重点是肯定那东西的四方性,而分析出来的联言命题的两支是平等的,没有重点或非重点之分。所以说语法上的主词不是一律地可以转化为逻辑上的谓词的。
(四)用命题的正确性代替客观事物的存在性
“摹状词理论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把存在当作是命题函项的一个属性。”对“某物存在”或“某物是存在的”这样的命题,这里的存在是性质还是关系?显然,把存在看作性质或关系都有困难。就客观事物说,存在是有或没有性质或关系的先行条件,这一条件不满足,性质或关系就无从谈起。谈不存在的事物的性质,所谈的是悬空的性质;谈不存在的事物的关系,所谈的是没有关系者的关系。因此,存在不是性质或关系,而罗素恰恰是化存在为性质。按照罗素的说法,存在是对命题函项说的,罗素的意思是:说桌子存在,实在是说“有x,而x是桌子”是真的。“x是桌子”中的x,是一个变项,如果这个变项的值是C,而C又实在是桌子,x是桌子这一命题函项就成为上述那个真的命题了。这样,个别事物的存在问题好像撇开了,存在好像就是命题函项的问题了,或者命题的真假问题了。这样罗素就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抽象问题,把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存在问题偷换成单纯的一般的存在问题,他要把认识论中的存在问题偷换成为他所搞的逻辑或数学中的存在问题。于是他就将语法上的主词转化为逻辑上的谓词,因为语法上的主词是表示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存在,把这样的主词转化为谓词,原来的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存在问题就偷换成命题的真假问题了。由此可见,罗素的存在论是以命题的正确性来代替客观事物的存在性,这是不正确的。
四、罗素摹状词理论的哲学意义
总的说来,尽管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有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但它正确地坚持了传统名字理论的观点,即专名既有含义又有指称,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名只有所指没有含义的观点,显然专名只有所指没有含义的观点是站不住的。另外,幕状词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它不仅有含义而且也有所指,据此我们可以对摹状词作比较全面、正确的理解。
摹状词理论的最重要的哲学意义在于:它禀承“奥卡姆剃刀”原则,以摹状词理论为武器,从根本上杜绝了本体论承诺,从而在迈农不得不承认那些虚构的实体的问题上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方向。“由于有了摹状词理论做武器,使它不需要拿对象做指称以确保每一个表面上的名字的有意义性。这样,罗素不仅把迈农的对象,而且把类、性质、甚至把物理对象都当作‘虚构’废除了。”
参考文献
[1] Russell. Bertrand Descriptions(1919)[A]. in Martinich, A.P.(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 [英]罗素著,马兰德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 杨雪芹.重读经典:罗素的摹状词理论[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1(76).
[4] [英]罗素.逻辑与知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6] [英]罗素.数理逻辑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4
一、逻辑概念的研究现状
逻辑概念存在吗?如果有,它反映什么对象?反映对象什么情况?与非逻辑概念有哪些区别?是如何形成的?是逻辑惟一的基因吗?等等,这些问题逻辑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长期从事逻辑研究和教学,深感到它的存在和重要。然而,逻辑概念的存在虽然是事实,而且被反复使用,但它并未受到逻辑界应有的重视,人们对逻辑概念的认识一直处于零散、不自觉的状态,没有达到概念明确、认识完整、知识融会贯通的程度,从根本上影响着逻辑研究的深入和逻辑教学的质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难导致。逻辑概念抽象、隐形,不好捉摸,研究相对薄弱,进展不大,因而产生诸多问题。
逻辑概念的问题,首先表现为态度上,因难生畏,否认其存在。这里先指出,本文随后也将证明,命题联结词、量词等,都是重要的逻辑概念。然而,陈波先生对它们却不认可。他主张不严格区别概念与词项,认为命题联结词、量词等“不是词项,而是运算符号”。他提出了两点理由:一是词项都可以直接作为定义对象,这些运算符号却不能;二是词项都有内涵和外延,而这些运算符号的内涵和外延是很难说清楚的。既然它们连一般的词项或概念都不算,当然更不是特殊的逻辑概念了。笔者认为,这些运算符号其实就是概念,是可以而且必须作为定义对象的。作为运算符号,同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符号一样,都有所指,反映的是已知到未知的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存在,而大凡存在都有相应的概念。这些运算符号尽管内容比较抽象,揭示其内涵、外延有一定难度,但内涵和外延很难说清楚不等于不能说清楚。对待逻辑概念的正确态度,应是不回避,迎难而上,设法揭示其内涵,寻找其外延,进而建立起完整统一的逻辑概念体系,使其成为逻辑学坚实的基础理论,为庞大的逻辑理论体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持。
对逻辑概念认识欠缺,还表现为内涵上不能精确定义、认识不到位,或者外延范围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在各种普通逻辑教材中,通常有一章介绍一般的概念,却没有逻辑概念的地位。大都是结合命题仅涉及一些特殊的逻辑概念,而且定性不准,用非逻辑意义代替逻辑意义。众所周知,逻辑要求人们使用的概念要明确,准确把握对象,为此提出了概念明确的标准。可是,很遗憾,普通逻辑竟连自身特有的概念都没有搞明确。
现代逻辑中,逻辑概念得到了较多的研究,但其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张尚水先生曾直接给出了几类基本的逻辑概念,包括命题联结词、量词、等词、模态词,并且指出逻辑概念对逻辑真命题有决定作用。应该说,在中国,张先生的介绍和强调对人们深入研究逻辑概念起到了引导作用,但他并没有给出一般的逻辑概念,也没有说明所给出的逻辑概念是如何形成的;除了已给出的逻辑概念是否还有其他逻辑概念,逻辑概念对逻辑真命题是怎样起决定作用的,结果使人对逻辑概念的认识终究还是不得要领。
还是在现代逻辑领域,王宪均先生在逻辑概念的意义上定义了真值联结词,并给出了5个真值联结词。如果王先生能恰到好处地把逻辑概念与真值联结词等同起来,那么他关于真值联结词内涵的认识是迄今为止对逻辑概念最深刻的认识。可惜,王先生实际上认为:“命题逻辑的规律反映复合命题的逻辑特征。”“复合命题的特征决定于联结词所反映的客观联系,所以,命题逻辑又被称为联结词的逻辑。”“命题逻辑只包括一部分逻辑形式和规律”。王先生认为,真值联结词只决定命题逻辑的逻辑形式和规律,不能决定所有逻辑形式和规律。而事实上,逻辑概念是一般的,是决定一切逻辑形式和规律的。可见,王先生明显把真值联结词只作为部分逻辑概念,把本应是整体的视作局部,没有把它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尽管有所谓真值联结词,还是没有完整到位的逻辑概念。值得指出的是,王先生还通过论述所谓真值函项,试图总结真值联结词的范围。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其思路和方法却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笔者将在后续文章对问题概念真值函项重新予以准确解释。
在逻辑界,明确使用逻辑概念称谓、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末木刚博先生。他把概念分为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指出后者“也可以称之为‘逻辑概念’或‘联结词’等等”,确立了逻辑概念应有的地位、名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逻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被陈波先生不幸而言中,当真没有说清楚。围绕逻辑概念产生的种种问题,笔者在长期思考之后,形成了《建立所有逻辑规律的基因族谱》系列论文。本文是上篇,明确承认逻辑概念存在,回答了什么是逻辑概念,从对象、内容、存在方式、語言表现以及作用等多方面揭示了其丰富的内涵特征。
二、逻辑概念独特的反映对象及内容——命题及真值
逻辑概念是专门反映命题的。命题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态,是人们在认识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运用概念反映对象情况的理性认识。断定情况、有真有假和用語句表达,是命题的鲜明特征。命题陈述的情况丰富、具体,其中陈述对象一般、根本、必然情况的命题,对变革对象的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例如,依据真实的条件命题、因果命题,自觉创造条件或限制条件,就能促使实践目标实现,从而达到驾驭对象、兴利除弊、造福人类的理想境界。正因为命题对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因而系统获得命题、正确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就成为全部科学的使命。事物都有发生的方式、原因、过程和规律,命题也不例外。命题的形成除了在实践中直接运用概念反映对象情况,还有间接的发生方式,即依据命题真值关系进行推理、证明,由已知到未知。要正确地进行推理、证明,一个必要条件是遵守命题之间的真值规律。因而,命题一经形成,自身又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的对象,目的就是发现命题本身具有的规律,以指导推理、证明,获得更多的新知识。逻辑概念就是认识命题过程中的产物。
逻辑概念以命题为反映对象,那么,它反映命题什么情况呢?命题事实上存在多方面的情况,要精确区分逻辑概念,就需要分析、挖掘命题的意义,以便从中进行取舍。概括地说,任何日常命题都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存在意义,即陈述了对象及其情况,包括对象的性质、关系、存在关系等。二是逻辑意义,即陈述了命题及其真值情况。因每一个日常命题首先有存在意义,有确定的断定对象和断定内容,所以随之产生与对象实际是否一致的关系,即真值性质,符合者为真,不符合者为假。在此基础上,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日常命题也随之产生各种可能的真值关系。真值性质和真值关系统称命题真值情况,是命题所特有的。命题真值情况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也有必然与偶然之别。查其根源,有的是内容导致的,称为存在的。因对象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依存或排斥关系,命题真值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存或排斥关系。有些是命题形式导致的,称为逻辑的。因命题形式所含的逻辑概念都有特定的真值意义,在变项取值相同的条件下,使命题形式之间在真值上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依存或排斥关系。
命题的上述两种意义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反复验证。对于其中必然的情况,无论是必然的存在情况,还是必然的真值情况,都有认识的必要。这样,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命题,即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同时,也派生出了两种不同的命题成分——非逻辑概念和逻辑概念。任意一个或一组日常命题,抽象出存在意义,即认为断定的对象是有别于命题的客体对象,断定内容是这些对象的情况,那么,对日常命题的这种解读就得到了所谓综合命题;抽象出逻辑意义,即认为断定的对象是所包含的命题,断定的内容是命题的真值情况,那么对日常命题的这种解读就得到了所谓分析命题。综合命题最终都是由非逻辑概念构成。所谓非逻辑概念,就是反映综合命题所涉及对象或者对象情况的概念。分析命题由支命题和逻辑概念组成。支命题是日常命题包含的命题,是分析命题的断定对象。由于每一个日常命题至少都包含自身,因而日常命题都有支命题。逻辑概念是分析命题的断定内容。所谓逻辑概念,即反映支命题真值性质或真值关系的概念。
这里,为什么把反映分析命题真值性质或真值关系的概念称为逻辑概念?这是科学分工的结果。因命题断定的客体对象及其情况是无限的,不是哪一门科学能单独认识的,所以,非逻辑概念就成了除逻辑学外全部科学的认识成果。人们运用非逻辑概念反映对象及其情况,积累科学事实,从中抽象概括出对象情况的普遍性质和必然联系,以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与变革对象的实践活动。至于命题的真值意义,则是有限的,一门科学能够承担,认识命题真值情况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逻辑学的肩上,反映命题真值意义的概念就命名为“逻辑概念”。逻辑概念也可以称为真值联结词。逻辑史上,真值联结词曾经只是特殊的逻辑概念,只是部分逻辑规律的根据,若直接使用它,似有用特殊代替一般之嫌。所以要使用它,必须限定,指出它是一般的,是全部逻辑规律的根据。逻辑概念是命题真值信息的载体,孕育着全部逻辑规律。有了逻辑概念,就可以记录、交流命题真值情况,积累材料,从中抽象概括出逻辑规律,指导人们实现有效推理,为各门科学中的正确推理创造必要条件。若缺少逻辑概念,逻辑规律都无从谈起。一旦解释了全部逻辑规律的本质原因,超出逻辑学范围,逻辑概念便失去任何意义。
虽然,逻辑概念有特指的意义,即命题真值情况,但是,由于概念都用語词表达,語词有多义性且命题确实存在两种一般意义,因而指称命题情况的語词就出现了一词多义现象,既有存在意义又有逻辑意义。同一日常概念,从存在看,是非逻辑概念;从真值看,是逻辑概念。例如,“符合事实”就是一个关于命题的概念,在存在意义上,反映对象情况存在;在逻辑意义上,反映命题有真的真值。又如,“并非”也是一个关于命题情况的概念,在存在的意义上,反映对象情况不存在;在逻辑的意义上,反映一个命题是假的,否定这个命题有真的真值。再如,“并且”也是一个关于命题的概念,在存在的意义上,反映若干对象情况共存;在逻辑意义上,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命题都真,有合取关系。这样,同一个关于命题的概念,舍弃存在意义,只保留逻辑意义,我们就得到了逻辑概念。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任意的基本命题,就有许多可能真值关系,因而有许多逻辑概念。例如,“或者”、“要么”、“如果,那么”、“只有,才”、“当且仅当,才”、“有些”、“所有”、“必然”等,单从真值看,都是一些重要的逻辑概念。
三、逻辑概念的特征
第一,如上所述,逻辑概念都是关于命题的真值概念。逻辑概念与非逻辑概念相对,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各自选择了日常命题不同的意义,承载了完全不同的对象信息。非逻辑概念是综合命题的基本成分,是反映命题所涉及客体对象及其客体情况的概念,包括反映个体对象的个体词,反映对象性质或关系的谓词。逻辑概念是分析命题的必要成分,反映内容是分析命题所断定命题特有的真值,即命题的真、假性质或真假关系。严格地讲,逻辑概念在分析命题中也是谓词,也是陈述对象情况的,但不是一般的思维对象,而是命题。其他认识对象本身无所谓真假,只有命题才有真假问题。既然逻辑概念以命题为对象,是命题真值的载体,因而,凡是反映命题所涉及具体对象或对象性质或对象关系的概念,都是非逻辑概念;只有反映命题真值性质或真值关系的,才是逻辑概念。
由逻辑概念独特的内涵出发,立即可以发现,在逻辑研究以及教学中逻辑概念常常被误解,用对象一般的存在情况代替命题的真值情况。目前具有传统逻辑风格的教材,基本上把“并且”定义为断定对象情况都存在,有所谓共存关系,而不是应有的命题之间在真值上的合取关系。一般也把“如果,那么”定义为对象情况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甚至是多因同果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应有的实质蕴涵关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分析错误原因,主要是逻辑概念是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们对逻辑概念的认识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由存在意义到逻辑意义的认识过程。在认识过程之初往往容易用个别代替一般,用存在意义代替逻辑意义。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个别逻辑概念語言形式意义的发展过程得到说明。最典型的是实质蕴涵的語词形式“如果,那么”。起初,人们用它反映多因同果的因果关系,包含它的命题被称为因果命题。如,“如果甲得了阑尾炎,那么甲肚子疼”;“如果物体摩擦,那么物体发热”。不久,人们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如果,那么”的普遍意义,更广泛的意义是包括这种因果关系在内的充分条件关系。如,“如果汽车正常行驶,那么汽车有油”;“如果教室日光灯亮,那么教室有电”。固然多因同果的因果关系都是充分条件关系,但对象情况有充分条件关系,却不一定有多因同果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有前后相继性,一定是原因在先,结果在后。鉴于此,我们只能说正常行驶是汽车有油的充分条件,但不能说成是其原因;同样,也只能说灯亮是有电的充分条件,不能说成是原因。如此,因果意义就被更一般的充分条件意义所代替。后来,人们进一步发现,充分条件关系还不是“如果,那么”最普遍的意义,最普遍的意义应该是命题间的蕴涵关系,即任意两个命题p、q,只要不是p真q假。比较这三种关系,反映多因同果因果关系的两个命题,反映充分条件关系的两个命题,它们都有蕴涵关系。而有蕴涵关系的两个命题,反映的对象情况却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和条件关系。如贵州一名妇女,在新闻节目中谈到当前社会风气时气愤地说:“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那么,那些贪官污吏早都被枪毙八遍了。”这个命题断定的两个支命题p、q都是假的,不是p真q假,有蕴涵关系,是真的。大家听后,也都感觉很解气,认为说的对。但是,断定的对象情况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条件关系。可见,蕴涵关系才是“如果,那么”最普遍最精确的含义。表达别的逻辑概念的語词形式,也都有同样的认识过程。由此可见,真正的逻辑概念之所以姗姗来迟,把对象情况的存在意义混同命题的真值意义,真值意义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应该是主要原因。
第二,逻辑概念的存在是普遍的、有限的、固定的。这与其上述独特的对象及内容有关。非逻辑概念是综合命题的基本成分,表示断定对象和所断定对象情况。因客体的对象无穷无尽,对象情况也千差万别,所以非逻辑概念的存在是个别的、无限的、变动不居的。逻辑概念是分析命题的成分,是陈述支命题的。尽管支命题存在意义状况无限,可以说千千万万,数之不清,举之不尽,但其真值是命题共有的。每一个命题有并且仅有真假两种可能之一,两个命题之间相互区别的真值关系也屈指可数,3个或3个以上命题的真值关系,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或两个命题之间的真值情况。所以,命题的真值情况是有限的。由此,以命题真值情况为内容的逻辑概念,就具有以下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普遍的,即每一个或每一组命题都能分析出命题的真值情况,并且都有相应的逻辑概念予以反映、表现,逻辑概念成为每一个分析命题必要的组成部分;二是有限的,即逻辑概念有穷,为数不多,可以全部列举,能给出确定的存在范围;三是固定的,即在命题中反复出现,成为变中不变的稳定成分。
这一组存在特征,对认识逻辑概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普遍性表明,逻辑概念是必然存在的,不仅对每一个或每一组日常命题都可以进行分析,而且是一定能分析到的;固定性表明,逻辑概念有稳定存在形式,有别于非形式概念,是可以先行一步认识的;有限性表明,逻辑概念是可以完全认识的。如果说化学元素周期表从理论上能穷尽化学元素,那么也可以排列出逻辑概念表,从理论上先行一步,给出全部逻辑概念。
第三,逻辑概念有单义的精确的人工語词形式,也有多样的但相对固定的自然語词形式。概念都用語词表达,逻辑概念同样如此。最初的逻辑概念都是用自然語词表达的。自然語词有同义词,表达同一逻辑概念的自然語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词。如表示支命题都真,也就是有合取关系的逻辑概念,就同时可用“并且”、“不仅,而且”、“虽然,但是”、“既,又”、“先,后”、“一方面,另一方面”、“和”、“与”等語词表达。逻辑概念反复出现,虽然多样,仍相对固定,依据其确定的語词形式就能寻找到所表达的逻辑概念。因自然語词多义,既有存在意义又有真值意义,研究过程中容易出现歧义,所以,现代逻辑采用特制的人工語词符号,排除了各种存在意义,只专门表示命题真值性质和真值关系,从而使其逻辑意义一枝独秀。
第四,逻辑概念的系统形成有其独特的能行性方法,得到的概念都是成双成对的。依据逻辑概念独特的对象、含义和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特征,考察日常具体命题,当然可以分析概括逻辑概念。但是,这样概括的逻辑概念是个别的、零散的,不系统的。其实,逻辑概念系统的形成是运用必然的能行性方法严谨有序设想出来的,它们根源于日常命题实际又高于日常命题实际。所运用的能行性方法是一种必然的思考方法,这就是:先穷尽被研究命题客观的取值范围,列举所有个别的取值;然后整理被研究命题各组有矛盾关系的真值,即为被研究命题不能都不具有、也不能都具有的一对对真值情况;再次,对每一对矛盾关系的真值,根据可能真值存在具有肯定否定方式或否定肯定方式的特征,选择出可能存在的两个真值;最后,直接反映每一对可能的真值,形成一对对逻辑概念。运用这种方法得到的逻辑概念都是成双成对的,如正概念与负概念,合取概念与反合取概念,蕴涵概念与反蕴涵概念,等等。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5
克里普克提出的存在有关于对象的必然真主要是指同一陈述是必然真的,即“专名之间的同一陈述”。他写道:“如果它们本来就是真的,那么它们就不得不是必然的。”这包括形如“x是x”的形式(例如“克里普克是克里普克”),而且也包括形如“x是y”这样的形式(例如“暮星”是“晨星”)。
2、什么是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含义:
(1)含义1(非分析的)
“本质主义”的第一层含义是非分析的即存在有必然的真,它的真不依赖于句子(或命题)是分析的。
(2)含义2(不是语词的含义)
本质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是它不是指语词的含义而是指存在有必然真,它的真是指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式或者这个世界不得不是什么。
(3)含义3
本质主义的第三层含义是指存在有关于客体或者对象的必然真。蒯因说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是“关于某个对象的一些属性的理论,可能被认为是对象的本质”。“本质主义”在第三层含义上至少包括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客体(3a)
存在有关于客体或对象的必然的真,这不依赖于如何对它进行指派真值。简单地说,和蒯因的必然性论证相对,存在有一种必然真的类型陈述,过去常常用这种独立的句子来表达它们,也就是说,即使存在这样的句子能够用来表达它们的含义也不能保证它们的真值。如果它被看作是这种类型陈述,存在的问题是这些类型陈述能被分析命题所表达,那么在这层含义(3a)上有些人可能是本质主义者,但在第1层或第2层含义上就不是——但是相反,一个协定论者也就是坚持所有必然真(必然真的这种类型陈述)的人把它们的真归因于这个所给的句子的含义是分析的或者是这个语词的含义。
“客体”和“对象”这两个语词是非常模糊的,并且本质主义在第3a层的含义上很容易混淆两个不同的观点,这里把它区分为第3b层含义。
第二,第3b层含义(殊像particulars)
本质主义在第3b层含义上主张存在有关于殊像的必然真,殊像被看作是“对象”的范例(典型的对象)和在现实世界上关于对象的最简单的描述。实证主义者认为允许存在有关于开放类的殊像的必然的真,他们认为关于殊像的非限制的一般性命题(所有的xs如何表达无论何时何地都是y,其中xs可能存在)可以是分析的,或者换句话说,这种形式的命题或者陈述能被看作是必然的真,而不必和存在有本质主义的第l或第2层含义相同。但是,我们可能更适合称这些命题或陈述是关于对象的种类的陈述,而这层含义上的本质主义指的就是第3b层含义上的本质主义,即存在有关于个体殊像的必然真。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非常轻易地被看作是在第3a层含义上的一个本质主义者,而不被看作是在第3b层含义上的本质主义者,即坚持存在有关于对象的必然真而不是关于个体的殊像的必然真。
3、克里普克弱化的“必然真”的含义
在克里普克早期的工作中,他重新定义的“必然真”是这样的:
在此,让我们给必然性一个弱的解释。如果无论什么时间我所提及的在此时此刻存在的对象,那么我们能把一个陈述看作是必然的,这个陈述应该是真的。
即使存在有能够说明它可能不是真的语境,像当“在此时此刻提及的这个对象”确实不存在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定义下一个陈述也能被看作是“必然真的”。并且在旧的含义上“真的,无论如何都是真的”这个陈述也被包括在“必然真”的含义之内。有时存在有更弱的关于“必然真的”概念:即如果它是真的话,那么同一陈述被认为是必然的。
4、在什么含义上克里普克是一个本质主义者
在哪一层含义上克里普克是一个本质主义者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事实上他不仅重新定义了“必然真”,而且根据这个事实,他的关于陈述的观点好像有两种不同的辩护,特别是同一陈述,他所认为的“必然真”在他定义的“必然真的”含义上是“必然真的”。
(1)克里普克的旧-式定义的辩护
一个辩护是每一个真的同一陈述都把它的真归因于自明的真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每一个对象都是它所是的并且不是其它的对象”。
(2)克里普克的新-式定义的辩护
首先应该回顾一下克里普克介绍的他的像“两个专名之间”的同一陈述是必然的这一类陈述。可能也已经注意到,他的观点好像没有考虑到蒯因的必然性论证,这使得他有这样的观点,任何由一个必然指称它的词语所指称的对象,也可以由一个不必然指称它的不同的词组所指称。一个显著的推论是,凡由一个“两个专名之间的同一陈述”说的,也可以这样来重新表示,其中相同的对象可以用不是专名的词组来指称。因此“在专名之间的同一陈述”被假定为是必然的,当相同的对象没有使用专名来指称时,它们所表达的真理(克里普克主张应该是关于对象的必然真的表达)应该被看作并非所有的都是必然真的。从表面上看,也就是说,至少,甚至在克里普克弱的含义上,他关于同一陈述是必然的主张也是复杂的。
克里普克似乎根据语句不包含严格的指示词来处理类型陈述的表达,不同于用严格的指示词作为检测必然真或者其它真理的标准。由这种语句表示的类型陈述如果为真,那么就必然为真。所有关于殊像以及非殊像的陈述,可以用在“是”的每一边放相同的严格指示词(对象的名称)来表示。这样,例如,“克里普克是《命名和必然性》的作者”,可以解释为“克里普克是克里普克”。在这种方式下,所有的真的同一陈述都可以算作是克里普克所定义的“必然”含义下的必然真。
(3)克里普克意义的“必然为真”和本质主义
如果我们接受克里普克重新定义的“必然真”,那么他的主张在第3a和3b的含义上是本质主义的:在这层含义上,他提出的必然真既是关于对象的,也包括殊像。在第1层含义上他的观点也是本质主义的:他的必然真已经超出了真除了能够被分析命题所表达之外,还能被像“克里普克是克里普克”这样的形式所表达(它们的含义迫使它们并非在所有的语境中都表达真,而是仅当“这个在此时此刻被提及的对象存在”时才表达真)。在第2层含义的说法上能否把克里普克看作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并不是很清楚的,因为似乎好像是他把形如两个专名之间的同一陈述归类为在他所定义的必然为真的理由是,语词的意义就是一个特定种类的意义。即那种只要被提及的对象在此时此刻存在,它就必定表达一个真理。
依这种观点看,对待“克里普克是克里普克”这样的句子或命题是它表达了一个必然真的类型陈述的理由似乎是由于这个句子或命题“克里普克是克里普克”必须表达一个真的陈述,由于它提供了一个“这个在此时此刻提及的对象存在”,也就是“克里普克”已经有了一个指称并且这个指称存在。
(4)必然为真和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
克里普克在旧的必然真的含义(即真无论如何都真)上是否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太明确的,因为这不是他所考虑的问题。但是,在“真无论如何都是真”的含义上,包含关于个体殊像的陈述被看是必然真的,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论证;并且在他的旧的含义上似乎把不必然为真的陈述(同样的关于殊像的陈述)也当作是必然真的,克里普克扩大了“必然真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克里普克没有把在他的第3b层含义上(殊像)是真的,就是必然真的的本质主义看作是在他早期的“必然真的”含义上也成立。我们不能合理地猜测,他是否相信用这个旧式意义上的必然真依据分析句子或语词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是否相信第1层含义(不是分析的)或者在第2层含义上(不是语词的含义)的本质主义在他的情况中是正确的。
二、协定论的修正
1、对“分析的”和“必然真”之间的关系的修正
我们已经看到被实证主义者发展了的协定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关于指称的新的工作也证明了任何类型陈述都能用非分析的命题来表达。为了保留有一类是以分析命题定义成的必然真,因此必须把它们从这些类型陈述中区别开来,即有些能被一个分析命题所表达(如一个语句含有一个意义迫使它总是表达真的语句)。因此,和蒯因的必然性论证的前提相反,并不是所有的陈述,而仅是这些在通常意义上被认为是必然真的陈述,才能被一个分析的命题所表达。因此必然为真的类型陈述和分析命题关系的这个修正,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并且可接受的方法来把有意义的记号陈述,区分为表达必然真的类型陈述和这些不能表达必然真的类型陈述。
这样,可以将记号陈述句分成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以及分成命题的,也就是具有相同和不相同意义的字词制造者,也应该可以把这些分成含有一个意义使它们在所有的语境中都表达真的(分析命题)和这些可能不表达真的(非分析命题)。所有的前者(分析命题)应该都表达必然真,因而任何这样的记号句子——即可以获知它表示与由字词制造者认为是分析的任何命题所表示的相同的类型陈述——也可以用来表达必然真。
必然真的这种处理,在这一意义上被认为是协定论者,即所有的必然真的真理是受字词意义/语句的分析性支配的。并且它们中没有一个说的是关于“世界里的对象”的。因为与传统上的约定主义相对的“本质主义”,有时候是可以以这些意义的约定主义相容的方式来定义的,因此这个所谓的“修正的约定主义”的说法,不能被认为是在“本质主义”这个词项的每一层含义上都是非本质主义的。
已经提到的克里普克的观点,一般被看作是本质主义的,可能在第二层含义(不是语词的意义)上被看作是非本质主义的,但他包括了一些不同的必然真的类型陈述的真值范围超出通常使用的范围。这是由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把“必然真的”意义“弱化”达成的,因此一个陈述所讲到的对象可能不存在,此时也不能把它们从“必然真的”这一类陈述中排除出去。这种新的规则是关于同一殊像的陈述。在这一新的意义上辨别必然真的方法,是看只要被涉及到的对象存在的话,仅只包含严格指示词的用来表示它们的语句,是否具有一个意义使得它们不得不表达真。
克里普克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通过改变“必然真的”意义这个方法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目的。应该保留传统的“必然真的”含义,由此它意味着“真无论如何都真”,并且要求由一个含有一个意义促使它在所有语境中都是不得不表达真,这样的语句就是“分析命题”。
2、对“综合的”修正
对“分析的”和“必然真”之间的关系的修正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必然真的陈述可能由一个非分析的命题来表达,并且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即这些非分析的命题是否应该被称作“综合的”。
在实证主义者的协定论全盛时期,在相信所有有意义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必然真的-先验的,要么是综合的-偶然的-经验的,“综合命题”被处理为:
a、那些不是分析的有意义的命题。
b、偶然命题/陈述。
像“当前行星的数目大于7”这个命题,不是分析的(它的意义不能迫使它不得不表达真),但是它却表达必然而非偶然的陈述。如果这个数目是9,因而它所表达的陈述就和“9大于7”所表达的是相同类型的陈述,则它就表达了一个必然的真。如果该数字是5,则它将表达一个必然为假的陈述。如果这一类命题被归为“综合的”,那么“偶然”和“综合”之间的传统联系就消失了:这样我们就会有表示必然的而非偶然的“综合”命题。其它的方法就是把这种命题分为不是综合的,因为它们不表达偶然陈述。
在这种情况下,有既非分析又非综合的有意义的命题,而所有(有意义)命题的“分析的”和“综合的纯实证论的区分就崩溃了”。这些词语仍然彼此相斥(没有含单一意义的语句,可以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但是它们并不穷尽(有意义的)命题。
因此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非分析的”词项,这样似乎是明智的,即用它来指称不是分析的(有意义的)命题,而把“综合的”保留给这样的命题的子类,即其意义使得它们表达(或者仅表达)一个偶然的陈述,即其真值依赖于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的陈述。这个原来被实证主义者简单化的协定论不能在这些情况下被保存,因为它否定了这个被指称研究者所介绍的复杂性,并且,随着这个研究工作的深入,命题可能会有更精致更复杂的分类,而不仅仅只分为令人误解的“分析的”和“综合的”。
三、评价本质主义
克里普克认为,事物的属性有本质属性与偶有属性之分,对于如何区分事物的本质属性,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一个个体的起源(或它用以构成的材料)对于该个体是本质的。他指出:“一个对象的起源对于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制造一个对象的物质对于这个对象来说也是本质的”。二是认为一类个体的本质是那个种类里的一切个体所具有的内在本质,它使得那个种类的成员资格在本质上依赖于具有这种适当的内在结构。他指出:“一般来说,科学试图通过研究某一种类的某些基本的结构特征来寻找该种类的本性,从而找到该种类哲学意义上的本质。”[1]97-105
根据克里普克的观点,在跨越不同的世界从而需要进行识别时,对于个体,我们考察其起源或其构成材料,对于种类,我们考察其内在结构,这样就能确定其本质,从而通过本质辨识跨界中的个体是否是同一个体。应该说借助于本质主义,克里普克较好地解决了跨界个体的同一及识别问题。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6
3 语法分析,添加成分。准确把握文题的成分关系,成功添加相关成分,这对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来说,都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行文的方向明确、中心突出,才能使文字凝练而切合题意。
写半命题作文,首先要填补题目的空缺内容。这既是审题的过程,也是写半命题作文最关键的一步。填补题目空缺时考生需具备一定的语法知识。考生要仔细琢磨缺的是文题的哪部分内容,在理解命题意图的情况下,从语法的角度确定行文重点,进而填入符合要求、适合自我、富有特色的最佳字眼。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7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2-0080-04
“谓”是《墨经》中联结“名”、“实”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此准确把握“谓”的含义,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后期墨家的名学思想。自上个世纪以来,研究者对《墨经》中“谓”概念的含义已有不少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认为1、“谓”是动词,《墨经》中“谓”的三种形式(移、举、加)可以与英文中的系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相对应。[1]2、“谓”既可以作动词,指“特定对象的具体言语活动”[2];也可以作名词,指“一种简单陈述句的表达形式”[3]。3、“谓”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命题。[4]4、“谓”表判断,是思维的内容。[5]5、“谓”相当于“谓词”,是判断的谓项,句中的谓语。[6]这些从现代语言学或逻辑学角度对“谓”的解释,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墨家“谓”概念的理解;但由于过多地强调“谓”与现代学科中某些概念的表面相似性,似乎对“谓”在先秦时的本来含义关注不够。因此,本文试图从“谓”的本义和在先秦时期的一般使用情况入手,通过分析墨家学派名实观的演变,来进一步探求《墨经》中“谓”概念的含义。
一、“谓”的本义
“谓”是一个相当后起的形声字。在先秦出土文献中,“谓”一般假借为“胃”字。根据《说文》“谓,报也,从言,胃声”[7],可知在许慎看来,“谓”的本义是“报”。“报”有“告”的意思,虽不从言,但也可以表示一种言说行为。例如“子贡还报孔子。”(《庄子·渔父》)“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庄子·应帝王》),其中的“报”指的就是“报告、告诉”。不过,“告”并不是“报”的本义。从古字形上看,“报”为会意字,有惩罚、治人罪的意思。《说文》云“报,当罪人也”[8],又曰“当,田相值也”[9]。“当”有“对当、对等”之意,可见“报”的本义似指“根据犯人之罪行而处以同等之刑罚,或以同等之刑罚来表达对某罪行之态度”。其意重在“相当”或“对等”。从字例上看,先秦典籍中的“报”字大多与其本义的用法相似,表达的是类似于“以与某物相对等的他物回报之”之类的意思,而不从“告”义。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报虐以威”(《尚书·吕刑》)、“报怨以德”(《老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荀子·正论》)等等。
从“报”的本义和先秦时期“报”字的用例来看,“报”有如下特征:1、“报”一般有两个成分:一个是“报”的对象,一个是“报”的内容。这两个成分在逻辑上有先后之分。例如“报虐以威”,是先有“虐”,再以“威”报之。2、“报”具有主观性,反映了这一行为的发出者对所“报”对象的认识和态度。例如,对于相同的对象“怨”,可以“报之以德”,也可以“报之以直”。“报”之对象是已有的事实,而“报”的内容则取决于主体的认识、态度和意愿。3、“报”的两个成分虽然性质不同,但客观上都以追求某种对等性为目的,有“当”的内在要求。4、“报”作名词时,是指“报”动作的内容。如“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爵位、官职、赏罚,都可以成为对某些行为或现象的“报”。
从“报”的本义出发,结合出土文献中假“胃”为“谓”不从言的事实,我们可以推知先秦时期的“谓”字不只是一种言说行为;“谓”的含义可能与“报”的本义有更密切的关系,具备与“报”的本义相类似的特征。
二、“谓”的用法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
谓”在先秦时期的用法进一步加深对它的理解。已有学者指出,先秦时期的“谓”字句(即以“谓”为核心动词的语句)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谓”必带有“a”、“b”两个不同的成分,并且所有句式都可还原为“谓ab”这一基本句型。[10]结合上文所论“谓”之本义,可知“a”、“b”之中应有一个成分是“谓”的对象(“所谓”),另一个是“谓”的内容(“所以谓”),并且对象之实与所谓之内容应具有某种对当或对等关系,以下我们通过举例来详细探讨这种对当或对等关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种情况,对象是人。例如:1、《庄子·盗跖》:“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此句中“子”、“我”为天下人“谓”的对象,若“子”、“我”之实为“盗”,则可谓之“盗丘”、“盗跖”。2、《荀子·臣道》:“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此句中“伊尹”、“周公”为“谓”之对象,由二人具有“圣臣”之实(这是言说者的主观判断),则可谓之“圣臣”。3、《论语·公冶长》:“孰谓微生高直?”此句中“微生高”为“谓”之对象,孔子认为他没有“直”之实(“直”的品格),因此提出怀疑。
第二种情况,对象是物。例如:1、《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此句中“乳”指某食品,“虎”指某动物,“乳”与“谷”是对同一食品的不同叫法,“虎”与“于莬”也是对同一动物的不同称谓,对象之“实”就是其自身之形貌等特征。2、《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擁肿,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规矩。”此句中“之”为代词,代“谓”之对象,“大本”云云,即是对象之实。
第三种情况,对象是现象或事件。例如:1、《尚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此句中“时”通“是”,代指一种现象,“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即为这种现象之实情,言说者将此种现象称为“巫风”,“巫风”即“谓”之内容。2、《墨子·七患》:“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此句中前一个“之”字代指一种现象,“一谷不收”为此现象之实情;言说者将其称之为“馑”,“馑”即为“谓”的内容。后半句之结构与前半句相同。
第四种情况,对象是行为。这种情况与上述第三种情况类似,例如:1、《诗经·小雅·宾之初筵》:“醉而不出,是谓伐德。”2、《老子》:“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也,是谓玄德。”3、《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4、《孟子·滕文公上》:“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
由以上例证,可归纳“谓”的用法如下:1、“谓”必有对象;2、对象必有实情;3、言说者(或隐或显)根据实情,对对象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
综合《说文》对“谓”的解释以及“谓”的用法,“谓”概念的含义可以概括如下:“谓”就其本义而言就是“报”,指主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之实情的基础上,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的行为。引申为名词时,“谓”指的就是“报”的内容。家对“谓”的阐发
“谓”在《墨经》中共出现66次,但与其含义相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条:1、“谓,移、举、加。”(《经上》);2、“谓:狗,犬,命也;狗犬,举也;叱狗,加也。”(《经说上》);3、“无谓则无报也。”(《经说上》)由“无谓则无报也”,可知后期墨家对“谓”的理解并没有偏离其本义。那么,所谓“谓,移、举、加”又当作何解呢?笔者认为,这是后期墨家在坚持“以报释谓”的基础上,在名学论域中对“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是对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的提炼和深化。
首先,“谓,移、举、加”一条出现在以概念界定为主的《经上》中,且紧接“名,达、类、私”,可知本条虽然是后期墨家对“谓”的专门论述,但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名”紧密相关。《经上》“所谓,名也;所以谓,实也。”可视为另一佐证。
其次,墨子的名学主张中其实已经提及了“移(命)”、“举”、“加”,只是不够系统。例如在论及名的产生时,墨子提出:“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勉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
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非攻下》)“义”的含义是明确的,就是“圣王之法”(即兼爱非攻)。而天下的诸侯行“攻伐并兼”等不义之实,却仍然拥有“誉义之名”;在墨子看来,这显然是人们“不察其实”而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因此,就“名”的生成而言,对待各种现象和行为要“察其实”而后“有其名”,对各种事物则应“分其物”而后“命其名”。
在论及名的使用时,墨子说:“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天志上》)“暴王”是已有之“恶名”,用“暴王”之名来称谓那些“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的诸侯国君,正是表达了墨子以“名”来分辨和评价对象的用名主张。
由上可见,在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中,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通过对象获得名,以及通过名认识、分辨和评价对象的建构存在,而“命”、“举”、“加”是其中的关键词。后期墨家正是在此基础上,以“命”、“举”、“加”重构了“谓”的含义,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系统表征“命名”、“举实”和“用名”的名学概念。
“命”,就是据实命名。例如谓“狗”为“犬”。“狗”在这里不是指称一个语词,而是指称命名的对象,属于语词的正常用法;“犬”指的是语词本身,即“犬”这一名称。看见一种动物,根据其实(如形貌等特征)将其命名为“犬”,这就是“命”。由其过程表现为将对象之“实”转以语词之“名”代替,因此也称为“移”。与此类似的,如“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经说上》)等等。其中的“命”都是指根据对象之实进行命名的行为。
“举”,即《小取》篇所说的“以名举实”。“举”的本义是“双手托物”,《墨经》又以“拟实”释“举”,都是为了说明“举”的功能就在于通过名来比拟实,或通过名来再现实,也即荀子所谓“名闻而实喻”(《荀子·正名》)之意。“举”可以看作是“命”的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举出来的“名”仍然是命名时的含义和指称,是“有固实”之名,因此《经说上》云“狗犬,举也”,即在强调其含义和指称的确定性。又如“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天志上》),“圣王”或“暴王”之“名”所对应的“实”都是确定的,即“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或“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用前者之名,意在举出或再现后者之实。
“加”,是将所举之名运用到具体语境中的行为。“名”产生于特定对象,但从其产生之时起,又必然与其命名时所据之对象相脱离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加”的过程,就是将这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公共之名”重新加以具体化,以指称新的对象的过程。所举之名一旦运用到具体语境中,就由静态之“名”转成了动态之“谓”,有了新指称对象,并体现出言说者的主观意愿和认识。例如《墨子》中的“圣王”之名,本产生于“禹汤文武”等特定的对象,但一经产生后,就可以用来指称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的诸侯。以“圣王”之名来指称这些诸侯,就是“加”。
我们可以通过《墨子》书中的原例来区分这三种“谓”的不同,例如:“禹汤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谓之圣王。……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天志上》)按照上文的辨析,可以将此节中的“命”、“举”、“加”区分如下:
命谓部分
对象:禹汤文武
对象之实: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命名:圣王
举谓部分
以名:圣王
举实: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加谓部分
所加之名:圣王
所指之实: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
指称对象:当时
的诸侯国君
析而言之,“圣王”在命名时具有确定的含义(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和所指的对象(禹汤文武),在“以名举实”的过程中也仍然保留了命名时所对应的“实”。到了“加谓”阶段,“圣王”之名便有了新的“实”(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等等)和指称对象(当时的诸侯国君)。因为新的“实”与“圣王”之名原有的“实”相对当(均可归结为“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因此可以将“圣王”之名加在新的对象(当时的诸侯国君)上,用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认识和态度。
综上,可知后期墨家并没有偏离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基本思想;只不过他们将这一整套过程简化成了“命”、“举”、“加”这三种“谓”的形式或环节。后期墨家对“谓”概念的细化和扩充,其实是对墨子名学主张的精致化和系统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谓”在先秦时期是一个使用非常普遍而又有独特意味的语词。一方面,它与“言”、“语”、“曰”、“云”一样,作为言说行为的表征动词,在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它又不是普通的言说动词。作为联结“名”与“实”的桥梁和手段,“谓”自有其独特的内涵和使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拿现代学科中的某些概念来比附。同样,作为先秦时期唯一对“谓”有过专门论述的学派,后期墨家对“谓”的理解和运用也与当时的语言使用背景和他们的学术渊源密切相关;如果不将这些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我们对《墨经》中“谓”概念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
参考文献:
[1]谭戒甫:《墨辩发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104页。
[2][3]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308、311页。
[4]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5]詹剑峰:《墨子的哲学与科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8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从“言必称生态”说开去
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在谈论事物时加上“生态”二字,可谓“言必称生态”的境地,堪与当年的“言必称希腊”相提并论。不仅如此,各种与生态结合而产生的学科门类层出不穷,如在语言类学科中就有新兴的生态文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翻译学等等。
“生态”一词的广泛应用与社会的发展需求分不开,但是如何把握在这一发展变化中生态一词的确切含义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对新兴学科中生态的含义存在误读现象。各个学科中对生态一词的理解有哪些异同,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并找出解决的办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先从生态一词本身的含义谈起,然后分析其在生态文学中的使用以及误读情况。
二 关于“生态”
1 生态一词的由来和定义
“生态”一词,词源来自希腊语,是由Oikos派生出来的,意思是住所或房子。在19世纪以前,独立的“生态”一词与生态学学科是不存在的。“生态”一词的诞生以及生态学的兴起,首先应归功于德国学者赫克尔,他于1886 年正式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认为生态学是“关于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外部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生态是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这里的自然界是指野外,即人类居住环境以外的地域除却城镇和村落。生存状态包括适应进化的历史和协调存在的现状格局。
2 生态含义的变化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快,“生态”一词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基本内涵,含义不断丰富、扩大,词义也不断深化。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生态的内涵是指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时的主体不包括人类。从6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必须用系统、整体的观点考虑社会、经济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过程中生态的内涵被不断扩大、深化,开始包含人类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关系,最后一直到人类环境中各种关系的和谐。同时,生态的主体也转为人类。
在生态内涵演化的过程中,“生态”一词的含义也逐渐由单纯生物学的含义向 “综合的、整体的”含义转变,蕴涵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内容。“生态”一词的词性也由单纯的名词转化为形容词。作为修饰定语,“生态”二字包含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系统”和“整体”的含义,如生态城市、生态建筑、生态社区、生态文明等等。
同时,由于生态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其与其他各学科的结合也开始变得可能,于是出现了生态文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翻译学、生态文化等等跨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
3 生态含义变化的原因
生态一词的含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变化,具体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是促使生态含义扩大的主要原因;(2)就全球而言,环境问题呈现出全球化特点,引起了整个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关注;(3)从个体国家而言,生态环境问题开始于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4)整个人类社会呼唤和谐“生态”系统。
三 生态一词的在生态文学中的使用和误读分析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的特点。
1962年,美国女作家卡森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生态文学时代的到来,即作家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美、英、法等国家纷纷出现各种体裁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批评也相应兴盛起来。中国的生态文学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80年代中期,内地文学界亦见生态意识的觉醒。近年来,生态文学思潮可谓形成。各级环保部门纷纷疾呼文学家将写作向生态倾斜,专门发表生态作品的文学刊物也已出现,最为可喜的是一些作家走出书斋、走进自然,被称为生态文学家。
当然,生态文学不仅仅是单纯的描写自然,它主要探讨和解释自然与人的关系,特别侧重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也即造成人类特征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有些可以不描写自然景物,但因其深刻发掘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社会原因而出名。
生态文学给人的第一反应是描写生态环境的文学作品,但是生态文学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指研究生态的文学,或研究文学与生态的关系的文学。从根本上来说,“生态文学”的关键是“生态”,这个限定词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指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而是指这类文学是“生态的”――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
而且,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潮,属于文学流派中的一种,是生态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更确切地说,生态文学指的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分析。它因生态思潮的流行和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产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对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已经过了高潮期,即无论怎么谈论都无法走出原有的分析套路,单纯冠上“生态”的名义并无太多的文学价值。而在国内,尽管生态环境保护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生态文学批评并没有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这方面的研究也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四 存在误读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1 存在误读的原因
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让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在各个领域对生态一词的使用更是成为一种时尚和显示自己符合时展要求的象征。基本上可以说,生态一词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满眼充斥的都是关于生态的名词和术语。这难免会产生对生态一词含义的不同解读,抑或是误读。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之所以产生误读的原因。
(1)生态一词自身含义的变化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对生态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中生态含义的错误解读,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生态一词的内涵。按照生态一词的定义,生态是指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其基本内涵是指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它的含义已远远超出基本内涵,开始转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甚至是人类环境中各种关系的和谐。主体也从不包括人类变为以人类为主体。
生态的内涵在变化,词义在扩大、丰富,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走出自身的范畴,开始于人文科学结合,并寻找契合点。在文学上以《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开始了对生态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在语言学上,把语言结构系统与生态系统相类比,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语言的本质,了解语言的发展变化。翻译中,借助生态的观点,出现了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以求通过翻译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含义的变化为生态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人们对生态本身的含义理解不到位,从而导致对交叉学科中生态一词的含义把握不准,出现误读现象。
(2)学科命名带来的概念混淆现象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作为新兴学科的命名,如何体现语言的简洁性和明确性是在为学科命名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目前国际学界在命名与生态学有关的跨学科研究时,大多采用“生态+某学科”的方式,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等。在语言类学科中,采用生态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来命名着实是一种符合命名学原理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术语却带来易让人们误解的弊端。因为同样的命名方法得到的术语应该具有基本一致的含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生态文学中的生态和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含义是不一样的,与生态翻译中的生态含义更是大相径庭。
毋庸置疑,每一种理论都有一些特定的术语,是形成这种体系理论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一种理论往往需要“借助于特定的语言”将“自己特有的认识成果”表达出来。命名一个学科必须寻找一个简短而又明了的术语,生态文学这一术语确实可以把体现生态思潮的文学作品与其他类型的文学形式区别开来,也让人们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但是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并不表示描述生态系统所使用的语言,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也不是指对那些关于生态方面的作品等的翻译活动。所以,这样的命名就在概念上给人带来易于混淆的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误读现象的产生。
(3)人们的认知心理模式
生态一词的含义不断扩大变化,体现了人类认识上的不断深化,也体现出人们认知心理模式的不断深入。关于认知的性质和发展的观点目前非常流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就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认知发展理论――他把人类认知看成是一个复杂有机体之于复杂环境的一种具体的生物适应方式。像其他形式的生物适应一样,认知总是表现出提示存在而又互补的两个方面,皮亚杰称之为同化和顺化。
根据这一认知理论,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时总是进行着同化和顺化两种认知活动。比如,人们一旦掌握了生态文学的含义,就会采用同化的认知方式去认识其他相似的学科如生态语言学和生态翻译学。按照这样的方式,人们就会把生态文学中“生态”一词的含义照搬到生态语言学等类似学科上,从而引起对不同学科“生态”含义的误读。
2 消解误读的措施
针对上述对误读产生原因的分析,笔者试图找出消解对生态一词含义误读的具体措施。
第一,加强对生态一词本身含义的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不断更新对生态含义的解读,才能在此基础上去理解与生态相结合的新兴学科中生态的真正含义。生态一词的含义早已超越生物学的范畴,逐步具有整体观、和谐的思想,所以这就要求人们在理解与生态有关的学科时顾及到生态的真正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态一词在交叉学科中的含义。
第二,科学合理的为术语命名。不断涌现的学科门类令人眼花缭乱,界定一个含义明确的术语就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认为,不要为了创造一个概念而去命名一个新的概念名称。如生态翻译学的命名就不太科学,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只是从生态学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既然生态翻译学这一术语容易造成误解,那么不妨把它定义为“生态翻译观”,或“翻译生态论”,或许会更容易令人明白。
第三,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转变认知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在不断的更新,人们对语言现象的认识也应该不断提高,不断学习新的认知理论模式,吸收新的认知模型和隐喻理论中的精华,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生态一词被广泛应用后的真正含义,减少或尽量避免对此的误读。
五 结语
生态一词的广泛应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多个学科结合出现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是生态含义不断扩大和学科发展需求相互结合的产物。本文通过对生态一词在生态文学中的应用,借用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发展变化理论,分析了生态一词的真正含义的变化历程和原因,并指出生态一词与文学结合后存在的一些误读现象,归纳出存在误读的三大原因,并在最后提出了几条消解这些误读的措施,以期本文能有助于人们对生态一词含义的准确理解和正确使用,并为跨学科术语的命名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 Piaget,J.Piaget’s theory.In P.H.Mussen(Ed.),Camichchael’s manual of child psychology[J],1970,vol.1.
[2]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J・H・弗拉维尔、P・H・米勒、S・A・米勒,邓赐平、刘明译:《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9
Development of "Worrying" and Mental Imagery
ZHOU Ling, SUN Yuejiao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The first part analyzed the glyph,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worry". Initially, the "worry" is through the "autumn" word to express. I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process, in order to emphasize the human mental activity, in the "autumn" word below added a "heart" to represent mental activity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 feelings. And psychology related to "worry" There are three kinds: sorrow, sorrow and nostalgia. With the "worry"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 poetry analogy to other commonly used to express the image of "worry". The second part respectively uses cicadas, autumn and landscape imagery three kinds to simulate of worrying.
Key words worry; autumn; image
1 “愁”的发展
离别相思之愁、伤春悲秋之愁、故园家国之愁,到处可见对愁的描写。正因为愁情无处不在,由此涌现出一批以描写此情而闻名的人物:李清照、辛弃疾、余光中等等。从古至今,愁情一直围绕着无论是文人过客还是平民百姓。
1.1 “愁”的形成
“愁”由“秋”和“心”构成。“秋”原型写做,完全是一只蟋蟀的样子,因为蟋蟀只活于秋季,秋过而生命消逝,因此用蟋蟀的形状来表示“秋”。又因为秋天万物萧瑟,草木凋零,秋虫身故,景象荒凉,因而古人也用“秋”来表示“愁”的情绪。《广雅·释诂四》中有:“秋,愁也。”“愁”情最初即是用“秋”字来表示的。“心”为象形字,最初是以心脏的形状来表示,即,随后发展为“心”,成为现代汉字中常见的组成部分,凡是跟心理活动有关的字词,都包含着“心”。
“愁”字出现较晚,是到了说文·心部中才有记载的,“秋”与“心”都出现较早,“愁”即是由这两字组合而成的。最初写作,虽然“愁”字出现较晚,但并不代表这种情感也出现教晚,只是这种愁情由出现较早的“秋”来表示。既然“秋”可以表示“愁”,为什么又要另外造“愁”字呢?这与语言文字交际职能的制约有关:“秋”的本义指四季之一,由于“秋”的时令特征(因为秋天草木凋零、万物萧瑟,因此很容易产生愁情)引申出“悲愁”之义,但是同一个字,既要表“秋”,又要表“愁”,容易产生混淆,进而有碍信息的准确传递,所以需要另造“愁”字分担其义。于是,人们便在“秋”字下面加了“心”部来表示“秋”的引申义——“愁”。①也更突出了“愁”为心理活动。
1.2 “愁”的含义
《说文》中有:“愁,忧也。从心,秋声。”“愁”有三种读音,每种意思不同。(1)chou读二声。其意思有:①,忧愁;忧虑。《说文·心部》:“愁,忧也。《增韵·尤韵》:“愁,虑也。”《后汉书·章帝纪》:“令失农作,愁扰百姓。”②,悲哀,悲伤。《广雅·释诂说》:“愁,悲也。”③,忿恨。《广雅·释诂二》:“愁,恚也。”④,苦。《墨子·所染》:“伤形费神,愁心劳意。”《论衡·治期》:“愁神苦思,撼动形体。”⑤,景象惨淡。汉班倢伃《擣素赋》:“佇风轩而结睇,对愁云之浮沉。”(2)qiao读三声《集韵》子小切,上小精。同“愀”。容色改变貌。《集韵·小韵》:“愀,色变而。或书作愁。”陆德明释文引郑玄曰:“愁,变色貌。”(3)jiu一声《集韵》将由切,平尤精。同“楢”。聚集。《及韵·尤韵》:“楢,《说文》:‘聚也。’或愁。”②
在“愁”的解释中,只有二声读音“愁”的前三种与心理学意义有关,但第三种“忿恨”已经不再用愁来表示。同时,“愁”的含义在发展中又衍生出另一种寓意,即“乡愁”,表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愁”的含义中,最常见的即是忧与悲的解释。由于意象思维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主要通过以物观象以及取象类比的方式认知世界、推演联系。③因此愁情经常以意象的方式表现出来。
2 “愁”的心理学意象
“愁”(worry, anxious),在甲骨文中原形为蟋蟀之类的昆虫。蟋蟀属于一种秋虫,只活于秋季,其叫声愀愀然,秋去即身死。高树藩总结说:“古人造“秋”字,文以象其形,声以肖其音,更借以名其所鸣之季节曰秋。”④因而,“秋”字所包含的原型意义,也就有了生命衰微走向死亡的信息,包含着凄凉和悲哀的意境。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意象符号是一种工具,是由读者接受过程中不断被改造成具有主观经验及情感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意象的选择、提炼、重组是受作者的主观情绪支配的。⑤文人墨客的作品中也处处留有取物类比的痕迹。鉴于以上对“愁”的分析,其意义主要表现为三种:忧愁、悲愁和乡愁,相应的通常以蝉、秋和自然景物的意象来体现。
2.1 以蝉所体现的“忧愁”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说:“忧愁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蝉意象凝聚着古代文人叹时伤逝的生命体验,是他们生命意识的外化。蝉到夏季才变为成虫,到了深秋季节就要死去,生命极其短暂。庄子有。“蟪蛄不知春秋”之说,据《雅·释虫》记载,蟪蛄即蝉的异名,是生命短促的象征。此意象与最初“秋”字的蟋蟀形象相同。而对人来说,生命也只是一次性的,蝉与人生命短暂的相似性,使人对蝉有了深深的认同感。因此,人们在听到蝉秋日的叫声,极易惹动自己对生命的惆怅之情,产生生命短暂,人生苦短的愁情。例如:唐代雍陶的《蝉》中有:“高树蝉声入晚云,不惟愁我亦愁君”;唐代陆畅的《闻早蝉》中有:“落日早蝉急,客心闻更愁。一声来枕上,梦里故园秋。”作者通过以蝉类比的方式,将愁情寄予其中。蝉也因此成为“忧愁”的代名词。
2.2 以秋所体现的“悲愁”
朱熹在分析悲秋—大自然的生命律动与人生自我关系时说:“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萧条寒凉,阴阳用事,草木零落而百物凋悴之时,有似叔世希邦,主昏政乱,贤智屏绌,奸凶得志,民贫财匮,不复振起之象。”⑥文人中也常以“秋”来表达愁情,如: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中有“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杜甫《登高》中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郎士元《登高》中有“共是悲秋客,哪知此路分”。作者分别将仕途坎坷之愁、沦落他乡之愁、分离之悲愁通过秋天的意象表现出来。
2.3 以景物所体现的“乡愁”
在台湾的散文创作中,思乡怀归情感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在以物寄乡愁的表达中,尤以余光中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后,余光中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因此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如:在散文《乡愁》中,他将乡愁比作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峡。席慕容的《乡愁》中也这样写到:“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以描写愁情著称的李清照也用自然景物来表达“愁情”。她在《一剪梅》中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注释
① 蒋蕊.“离人心上秋”——说“愁”.咬文嚼字,1995(4):13.
②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971-972.
③ 吕小康,汪新建.意象思维与躯体化症状:疾病表达的文化心理学途径.心理学报,2012.44(2).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10
1 作为真实个体的存在与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
关于存在的涵义,粗略一看,似乎很简单,我们常说“某某存在”或“某物存在”,其意 就是“有某某”或“有某物”。但仔细思考,可以看出,自然语言中所指的存在或存在物, 是有不同的涵义或层次的。比如,在下列四个语句中,所讲的存在的涵义严格地说是不完全 相同的:
(1)艾菲尔铁塔存在。
(2)动物存在。
(3)存在着大于3而小于7的质数。
(4)他的身上存在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在语句(1)中,存在的对象是“艾菲尔铁塔”,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个体,在语句 (2)中,存在的对象是“动物”,即由各种各样的具体个体组成的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 无法找到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作为类的“动物”,在语句(3)中,存在的对象是数,即 数学的对象,而在语句(4)中,存在的则是对象所具有的某种性质或属性,因此,这几种存 在物是有别的。语句(1)中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真实的个体,语句(2)、(3)、(4)中所存在 的对象则或是个体所组成的类即共相或是数学的对象或是对象的性质,我们统称为“抽象实 体”。可见,存在或存在物是有不同的层次或类型的,事实上,如果从时间上来考虑的话, 存在或存在物还可以有时间上的层次:过去的存在与现在的存在,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的存在是过去的存在,当今美国总统布什的存在就是现在的存在。当然,出于研究的 考虑,在本文我们忽略存在的这种时间层次上的差别。
关于存在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何物存在”,即存在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 一般地说,存在问题所涉及到的存在对象主要包括上述四类对象。就唯名论而言,他们只承 认存在有个别的具体事物,即真实的个体,而不承认诸如类、数、关系、属性等所谓的“抽 象实体”的存在。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者则承认抽象实体的存在,认为各种数学与集合论的 对象以及属性、关系等均可以是存在的对象。
在存在问题上,注意到“存在”的不同类型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可以认为,唯名论所理解 的存在是狭义的,按照这种理解,只有客观的个体对象才是存在的。而实在论则对存在作广 义的理解,认为共相以及属性、关系、数等等都可以是存在物。从这一点出发,则可以推出 ,唯名论不承认思想中的对象的存在,而实在论则认为不仅客观现实中的对象是存在的,思 想中的对象也是存在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个人认为,严格地说,存在问题及其争论主要是 在唯名论的意义下出现。如果取实在论的观点,即承认各种不同层次的存在或存在物,则所 谓的存在问题就不会出现。当然,尽管对存在或存在物可以区分出很多层次或类型,但是, 从实用和简单原则出发,我认为,可以宏观地把存在分成两个层次或类型:现实中的真实的 存在与思想中的存在。我们在分析存在语句时,只要注意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区分,则所谓的 存在难题就并非是难以解决的。
在存在问题的诸多难题中,其中之一就是梅农所谓的“金山存在”问题。按梅农的观点, 当我们说“金山不存在”时,由于我们一般都预设了语句的主词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将面 临这样一个难题:如果金山不存在,那么“金山”这个词无意义,因而“金山不存在”这句 话是无意义的,如果金山存在,那么“金山不存在”这句话就等于是说“存在的金山是不存 在的”,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所以,“金山不存在”这句话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自相 矛盾的,因此,我们不能说“金山不存在”,而只能说“金山存在”[1]。
可以看出,如果对“存在”只作唯名论意义下的理解,即只承认客观世界中真实个体的存 在,那么,毫无疑问,梅农的这一“存在难题”确实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对“存在” 作实在论意义下的理解,取“存在”之广义,即承认思想中的对象的存在,那么,梅农所谓 的“金山不存在”问题则是可以解决的:在“金山不存在”这一语句或命题中,主词“金山 ”所意谓的存在是思想中的存在,而谓词“不存在”中所指的存在则是作为客观现实中的真 实个体的存在,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存在,因此,主词所意谓的“存在”并不构成对谓词“ 不存在”的否定,这句话的真实涵义是:作为思想对象存在的金山在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 也就是说,“金山”只是一种思想中的存在物,并不是客观现实中的真实个体)。在这种理 解下,则不仅“金山不存在”之类的语句难题可以解决,即使像“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 屋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语句也是可以理解的:“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指思想 中的对象,是人们思维中的存在物(谁能否认这种思想之物的存在呢?人们在思想中是可以想 像 该对象的存在的),而谓词的“不存在”则是指它作为客观真实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因此, 这句话的实际涵义是: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物的“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在客观现 实中是并不存在的。
在存在的类型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要区分“可能世界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存在”, 比如国内学者陈波与杜国平等都有此看法。例如,陈波认为:“自然语言中的存在语句大都 相当于一个命题函项:a存在于W,这里的a是个体常项,W是世界变元(或场所变元),它的值 域是由所有的可能世界组成的集合。当对这个函项中的惟一的不确定成份(变元)W代之以可 能世界集合中的不同世界时,相应的存在语句就获得不同的真值:在W的一种赋值下为真, 在另一种赋值下为假。例如,如果我把‘贾宝玉存在’理解为‘贾宝玉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 ’,该语句为假;但若把它理解为‘贾宝玉存在于《红楼梦》所描绘的可能世界中’,则该 语句显然为真。”[2]杜国平先生也认为,“存在”是一个跨界谓词,即跨越可能世界与现 实世界之间的,因此,要注意区分不同世界下的‘存在’”[3]。
将存在分成可能世界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存在,这一观点我是基本同意的,运用这一观点 ,也可以很清楚地消除“金山不存在”之类语句的难题:在可能世界W中(可能)存在的金山 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可能世界”是一个逻辑学概念,它有一个基本的要 求,就是在“可能世界”中不允许逻辑矛盾的出现,所以,对于“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 屋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语句,即使用跨界存在理论也无法解决,因为,“又圆又方”是一 逻辑矛盾,从逻辑学的观点看,这种逻辑矛盾即使在可能世界中也不应存在[4]。
正是由于运用“可能世界”概念也不能完全解决存在难题,所以,我认为,不妨撇开“可 能世界”这一概念,将存在分成“作为客观现实的真实个体的存在”与“作为思想对象的存 在”:由于在“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中,思想对象即思维中的产物,因此,即使它是自相 矛盾的也是允许的,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它只能存在于思想中而无法 存在于客观现实中。
2 隐含的存在与明示的存在
对于“金山不存在”或“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不存在的”之类的“存在难题”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是试图将存在作“真实个体的存在”与“思想对象的存在”之分来 解决的。对于这种解决方式,有人可能不同意,即不同意将存在取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倾向 于唯名论意义下的存在。那么,下面我们要考虑的是,如果取唯名论意义下的狭义的存在, 即认为存在只是真实个体的存在的话,我们怎样解决上述的“存在难题”呢?
存在问题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主词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逻辑哲学中的表 述就是:在形如“S是P”或“S不是P”之类的命题或语句中,S作为命题或语句的述说对象( 即主词),是被预先假定为“存在”的,这也就是说,一旦某人作出“S是(不是)P”之类的 命题或语句,他就认定了S是存在的。也正是由于这个主词存在的预设,就导致了“金山不 存在”之类的“存在难题”:在形如“S是不存在的”之类的命题或语句中,一方面该命题 或语句本身预设了主词S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命题或语句的谓词又指出了S是不存在的,因此 ,“S是不存在的”就等于说“那个存在的S是不存在的”。
要在取“存在”之狭义即在唯名论所指的存在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有必 要将存在区分为“隐含的存在”与“明示的存在”。
转贴于
我认为,任何一个形如“S是(不是)P”之类的命题或语句都预设了主词S的存在,这种意义 下的存在是通过语法或语义蕴涵“隐含地”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把这种意义下的存在谓 之命题或语句的“字里之意”或“潜在之意”,它所谓的“存在”是一种“隐含的存在”。 而在“S是存在的”或“S是不存在的”中作为语法谓词所明确宣称的“存在”或“不存在” ,则是命题或语句本身明确地显示的,因此,这种意义下的存在我们谓之“明示的存在”, 它属于命题或语句本身的“字面之意”。从逻辑层次来说,在一个命题或语句中,“明示的 存在”要强于“隐含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命题或语句中,其隐含的存在与明 示的存在并不矛盾,那么隐含的存在就可以上升为明示的存在,即由“隐”变“显”,比如 在语句“小张考上了大学”、“史密斯先生出去旅游了”中,都有“小张存在”或“存在一 个叫史密斯的人”之类的隐含存在,由于它们与语句本身的明示之意不相矛盾,因此,这些 隐含的存在是合理的,可以由“隐”变“显”。反之,如果在一个命题或语句中,既有隐含 的存在,也有明示的存在,且两者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明示的存在要 强于隐含的存在,于是,明示的存在就自动地消除了隐含的存在,整个语句便只包括“明示 的存在”之意。例如,在“孙悟空是不存在的”这一语句中,主词预设了“孙悟空是存在的 ”,但语法谓词“不存在的”则明示了孙悟空的不存在,在这里,隐含的存在与明示的存在 发生了矛盾,因此,明示的存在就自动地消除了隐含的存在,这样,整个语句的意思就是“ 孙悟空是不存在的”而不是“那个存在的孙悟空是不存在的”。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 解决“金山不存在”与“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不存在的”之类的难题。
这也就是说,作为命题或语句的字里之意的“隐含的存在”与作为命题或语句的字面之意 的“明示的存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存在,一旦在命题或语句中两者发生冲突,则明示的存 在就自动地消除了隐含的存在,这样,整个命题或语句就以明示的存在为准。
在对存在作“隐含的”与“明示的”之分这一点上,逻辑学家盖士达的“潜预设”(Pre-Su pposition)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是有助的。按盖士达的观点,所谓一个语句的 潜预设,是指该语句所具有的潜在的、可能的预设,它是一个句子从语义上分析而得到的预 设。一个语句的潜预设如果与该语句的特定的语境相一致,则它就显现出来,成为实际的预 设,反之,如果它与该语句的特定的语境相矛盾,则它就被该语境消去而不复存在了。例如 ,相对于语句“小王用不着戒烟,因为事实上小王从没有抽过烟”,尽管“小王用不着戒烟 ”有预设“小王曾抽过烟”,但由于它与后面的语句相矛盾,所以,后面的语句“因为小王 从没有抽过烟”就自动消去了这个预设,因此,这只是一个已被消去的潜预设[5]。可见, 按盖士达的观点,对语句的潜预设的设定只是语义上的分析,而该潜预设在具体的语境中能 否显现出来,则是一个语用问题。套用盖士达的这一说法,我认为,我们也可以说,隐含的 存在只是一个语义上的问题,而它能否变成明示的存在则是一个语用问题。
3 传统逻辑的存在与现代逻辑的存在
存在问题并非现代逻辑的产物,实际上,在传统逻辑的性质命题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主词存在问题”。
我们知道,在性质命题中,同一素材的四种命题A、E、I、O之间具有真假之间的可推导关 系: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矛盾关系、差等关系。根据这些关系,我们便可以在四种命题 间进行推导,比如,由A命题的真,可以推知E命题为假,由0命题的假可以推知A命题的真, 等等。这种同一素材的A、E、I、O之间的真假关系,也叫对当方阵。但是,这种推导关系有 时会出现问题。例如,根据差等关系,由SAP的真可以推出SIP一定真,可是,当我们由“所 有的金山都是金子做成的”推出“有的金山是金子做成的”时,我们就发现,这种推理并非 是保真的,因为,在这个推理中,前提“所有的金山都是金子做成的”无疑是真的(即使并 不存在现实的金山),但结论“有的金山是金子做成的”却是假的,因为后者是一个特称命 题,也叫存在命题,其意为:至少存在一座金山是金子做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逻 辑对根据对当方阵所进行的推理有一个要求,即性质命题的主词必须被假定是存在的,如果 不假定主词是存在的,则从全称到特称的推理就不是保真的。
因此,传统逻辑在推理中引入了本体论的假定,它要求主词都必须是存在的。而事实上, 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这种假定是错误的。所以,现代逻辑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解。我 认为,现代逻辑对存在问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现代逻辑对传统的性质命题作了更为精确的分析。就传统逻辑来看,性质命题都是 主谓形式,它们所断定的是普通名词之间存在的关系,因此,传统逻辑认为,全称命题A与 特称命题I的区别只是主词的周延情况不同,即前者的主词是周延的而后者不周延,除此之 外,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这一观点,现代逻辑并不同意,现代逻辑认为,全称命题A 与特称命题I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于主词的存在并没有作断定,而后者则对于主词的存在 作了明显的断定,因为,全称命题是一个假言命题,而特称命题是一个存在命题。这也就是 说,全称命题“所有S都是P”的真实涵义是:对于所有的个体x,如果x是S,那么x是P,用 公式可以表示为:。而特称命题“有的S是P”的真实涵义则是:至少存在一个 个体x,x是S并且x是P,用公式可以表示为:。通过现代逻辑的这一分析,我 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主词并不存的情况下,全称命题仍然是真的,而特称命题则是假的 ,因此,在现代逻辑中,SAPSIP的推理是无效的。
第二,在“存在是不是一个谓词”这一问题上,现代逻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针对“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提出,“存在”不是一种性质,因此,它不是 一个谓词,随后,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逻辑学家与哲学家的赞同,弗雷格、罗素、斯特劳 逊、摩尔、赖尔、艾耶尔、奎因等都持相同观点。按他们的观点,尽管“棕色的牛是存在的 ”与“棕色的牛是健壮的”这两个句子形式相同,即“存在的”与“健壮的”都出现在谓语 位置上,因而从形式上看两者都是谓词,但实际上,语句中的“存在”是可以等值地消去的 ,因为,“棕色的牛是存在的”可以等值地转换为“有的牛是棕色的”,而“棕色的牛是健 壮的”中的“健壮的”却不能被等值地消去。因此,“存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逻辑谓词而 是一个量词,存在语句实际上是一个量词语句,所以,可以用现代逻辑的量词理论来处理存 在语句。
我们知道,在谓词逻辑中,量词主要有两个,即全称量词与存在量词,分别表示为x与x, 前者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所有”、“任何”、“一切”等,后者则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 有”、“有的”、“有些”等。如果我们对量词取其客观解释,则全称量词可 解释为“对宇宙间的所有事物x来说,x都是F”,而存在量词则可以解释为“ 宇宙间至少有一个事物x,x是F”。以这种解释为基础,弗雷格与罗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 点:存在就是命题函项的可满足性。按弗雷格与罗素的观点,谓词其实质是以命题为值域的 函项,一个全称语句是指所有的个体都满足该命题函项,而一个存在语句则是指至少有一个 个个体满足该命题函项。说一个存在语句为真,也就是说这个存在语句的命题函项是可满足 的 [6]。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奎因也认为,我们如果要探究某一理论或思想中 的本体论,即探究这种理论或思想中承认哪类对象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或思想先 进行谓词逻辑的处理,将其语句进行量化,然后确定该理论或思想中哪些量词式是真的(即 确定哪些量词式是该理论中的定理),最后再确定要使得这些量词式为真,存在量词式的约 束变项该取什么值。这些存在量词式的约束变项所取的值便是该理论或思想所认可的存在物 。因此,奎因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存在物的整个领域是变项的值域,存在就是一个 变项的值”[7]。奎因还进一步指出,所谓存在,就是在一个约束变项这种代词的指称范围 之内。“被假定为一个存在物,纯粹只被看作一个变项的值”,“我们的整个本体论,不管 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本体论,都在‘有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这些量化变项 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当且仅当为了使我们的一个断定是真的,我们必须认为,所谓被假定的 东西是在我们的变项所涉及的东西范围之外,才能确信一个特殊的本体论的假设。”[8]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认为“存在”不是一个逻辑谓词,用量词理论来处理存在问题, 这就是现代逻辑对存在问题的主流处理方式。(当然,也有一些现代逻辑分支仍然认为存在 是一个谓词,比如非经典逻辑中的自由逻辑就持此观点。)在这种处理方式下,存在被看作 命题函项的可满足性,是约束变项的值。很明显,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就是将存在问题变成 了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从而从逻辑上解决了所谓的“存在难题”。但我认为,这种处理方 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回避了存在作为一个谓词所面临的各种逻辑哲学问题,毕竟,存在 至少是一个语法谓词。因此,我认为,本文的第一与第二部分实际上就是在承认存在是一个 逻辑谓词的前提下对解决存在问题所作的一种探讨。
参考文献
[1][6]陈晓平.关于存在问题[J].哲学研究,1997(12).
[2]陈波.逻辑哲学引论[M].人民出版社,1990.289.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11
李商隐写了大量的“无题”诗,由于用典与含混的语词,使得诗的意境朦胧,意义丰富,理解多样。“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本来是传说中的人事,着一“迷”一“托”,使得“晓梦”“春心”更加凄迷奇幻,读之令人怅惘。本真意义上的诗歌往往通过语态的失衡来呈现诗人个体经验认识的极限性,诗的含混性让读者有了二度创作的欲望,有利于诗境的开拓、诗意的阐释、诗情的抒发。李小宁诗《隐喻》
手捧一万个小心,星星
点灯,点不亮我的领袖
怎能点亮我的胸襟
马首,所能回眸的狮身
蛇腰的美人,鱼
欲望的灯火愉快地领路
如果说“小心”(小小的心灵,小心点儿,小心眼儿)“点灯”(一点灯火,点点灯火,点亮灯火)等语汇多义,往往带有机械生发的味道,那么“领袖”(头领)常用的比喻义经过“胸襟”的拉扯,使其极力回到原始意义,但又不能够,便形成张力。“马首”(马首是瞻)“狮身”(狮身人面像)的组合,便有“斯芬克司”之谜的隐喻。“蛇腰的美人”(“美人鱼”),即“欲望”(“鱼”,即“欲”即“育”即“雨”);“领路”又还原了“领袖”“马首”等普遍的世俗意义。隐喻,则必然含混。
实用语言总是力图取消含混,或降低含混发生的机率,从而使意思变得明朗、确定、固定、唯一;而含混则是人对世界的歧义性理解。相对处于正统地位的本义来说,它是异端,它实际对语言与世界(名与实)共构的秩序造成威胁。名实共构,是指世界在语言下的规范和语言对世界的确认这二者共同构成的人类心理(集体无意识)的非自然状态。人类的教育过程总是从这一状态开始,以后一直伴随着这一状态,并不断使之得到加强。与名实共构相对的另一种状态,就是“无言”状态。它是人们在使用语言以前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一种纯粹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整体的、混沌的个体感觉(个体意识),是原认识。
因人们的误读而可能生成的语义,称为“误义”。利用误义,可以使语词本义的影响受到削弱,甚或可以使本义受到侵害而溃散,提高人们的误识、误解的几率,从而强化语言的诗意性表达的效果。
将一事物指示为另一事物,并通过强迫性思维让阅读者寻找两事物之间可能有的渊源,以期在它们之间建立全新的因果关系,称为“强指”。将两个或多个表面看来无甚关联,而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有着内在相关性的事物强制性地牵扯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定的联系。利用强指,可以于荒谬之间彻底颠覆词语本义;颠覆约定俗成的本义,使诗意的解读走上更为广阔的道路。
诗歌的解读,强调“随机”的解读。将解读的主动权完全交给读者,作者从作品中淡出,让语言“自语”。将表面看来无甚关联的词语抑或语句叠加在一起,以期产生奇妙的效果。当然这种随机是作者有意制造的,而不是一些所谓“先锋诗人”那样随意翻动词典胡乱组合的那种随机。作者是要创造一种在读者看来其诗句是随机组合的新异效果。“随机义”的创造,往往更可能导致整个名实共构的意义系统的崩溃,从而形成对“无言”状态的无限逼近,以期最大可能的接近心灵“混沌”的那个真实状况。
总之,含混、误义、强指和随机义都是旨在消解既定意义,复原深受集体无意识影响而自我戕害的个体感觉,使诗歌真正从作者的一厢情愿和图解式的写作中解放出来,尊重读者“个人”的阅读,尊重“人”的不同发现与体验,从而使诗歌真正走向“真实”。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权威和既有知识的挑战,是针对约定俗成意义的强有力的反叛。
诗歌创作本身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寻“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命“名”,一种寻道、命名的不可能的可能,是意义“在场”与“不在场”的双重可能,是“多义”和“含混”的无限可能……同时,诗歌创作也是本真生命的构建和彰显的最好方式。
诗歌语言的丰富性和含混性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培养创造能力。可以说,越是优秀的诗作,其激发人想象的空间就越大,读者也就在这样的被激发中尝到了阅读的快乐,从而培养了纯正的文学趣味。
混 沌
诗歌的“含混”是从表达的角度而言的,侧重于语言,也就是诗人的“言语”状态;“混沌”则是从内容的角度而言的,侧重于思想,也就是诗人的“意识”状态。
《庄子》有个“倏”“忽”为“浑沌”凿七窍的寓言,日凿一窍,第七日“浑沌”就死了。显然,人有七窍人就有了看清世界的欲望,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人根本是无法看清世界的,人的痛苦就在所难免。人痛苦的根源就在于人的欲望与理性追求之间的矛盾。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要人对抗人的此岸的现实存在,而去追求人的彼岸的精神存在,只能用诗的含混语言诠释隐藏于万物深处的神性――“存在之真”。“只有当诗发生和出场,栖居才会发生”(海德格尔语),这让我们看到了诗必须存在的理由。
诗歌意义的混沌性追求,恰好拯救了诗的生命。诗之生命,即展现人之生命本真的活动。人性之中最活跃最能动的部分应是潜意识,诗的使命就是要把最富生命力的东西挖掘出来,且要表达得鲜活,而不是清晰。顾城诗《远与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作者欲用含混的语言表达一个人生命内里的混沌的感觉。
其实,一个人立于世的模样,如同一扇窗户被打开的情状;心灵在混沌忙乱之隙,总有偷暇外窥的焦渴,此时所能见的野鹤闲云般的景象,总是那么让人感到亲切、美好。语言,特别是诗的语言,必须为混沌的心灵做件相称的嫁衣。李小宁诗《牵牛花》
嘴如露,眼似霞
柔软,蛇一样缠绵
无数脸盘,闪现
湿漉漉,花瓣
人对于美首先是一种混沌的直觉,由“牵牛花”之美到“美人”之美,这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跳跃。嘴,如“露”般玲珑剔透,谁人见之?眼,似“霞”般灿烂迷幻,亦非写真。“露”与“霞”既是美好易逝之物,“美人”也是,但此类物常招人怜惜。此诗看起来只是诗人一次真实地“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语)的“心动”(而不是“旗动”),但由于“花瓣”(庞德诗句“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的强制还原,不至于拟人化的混沌之美只停留在人事上,而使其表达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即“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移情。
《诗经・蒹葭》是一首很混沌的诗,不能像一般的诗评家那样,把它简单的归入“朦胧”一类。“古之写相思,未有过之《蒹葭》者。”相思之所谓者,望之而不可即,见之而不可求;虽辛劳求之,终不可得。于是幽幽情思,漾漾于文字之间。一个人混沌的情思,靠含混的语言暧昧地言语,以抵达生命的真实。
白居易诗不仅以语言浅近著称,其意境亦多清晰,意蕴亦多显露。不过,有首题为“花非花”(无题)的诗,却颇显“混沌”之味,于白氏诗中,确乎为一特例。白居易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诗首二句“花非花,雾非雾”,给人一种难以捉摸、飘忽不定的感觉。“夜半来,天明去”,则颇使读者疑心似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四字,则见又不然了,“梦”原来也是一比。“夜半来”者也,虽美却易逝去,便引出一问――“来如几多时”?“天明”见者朝霞也,霞虽美却易幻灭,则引出一叹――“去似朝云无觅处”!一连串比喻,谓之博喻。诗环环紧扣,如云行水流,自然成文;反复以鲜明的形象突出一个未曾说明的喻意。然而此诗只见喻体而不明本体,就如同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则使诗的意境蒙上一层“混沌”的色彩,不明了了。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的混沌主要体现在语言表情达意上的含混上。含混不是意象重叠,晦涩难懂,含混美是诗歌的理想艺术形态。含混与混沌之间没有壁垒森严的鸿沟,含混是由于言语的混乱,混沌则是因为心灵的暧昧。
现代诗,就“含混”这点而言,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作品内涵越丰富,其语言的弹性与张力就更大。由于作家的多意性追求,所表达思想时甚或会与传统相悖,理解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但是,只要不过于违背生命的真实,过多使用佶屈聱牙的语言,堆砌过于繁复的意象,在精神内涵上不是十分空乏,那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假如是“含混”得过了头,给读者领会作品造成一定的难度,难免会给人一种故弄玄虚的感觉。倘或如此,则对作品的艺术生命的延伸造成严重伤害,这不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则为诗歌指向“混沌”的生长提供了实质的现实环境。语言是一切文学的载体,诗歌借助语言而具有了飞翔的可能。诗人对语言驾驭的不确定性,也会让诗歌滋生出多重理解的含混。海德格尔说“诗作是从一种模糊的两义性来说话的”,这种“模糊的两义性”即“混沌”,海德格尔同时指出“但诗意的道说的这种多义性并不转化为不确定的歧义性”(《海德格尔――思想之路》)。也就是说,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并不是“松懈的不准确”,而是由组成这首诗的核心来决定这种多义性的延伸范围。它是自由的,但不是绝对自由,它必须遵循存在的规律。因此,从一个方面来说,诗歌含混的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了诗歌混沌美的魅力。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12
命题作文的题目都是指定的,在审题时,我们首先要找到题目中的核心词,对这个核心词进行品味揣摩。如果作文题目中的核心词是具体的事物,而这个事物因为太过具体反而让我们不知如何立意时,那么我们就要发挥联想和想象,把题目指向抽象的情感或精神。这就是所谓的“化实为虚”。
例如,作文题“必须跨过这道坎”,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出这个题目的核心词――“坎”。首先我们要弄清“坎”的含义,“坎”的本义是“坑,穴”。此时,如果我们就来写现实生活中的沟沟坎坎,那就显得肤浅了,文章难有深意。这时,我们就要发挥联想和想象,由现实中的沟沟坎坎联想到生活乃至人生中的沟沟坎坎,如学习的挫折、友情的挫败、人生的不幸等等。以此来立意,进行叙事、抒情,写出“坎”的象征意义,这样的文章立意才深刻,内容才动人,才能写出精彩!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化实为虚”的方法根据关键词发挥联想和想象来探究题目的比喻义时,不能脱离本义、胡思乱想,那就会让人不知所云了。
二、化虚为实
与前面的情况相反,有些寓意型命题作文题目中的核心词并不是具体的事物,而直接是抽象的精神或情感,比如“高尚”“卑鄙”“理智”“疯狂”等。如果就直接围绕这些精神情感来写又会失之空洞,给人“假大空”之感。此时,我们如果把这些抽象的精神情感具体化,通过实实在在的事情来表达这些抽象的精神情感,文章就会显得真实感人。这就是所谓的“化虚为实”。
例如,作文题“这,也是一种高贵”。在审题立意时,我们首先要抓住题目中的核心词――“高贵”,明确其含义。然后把抽象的含义具体化,结合题目“这,也是一种高贵”的意蕴,把高贵的精神寄托在一件真实感人的平凡小事上来写。这样下笔容易,写出来的文章也一定会更吸引人。
三、大题小做
有些寓意型命题作文的题目,核心词的含义比较宽泛,看起来很简单,觉得什么都可以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宽泛的词义落实到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度甚至某一点上,把大题目写小,写实。这就是所谓的“大题小做”。
例如,作文题“我想握住你的手”。题目中的“你”概念极其宽泛,可以说,除自身以外的大自然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你”。写作时要抓住其中一个方面,缩小写作范围,从小处着笔。比如,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经历设定“你”是某个让我们难忘的人,抓住相处中的一个细节表达“我想握住你的手”的意蕴,这样才会将文章写得立体饱满、真实感人。
四、小题大做
生命现象的含义篇13
1作为真实个体的存在与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
关于存在的涵义,粗略一看,似乎很简单,我们常说“某某存在”或“某物存在”,其意就是“有某某”或“有某物”。但仔细思考,可以看出,自然语言中所指的存在或存在物,是有不同的涵义或层次的。比如,在下列四个语句中,所讲的存在的涵义严格地说是不完全相同的:
(1)艾菲尔铁塔存在。
(2)动物存在。
(3)存在着大于3而小于7的质数。
(4)他的身上存在着一种高贵的气质。
在语句(1)中,存在的对象是“艾菲尔铁塔”,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个体,在语句(2)中,存在的对象是“动物”,即由各种各样的具体个体组成的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无法找到不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作为类的“动物”,在语句(3)中,存在的对象是数,即数学的对象,而在语句(4)中,存在的则是对象所具有的某种性质或属性,因此,这几种存在物是有别的。语句(1)中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真实的个体,语句(2)、(3)、(4)中所存在的对象则或是个体所组成的类即共相或是数学的对象或是对象的性质,我们统称为“抽象实体”。可见,存在或存在物是有不同的层次或类型的,事实上,如果从时间上来考虑的话,存在或存在物还可以有时间上的层次:过去的存在与现在的存在,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是过去的存在,当今美国总统布什的存在就是现在的存在。当然,出于研究的考虑,在本文我们忽略存在的这种时间层次上的差别。
关于存在问题,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何物存在”,即存在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一般地说,存在问题所涉及到的存在对象主要包括上述四类对象。就唯名论而言,他们只承认存在有个别的具体事物,即真实的个体,而不承认诸如类、数、关系、属性等所谓的“抽象实体”的存在。实在论或柏拉图主义者则承认抽象实体的存在,认为各种数学与集合论的对象以及属性、关系等均可以是存在的对象。
在存在问题上,注意到“存在”的不同类型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可以认为,唯名论所理解的存在是狭义的,按照这种理解,只有客观的个体对象才是存在的。而实在论则对存在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共相以及属性、关系、数等等都可以是存在物。从这一点出发,则可以推出,唯名论不承认思想中的对象的存在,而实在论则认为不仅客观现实中的对象是存在的,思想中的对象也是存在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个人认为,严格地说,存在问题及其争论主要是在唯名论的意义下出现。如果取实在论的观点,即承认各种不同层次的存在或存在物,则所谓的存在问题就不会出现。当然,尽管对存在或存在物可以区分出很多层次或类型,但是,从实用和简单原则出发,我认为,可以宏观地把存在分成两个层次或类型:现实中的真实的存在与思想中的存在。我们在分析存在语句时,只要注意对这两个层次进行区分,则所谓的存在难题就并非是难以解决的。
在存在问题的诸多难题中,其中之一就是梅农所谓的“金山存在”问题。按梅农的观点,当我们说“金山不存在”时,由于我们一般都预设了语句的主词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果金山不存在,那么“金山”这个词无意义,因而“金山不存在”这句话是无意义的,如果金山存在,那么“金山不存在”这句话就等于是说“存在的金山是不存在的”,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所以,“金山不存在”这句话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们不能说“金山不存在”,而只能说“金山存在”[1]。
可以看出,如果对“存在”只作唯名论意义下的理解,即只承认客观世界中真实个体的存在,那么,毫无疑问,梅农的这一“存在难题”确实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对“存在”作实在论意义下的理解,取“存在”之广义,即承认思想中的对象的存在,那么,梅农所谓的“金山不存在”问题则是可以解决的:在“金山不存在”这一语句或命题中,主词“金山”所意谓的存在是思想中的存在,而谓词“不存在”中所指的存在则是作为客观现实中的真实个体的存在,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存在,因此,主词所意谓的“存在”并不构成对谓词“不存在”的否定,这句话的真实涵义是:作为思想对象存在的金山在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金山”只是一种思想中的存在物,并不是客观现实中的真实个体)。在这种理解下,则不仅“金山不存在”之类的语句难题可以解决,即使像“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语句也是可以理解的:“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指思想中的对象,是人们思维中的存在物(谁能否认这种思想之物的存在呢?人们在思想中是可以想像该对象的存在的),而谓词的“不存在”则是指它作为客观真实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因此,这句话的实际涵义是: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物的“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在客观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
在存在的类型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要区分“可能世界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存在”,比如国内学者陈波与杜国平等都有此看法。例如,陈波认为:“自然语言中的存在语句大都相当于一个命题函项:a存在于W,这里的a是个体常项,W是世界变元(或场所变元),它的值域是由所有的可能世界组成的集合。当对这个函项中的惟一的不确定成份(变元)W代之以可能世界集合中的不同世界时,相应的存在语句就获得不同的真值:在W的一种赋值下为真,在另一种赋值下为假。例如,如果我把‘贾宝玉存在’理解为‘贾宝玉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该语句为假;但若把它理解为‘贾宝玉存在于《红楼梦》所描绘的可能世界中’,则该语句显然为真。”[2]杜国平先生也认为,“存在”是一个跨界谓词,即跨越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因此,要注意区分不同世界下的‘存在’”[3]。
将存在分成可能世界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存在,这一观点我是基本同意的,运用这一观点,也可以很清楚地消除“金山不存在”之类语句的难题:在可能世界W中(可能)存在的金山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可能世界”是一个逻辑学概念,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在“可能世界”中不允许逻辑矛盾的出现,所以,对于“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语句,即使用跨界存在理论也无法解决,因为,“又圆又方”是一逻辑矛盾,从逻辑学的观点看,这种逻辑矛盾即使在可能世界中也不应存在[4]。
正是由于运用“可能世界”概念也不能完全解决存在难题,所以,我认为,不妨撇开“可能世界”这一概念,将存在分成“作为客观现实的真实个体的存在”与“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由于在“作为思想对象的存在”中,思想对象即思维中的产物,因此,即使它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允许的,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它只能存在于思想中而无法存在于客观现实中。
2隐含的存在与明示的存在
对于“金山不存在”或“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不存在的”之类的“存在难题”,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是试图将存在作“真实个体的存在”与“思想对象的存在”之分来解决的。对于这种解决方式,有人可能不同意,即不同意将存在取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倾向于唯名论意义下的存在。那么,下面我们要考虑的是,如果取唯名论意义下的狭义的存在,即 认为存在只是真实个体的存在的话,我们怎样解决上述的“存在难题”呢?
存在问题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主词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在现代逻辑哲学中的表述就是:在形如“S是P”或“S不是P”之类的命题或语句中,S作为命题或语句的述说对象(即主词),是被预先假定为“存在”的,这也就是说,一旦某人作出“S是(不是)P”之类的命题或语句,他就认定了S是存在的。也正是由于这个主词存在的预设,就导致了“金山不存在”之类的“存在难题”:在形如“S是不存在的”之类的命题或语句中,一方面该命题或语句本身预设了主词S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命题或语句的谓词又指出了S是不存在的,因此,“S是不存在的”就等于说“那个存在的S是不存在的”。
要在取“存在”之狭义即在唯名论所指的存在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将存在区分为“隐含的存在”与“明示的存在”。
我认为,任何一个形如“S是(不是)P”之类的命题或语句都预设了主词S的存在,这种意义下的存在是通过语法或语义蕴涵“隐含地”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把这种意义下的存在谓之命题或语句的“字里之意”或“潜在之意”,它所谓的“存在”是一种“隐含的存在”。而在“S是存在的”或“S是不存在的”中作为语法谓词所明确宣称的“存在”或“不存在”,则是命题或语句本身明确地显示的,因此,这种意义下的存在我们谓之“明示的存在”,它属于命题或语句本身的“字面之意”。从逻辑层次来说,在一个命题或语句中,“明示的存在”要强于“隐含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命题或语句中,其隐含的存在与明示的存在并不矛盾,那么隐含的存在就可以上升为明示的存在,即由“隐”变“显”,比如在语句“小张考上了大学”、“史密斯先生出去旅游了”中,都有“小张存在”或“存在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之类的隐含存在,由于它们与语句本身的明示之意不相矛盾,因此,这些隐含的存在是合理的,可以由“隐”变“显”。反之,如果在一个命题或语句中,既有隐含的存在,也有明示的存在,且两者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明示的存在要强于隐含的存在,于是,明示的存在就自动地消除了隐含的存在,整个语句便只包括“明示的存在”之意。例如,在“孙悟空是不存在的”这一语句中,主词预设了“孙悟空是存在的”,但语法谓词“不存在的”则明示了孙悟空的不存在,在这里,隐含的存在与明示的存在发生了矛盾,因此,明示的存在就自动地消除了隐含的存在,这样,整个语句的意思就是“孙悟空是不存在的”而不是“那个存在的孙悟空是不存在的”。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解决“金山不存在”与“伯克利学院的又圆又方的屋顶是不存在的”之类的难题。
这也就是说,作为命题或语句的字里之意的“隐含的存在”与作为命题或语句的字面之意的“明示的存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存在,一旦在命题或语句中两者发生冲突,则明示的存在就自动地消除了隐含的存在,这样,整个命题或语句就以明示的存在为准。
在对存在作“隐含的”与“明示的”之分这一点上,逻辑学家盖士达的“潜预设”(Pre-Supposition)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是有助的。按盖士达的观点,所谓一个语句的潜预设,是指该语句所具有的潜在的、可能的预设,它是一个句子从语义上分析而得到的预设。一个语句的潜预设如果与该语句的特定的语境相一致,则它就显现出来,成为实际的预设,反之,如果它与该语句的特定的语境相矛盾,则它就被该语境消去而不复存在了。例如,相对于语句“小王用不
更多精品:3edu文书更多精品:3edu文书
着戒烟,因为事实上小王从没有抽过烟”,尽管“小王用不着戒烟”有预设“小王曾抽过烟”,但由于它与后面的语句相矛盾,所以,后面的语句“因为小王从没有抽过烟”就自动消去了这个预设,因此,这只是一个已被消去的潜预设[5]。可见,按盖士达的观点,对语句的潜预设的设定只是语义上的分析,而该潜预设在具体的语境中能否显现出来,则是一个语用问题。套用盖士达的这一说法,我认为,我们也可以说,隐含的存在只是一个语义上的问题,而它能否变成明示的存在则是一个语用问题。
3传统逻辑的存在与现代逻辑的存在
存在问题并非现代逻辑的产物,实际上,在传统逻辑的性质命题中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主词存在问题”。
我们知道,在性质命题中,同一素材的四种命题A、E、I、O之间具有真假之间的可推导关系: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矛盾关系、差等关系。根据这些关系,我们便可以在四种命题间进行推导,比如,由A命题的真,可以推知E命题为假,由0命题的假可以推知A命题的真,等等。这种同一素材的A、E、I、O之间的真假关系,也叫对当方阵。但是,这种推导关系有时会出现问题。例如,根据差等关系,由SAP的真可以推出SIP一定真,可是,当我们由“所有的金山都是金子做成的”推出“有的金山是金子做成的”时,我们就发现,这种推理并非是保真的,因为,在这个推理中,前提“所有的金山都是金子做成的”无疑是真的(即使并不存在现实的金山),但结论“有的金山是金子做成的”却是假的,因为后者是一个特称命题,也叫存在命题,其意为:至少存在一座金山是金子做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逻辑对根据对当方阵所进行的推理有一个要求,即性质命题的主词必须被假定是存在的,如果不假定主词是存在的,则从全称到特称的推理就不是保真的。
因此,传统逻辑在推理中引入了本体论的假定,它要求主词都必须是存在的。而事实上,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这种假定是错误的。所以,现代逻辑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解。我认为,现代逻辑对存在问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现代逻辑对传统的性质命题作了更为精确的分析。就传统逻辑来看,性质命题都是主谓形式,它们所断定的是普通名词之间存在的关系,因此,传统逻辑认为,全称命题A与特称命题I的区别只是主词的周延情况不同,即前者的主词是周延的而后者不周延,除此之外,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这一观点,现代逻辑并不同意,现代逻辑认为,全称命题A与特称命题I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于主词的存在并没有作断定,而后者则对于主词的存在作了明显的断定,因为,全称命题是一个假言命题,而特称命题是一个存在命题。这也就是说,全称命题“所有S都是P”的真实涵义是:对于所有的个体x,如果x是S,那么x是P,用公式可以表示为:。而特称命题“有的S是P”的真实涵义则是:至少存在一个个体x,x是S并且x是P,用公式可以表示为:。通过现代逻辑的这一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主词并不存的情况下,全称命题仍然是真的,而特称命题则是假的,因此,在现代逻辑中,SAPSIP的推理是无效的。
第二,在“存在是不是一个谓词”这一问题上,现代逻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针对“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康德提出,“存在”不是一种性质,因此,它不是一个谓词,随后,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逻辑学家与哲学家的赞同,弗雷格、罗素、斯特劳逊、摩尔、赖尔、艾耶尔、奎因等都持相同观点。按他们的观点,尽管“棕色的牛是存在的”与“棕色的牛是健壮的”这两个句子形式相同,即“存在的”与“健壮的”都出现在谓语位置上,因而从形式上看两者都是谓词,但实际上,语句中的“存在”是可以等值地消去的,因为,“棕色的牛是存在的”可以等值地转换为“有的牛是棕色的”,而“棕色的牛是健壮的”中的“健壮的”却不能被等值地消去。因此,“存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逻辑谓词而是一个量词,存在语句实际上是一个量词语句,所以,可以用现代逻辑的量词理论来处理存在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