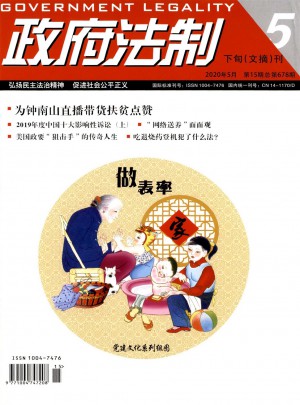篇1
但是,经济法理论的研究现状却是:一系列基本的范畴尚未完全建立,学者对某些基本的理论尚无暇顾及,以至于经济法学上有关“行为理论”的园地尚很荒芜,从而影响了经济法学的成熟、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如何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来研究相关的行为理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入口和思考线索。
考虑到经济法学上各种具体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曾以前辈学者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重“二分”,使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得以形成(这并非刻意的设计)。如在体系上把经济法规范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在主体上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宏观调控法上的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以及市场规制法上的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等等。(注:这种“二分法”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对此我在《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曾经有所揭示。由于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涉及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政府与市尝公平与效率等多个方面,因而在各个方面都会形成一种“二元结构”。这是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假设。经济法究竟是应存在于该“二元”框架中,还是应当对其予以突破,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了研究上的便利,在此可把经济法的主体进行再概括,即把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合称为“调制主体”,把受控主体和受制主体合称为“调制受体”。
与上述经济法主体的分类相对应,本文把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分成两大类,即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或简称为调制行为和市场行为。其中,前者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行为,而后者则是调制受体(即实际上的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基于经济法的特殊性,以及调制行为的特殊重要地位,本文拟在后面的几个部分着重探讨有关调制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
要有效地探讨调制行为问题,还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从研究方法来看,如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等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假设一样,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方法、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的方法、演进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法、干预主义与非干预主义方法等诸多“二分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方法论上的“二分法”都是虚假和误导他人的,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不可能严格地处于某一方面而与另一方面相对立,事实上,许多社会理论家采取的恰恰是较为中庸温和的立场,并开辟了方法论上的“中间道路”。(注:卢瑟福提及的著名学者阿加西(Agassi)关于吸纳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的论述,可参见J.Agassi,InstitutionalIndividualism,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26(June),1975,P154.)[2](P6、46)从现实的研究需要来看,综合各种方法的可取之处确实是必要的。因此,结合经济法学本身的研究特点,在研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时,同样要注意各种方法论的可取之处。例如,不仅要注意整体主义的方法,也要考虑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而不仅可以看到法律制度、国家调制对个人的影响,也能看到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变迁,特别是对于国家调制的目标与手段的影响。
此外,不仅综合各种重要方法论的优长是必要的,而且结合论题,确定较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很必要。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各类调制主体所采行的调制行为,且这方面的抽象、概括还很不够,因而本文需要更加注意规范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新兴的、受大陆法系思想影响较深的经济法学的现实理论发展,也许更加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及对研究方法的考虑,本文选择有关调制行为的如下几个问题着重进行探讨:为什么要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它与经济法的职能有何联系?如何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认识调制行为的地位?调制行为有那些构成要素以及如何判断其合法性?
二、“调制行为”概念的提出及其与经济法职能的联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已经越来越注意运用一系列法律化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手段来影响经济运行,规范市场秩序。例如,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问题,国家非常重视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转移支付、利率调整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其中,七次大幅度调低利率(注:开征利息税,具有变相降息的效应,这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如果算上利息税的恢复开征,则在近几年内,我国已八次降息。与此同时,我国还两次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以期影响货币供应量。)、多次大幅度调低关税税率年4月,我国曾降低了4900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从而使我国的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23%;1997年10月再次降低了4874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使我国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又降至17%;而1999年和2000年,为了加入WTO,我国又主动调整了一些商品的关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了我国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调高出口退税率(注:出口退税率本来应当贯彻“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但由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出现了大量骗税等特殊情况,因而国家曾在1995年两次决定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这是重要的调制行为。但其后果却是对出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刺激出口,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较高增长率,也同时保护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我国近两年多次调高一些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开征利息税、增发国债(注:近几年,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大幅度提高,国家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2000年中央赤字为2299亿,国债发行总规模为4380亿,这样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调控的行为是否合适,规模是否过大,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等宏观调控行为,已经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国家所实施的各类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其他市场规制行为(注:如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地位的调整,对民航业“机票打折”问题的态度,对某些家电行业的降价浪潮的规制,对于某些商品出口的竟相压价的规制,等等,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究竟在法律上应如何看待,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如何,是否侵犯国民的权利,是否构成对市场行为的不当干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但整个法学界却未能给予充分注意。由于上述问题与经济法的调整密切相关,因而经济法学者应担负起研究的重任,更何况对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展开深入研究,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理论研究的需要来看,有关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难垦之地”,同时,与其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如经济法上的可诉性问题、经济法的“自足性”问题,以及整体上的“现代性”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很难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缺失密切相关。经济法学如果不能在行为理论上有所突破,则许多相关理论的研究就很难拓展。因此,有必要对大量的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进行抽象和概括,以形成类似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之类的重要概念(注:民法学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研究远比对“民事行为”的研究要多。“法律行为”作为德国学者的重要创造,给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行政行为”这一术语作为德国行政法的奠基人奥托·梅耶(OttoMayer)的贡献,也对行政法学的学科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同上述术语一样,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方面,同样也需要提出一些重要概念,并由各个方面的学者共同作出深入探讨。),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
在经济法理论上,经济法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能径称为“经济行为”,是因为“经济”一词词义较多,且外延往往较大,容易造成歧义和混淆。因此,必须在对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复杂行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概括和提出新的范畴。如前所述,基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我把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和规制行为统称为调制行为,并认为它像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一样重要。
为了明确何谓调制行为,不妨对其作出下列大略的界定: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亦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由于调制行为是经济法主体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而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因而其全称应当是经济调制行为。此外,在上述界定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不同层次调制行为的手段和目标。
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是因为它是经济法学者应予以关注的一类特殊行为,并且,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和制度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调制行为的一些特质及其成因也须注意。由于各个部门法都有自己的宗旨、职能、任务,因而各个部门法在调整对象、法域、价值取向、调整手段、权义结构、责任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其中,调制行为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的差别就更是巨大(这实际上也是认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区别与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说,上述三类行为的区别至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的主体不同。民事行为的主体是各类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主要是行使行政权的各类行政机关;而调制行为的主体则是享有调控权和规制权的宏观调控部门和市场规制部门(未必是行政机关,更不是全部行政机关)。
2.行为的权源不同。合法的行为,必须有正当的权源,即必须有相应的权利/权力依据。民事行为的合法性,与民法所确定的民事权利相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行政法所确定的行政权力相关联;而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则与经济法所确定的调制权(包括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相关联。
3.行为的性质不同。由于行为的主体不同、行为的权力/权利保障不同,相应地,行为的性质也不同。民事行为具有平等性,行政行为具有隶属性,或称命令-服从性;而调制行为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不完全的平等性和不完全的命令-服从性。调制行为之所以会存在,之所以会与相关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有所不同,主要是导因于经济法的特殊宗旨和职能。事实上,调制行为的实施正是实现经济法职能的需要。从经济法理论上的“机能说”来看,经济法之所以会存在并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法有着特殊的职能。(注:德国学者彼姆(F.B附图mu)和林克(Rinck)等强调经济法在“经济统制”方面的独特机能和功用的观点,被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概括为“机能说”。尽管这些学者的经济法理论尚可商榷,但能够认识到经济法有其独特的机能,则是较为可取的。)从经济法的宗旨出发,以及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来看,经济法最主要的职能和任务就是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使“调制行为”的概念得以提出,并使其成为经济
法需加规范的一类重要行为。因此,深入研究经济法的职能或称机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具体职能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等“二元结构”中,经济法是联系“公”与“私”的桥梁,它就像调制解调器一样,要把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的信息信号进行转换,把国家的制度供给信息传递给私人经济。同时,经济法也需要通过自身的调整,把市场主体的需求信息带给国家(或称政府)。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调整是在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转移和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国家正是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自己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目标,而在调整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信号转换,则调整的实效必然欠佳。
在职能方面,经济法不仅是“调制解调器”,同时也是“内在稳定器”。而之所以能够实现“内在稳定”,是因为经济法的调整有助于达到“整体协调”的效果。事实上,调制是经济法调整的手段,而其目标则是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状态。因为只有达到这种状态,系统才是稳定的,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类主体的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由于调制行为直接体现着经济法的“调制解调器”和“内在稳定器”功能,因而必然在经济法主体的诸多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需加研究和重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三、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在经济法的行为理论研究中应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也因为它是经济法的立法中心与执法重心,从而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明确调制行为的重要地位,更有助于说明研究调制行为的重要性。
1.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从行为结构上看,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虽然在总体上包括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两类,但前者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这与调制主体及其调制权的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事实上,调制受体的行为,主要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它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博弈,也不同于通常的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遵从,而是针对国家调制所做出的遵从或不遵从的选择;调制受体一般要比民法主体的选择余地小,而比行政相对人的选择余地大。
其实,与调制行为相对应的市场对策行为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它同样是在经济法理论上创设的概念,可用来揭示调制受体针对国家的调制行为所从事的对策行为。例如,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来进行市场规制,都属于调制行为。当国家财税部门调整税率和税收优惠措施,金融部门调整利率、汇率,计划部门调整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以进行宏观调控时,相应的受控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求趋利避害,这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同样,如果国家的有关部门根据市场竞争的情况,加强或放松市场规制,则市场主体同样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使自己的利益损失最小化。这也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
可见,市场对策行为的采行,是以经济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的,是调制受体针对调制行为所进行的博弈活动。如果没有调制行为,则针对调制行为的市场对策行为就无从发生,从而使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得以成为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一对范畴。事实上,不仅存在着针对国家调制行为的纵向对策行为,而且也存在着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对策行为。其中,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市场对策行为,不仅侵害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社会公益,因而是经济法重要的规制对象。
由于经济调制行为,决定了经济法意义上的市场对策行为的对立存在,并且,个别的市场对策行为相对于政府的调制行为是很弱小的(这并不是忽视市场主体对策行为的整体力量),因而经济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必然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并使两类行为之间存在主从性、不对等性。其中,不对等性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
2.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与市场对策行为的对比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法制建设领域,特别是在立法、执法,以及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上。事实上,经济法需着力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等问题;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力所不及的,因此国家的调制非常必要。但由于人类理性存在局限,国家的调制未必尽如人意,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因而如何做到“调制适度”,如何把调制行为纳入制度或法律的轨道,使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在立法上,一方面,为了解决经济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大量地规定有关政府调制的问题,从而形成经济法所特有的调控和规制的手段,并进而确立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调制行为的权源、效力、实施程序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使调制行为也受到法律的制约。而这两个方面,都会使有关调制行为的规定成为经济法立法上的中心,从而也成为执法上的重心。
调制行为作为立法上需要规范的“核心标的”,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上都有体现。例如,在财税法上,首先要规定从事财税调制行为的主体及其职权分配,规定行使财税调制行为的要件(如课税要素、预算收支的基本原则等)等;在金融法上要规定从事金融调制行为的主体,以及如何运用法律化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等;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要规定执法主体,以及规制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件、程序等。事实上,各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都是围绕着相关主体的调制权以及相应的调制行为而展开的。
调制主体所从事的
具体调制行为繁多,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与经济法作用领域的广泛性相关,同时也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手段的多样性有关。通常,调制主体都在从事一系列重要的调制行为,在宏观领域如预算收支调整行为、税目与税率的调整行为、税收优惠或税收重课行为、国债发行与收买的额度调整行为、转移支付行为;银行利率与汇率的调整、存款准备金与再贴现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行为等;在微观领域如对非法卡特尔、滥用市场经济力等垄断行为的禁止,对在价格、质量、信息等方面影响市场秩序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划,等等。上述典型的调制行为,不仅是经济法立法的中心,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执法的的重心。惟有摆正它们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总体上的“经济宪法”作用。(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高度重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用,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宪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观念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在各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谈到法律在整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时,已经越来越不能忽视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和作用了。因此,在此强调要在“总体上”发挥它们的作用。)
可见,无论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还是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调制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确保其合法性,如何确保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以真正达到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协调”状态,则是更为重要的。因此,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
四、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合法性
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即构成调制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或称要素。对于个别的调制行为,在经济法学的某些分支学科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在税法学上,对于课税要素等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尚未发现有人从总体上来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从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入手,不仅有助于调制行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从理论上解决经济法研究方面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微观上说调制行为如果不具备应有的要件,则调制行为就不能独立存在,从而不涉及合法性、效力等问题,也谈不到对于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益如何均衡保护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再研究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效力等问题。
1.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调制行为作为经济法主体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类行为,其实施主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调制主体,从而使调制行为在各类主体的行为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Lloyd)曾指出,行为总是发生在关系、规则、角色和阶级的结构之内(注:在对人类行为的认识上,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指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结构主义”,强调要认识到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各自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参见前注引卢瑟福著,第45页。),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行为与一定的社会角色及其按照一定的规则所确立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关,因而在研究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时,也应考虑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
基于上述考虑,不难发现,一种行为的构成,从角色的维度说,涉及到行为的主体、客体(在此指一种相对被动的主体),这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此外,还必须有主体针对客体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如法律或其他规范),也可能不考虑任何规则,并使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一种关联,形成一种关系。基于上述认识,可以把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要素调制行为所涉及的主体,主要是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其中,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是享有调制权的经济法主体。通常享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主要是财税部门、中央银行、计划部门等;享有市场规制权的主体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如公平交易委员会等。这些机构虽然有些本身也是行政机关,但由于在调制方面行使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而非传统的行政职能,因此,与行政行为的主体还有所不同。
从主体要素来看,调制行为离不开调制主体,即拥有调制权的主体;不具有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就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同时也要看到,如果没有调制受体,调制行为就是无的放矢。通常,调制受体主要是不特定的从事市场交易行为的主体(但未必都是纯粹的市场主体)。
(2)行动要素调制行为的发生,不仅要有调制主体,还必须有主体运用其调制权的活动或称行动。并且,行使调制权的行为应当公示,以为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所知晓,从而使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发生联系,并形成其间的博弈。
从行动要素来看,调制主体必须履行其调制职能,审时度势,调控规制。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有为”,也可以“无为”,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要基于调控的需要。而不能怠于行使调制职权。不行使调制职权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如果对采取的调制措施秘而不宣,使调制受体无法知晓,则也不能构成调制行为。
(3)关联要素单有主体和行动要素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行动可以归属于具有调制权的主体,即调制主体与调制活动存在直接的关联;同时,还必须使调制活动与调制受体存在关联,从而形成两类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样,调制行为才能够真正确立,才有自己的独立意义和价值。
关联要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一般可能认为有了主体和行动的要素已经足够,或者把这一要素隐含在上述要素之中。其实,这一要素有时恰恰很重要。例如,税法上的征税行为是一种调制行为,该行为就需要与纳税人发生关联。当纳税人规避税法,致使“调制行为落空”时,就应依据税法上的“实质课税原则”,找到实际应承担税负的主体。为此,德国和日本等国学者曾主张,应当把“课税对象的归属”(Zurechnung)也作为一个课税要素[3](P109),以使国家的调制更加有效和准确。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主体与客体“联系”的
重要性,因为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真正能够确定征税的具体范围。
上述要素只是作为调制行为所应具有的一般要件,仅与之相符未必就是合法的调制行为或称调制法律行为。因此,还需进一步探讨调制行为的合法要件。
2.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实施调制行为是现代国家主体角色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因而下面仅从法律意义上来分析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要件。
调制行为有多种分类,但首先可以分为合法调制行为和非法调制行为,这种分类暗含着研究合法调制行为的必要性。根据调制行为的特点,可以将合法调制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概括如下:
(1)主体合格即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必须享有调制权,无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属于调制行为,当然也不是合法调制行为。事实上,享有调制权的国家机关并不多,许多国家机关,特别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是无权从事调制行为的。
(2)权源合法调制权的来源合法,是指调制主体的调制权,或者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经由合法的授权;所行使的调制权,不是超越自己应有权限的权力,也不是被溢用的权力。权源合法是调制行为合法的重要基矗
(3)调制合法包括调制的内容、调制的程序或称形式都要合法,即调制要充分认清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与相关的社会问题,尊重规律,审时度势,适度调制;同时,在调制的具体程序或应有的形式上,也都必须要注意,以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平衡私人利益。上述的“合法”,不仅包括符合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包括要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宗旨。(注:经济法的宗旨是与经济法所欲解决的基本问题(如市场失灵问题)、所需协调的基本矛盾(如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直接相关的。正是由于该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我曾专门对其进行探讨(拙文《略论经济法的宗旨》,载于《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此后又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并越来越认识到宗旨对于确保调制合法的重要。)
以上各项合法要件,直接影响到调制行为的效力,影响到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因而非常重要。在合法要件的约束下,如果调制受体不遵从合法的调制行为,则可能要承担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如果调制行为违法,并给调制受体造成了损害,则调制主体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经济法上的责任。
除上述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以外,调制行为的效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调制行为可分为有约束力的调制行为和无约束力的调制行为,但一般都具有公定力和确信力,同时,许多调制行为也都有拘束力以及执行力。
调制行为的公定力,是一种使社会公众对调制行为予以概括肯定并遵从的效力。作为对世的效力,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即应被概括地推定为合法,调制受体必须予以承认,这是确保调制的效率与秩序的需要。当然,如果调制行为因违法而无效或失效,则不应维持其公定力。
调制行为的确定力,实际上是对于已生效的调制行为不得任意改变的效力。其中,作出调制行为的调制主体,必须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调制约定(调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契约行为),否则就可能损害调制受体的“信赖利益”。作为调制受体,一旦接受了调制条件,也不能任意改变,否则国家的调制将无任何权威可言。同样,上述的确定力也是以调制行为具有合法性为前提的,违法的调制行为当然不具有“不可争力”。
调制行为的拘束力,亦即已生效的调制行为对相关主体所具有的约束力和限制力。从调制受体的角度说,由于现代国家越来越注意采取间接的调制行为,因而调制受体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通常,对于国家的调制条件,如税率、利率等,调制受体无权改变,这也是上述调制行为确定力的体现;但与此同时,调制行为的拘束力却受到限制。由于调制受体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行为的方式来回避国家的调制,因而若其未接受调制条件,则不能对其产生拘束力。
调制行为的执行力,主要是为确保调制目标实现而要求调制受体遵从调制行为的效力。其实,执行力与调制力一样,都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注:根据王绍光、胡鞍钢的研究,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调控的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执行力。参见王绍兴、胡鞍钢著:《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如果调制受体不能自动遵行国家的调制行为,则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这种执行力,同对调制受体的救济措施的执行,有很大的不同。因而有的学者将两者相等同是不妥当的。(注:与此相类似,在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执行力应同样针对行政机关。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以及〔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等等。)
调制行为的上述四个方面的效力,是合法的调制行为应有的外部效应的体现。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就相对地独立于相关主体并对其产生约束。
五、结论
篇2
论文摘要:国际法和其他国内法一样,同为法律,均具有强制性,都是必须遵守执行的。虽然二者的强制实施方法有所不同,但法律本身的强制力并无强弱之分。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法强制的有关内在因素趋于完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守与执行。 关键词:法律性;强制性;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有关国际法强制性的相关理论论述 国际法究竟是否具有强制性,是每一个不熟悉国际法或者初学国际法的人都会产生的疑问。即便在学界中,对于国际法强制性问题仍然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要认清其强制性的问题,必须首先从国际法究竟是不是法律这个问题人手进行探讨。 (一)否定国际法法律性的理论学说 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状态学说 按照霍氏的理论,各主权国家不是共同处于有组织的国际社会中,而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在自然状态中,主权国家都尽力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和权力并保全自己的生存,而很少顾及到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权力和生存。因此国际间既不实行道德规则,也不实行法律规则,而实行着调节一些物质力量相互关系的自然法则。 2.奥斯汀的国际道德说 奥斯汀是英国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他将法定义为主权者作出并予以强制执行的命令。由于国际法不符合他对法的定义,因此,他只认为国际法是“实定的国际道德”。 3.耶利内克等人提出的主权自限说 他们认为主权国家的意志决定其在什么范围内在法律上受到限制。即使在主权国家缔结条约以后,由于条约所产生的“法”总是仍然处在主权国家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国家可以在必要时单方解除条约,从而使条约义务消灭。这样,主权自限学说否定了国家之间存在着任何法律拘束力,从而会导致在国际往来中毫无法律安全的结果。 (二)国际法具有法律性 依笔者看来,既然有社会,就有法律,国内如此,国际也如此。因此,只要有国际社会的存在,就有国际法的存在,国际法就是法律。奥本海先生就是从这个观点来论证的,他认为法律存在的主要条件有三:第一,必须有一个社会;第二,在这个社会必须有一套人类行为的规则;第三,必须有这个社会的共同同意,认为这些规则应由外力来强制执行。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普遍性的国际社会内部实际上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各国之间的行为规则,而这些行为规则于必要时是由外力强制执行的。因此,国际法是法律。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制执行的外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像国内法那样的强制执行的外力。如果那样,国际法就不成为国际法,而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的世界法了。这样的世界法现在没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国际法是法律,而因为是真正的法律,所以它是有强制性的。我们将在下文中对该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二、国际法具有强制性的具体理论分析 在时下,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国际法无强制性,其主要理论依据在于:第一,国际社会显然没有也不应该有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强制机关。国际法在立法、行政、司法上的效能明显弱于国内法,因而国际法无强制性。另外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由于在各国政府之上还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能够在一切情形下确保国际法规则的强制执行,因此,与国内法的强制执行所可以利用的方法相比较,国际法无强制性。 (一)从“社会合意”理论看国际法的强制性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西方法理学家们更多地从“同意”或“默许”而非“制裁”的角度去看待法律现象,这就是推动当代西方法理学变革的“社会合意”理论(Social Consensus)。该理论指出,人们遵守法律主要并非由于他们慑于制裁机关的权威,而是由于他们同意至少是默许法律的实施与运行。反之,法律制度能够发挥其功能也正是主要基于这种同意,而非强制力的威胁与恐吓。 社会合意理论在国际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法主体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及相关事宜方面已经达成了广泛、普遍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社会各成员基于共同价值取向,积极主动地接受其同意或认可的国际法规则的指引并以其作为评价他人行为的基础或标准,这种共同利益和基本价值的内在驱动比武力强制和法律制裁作用领域更广,发挥的作用更直接、更有效。因此,我们说国际法具有强制性,并且其强制性有别于国内法的强制性。 (二)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异同看国际法的强制性 认为国际法无强制性的学者实质上是以国内法强制执行方式的特点为标准去衡量国际法。笔者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法律主体、制订方式效力范围尤其是强制执行方式上彼此迥异的两个法律体系。究其根源,我们可以从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到答案。 国内社会是以国家为最高权威的,由自然人和法人为成员而构成的一种纵向的“宝塔式”社会,而运用国际法的国际社会则主要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是一个高度分权的横向的“平行式”社会。作为法律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结构差异必然在法律调整中得到反映。正如李浩培教授所指出的,国际社会的法是并列法,而不是从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结构在逻辑上的当然结果。他进一步指出,早期的国际法主要是共处法。随着互赖的增加,就产生了合作法。显然,有“合作法”之称的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力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横向的,确切来说是一种“合力”。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随着科学技术、交通、通讯事业的迅猛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内管辖事项溢出国界,有些甚至唯有通过国际互助合作才能解决。而且,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越发达,这种寻求合作的愿望就越强烈。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各国基于各自的主权利益、文化差异、民族传统不会完全融为一体,但在经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合作和依存日益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需要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很难说这种国际社会的“合力”会比“宝塔式”的国内社会所产生的“压力”要小。可见,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力不仅存在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三)从现今国际法律实践看国际法的强制性 首先,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在其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它不但要求一切成员国家严格执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调整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而且通过组织措施行动,加强对成员国义务、责任的监督执行和惩罚机制,使各个成员国在自己的国内法体系之外又要遵循普遍的国际法规则,协调各自的行动。 其次,国际法院和其他区域性专门法院的成立,提高了国际法执行和实施方面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是现行极具广泛管辖权、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司法机关,它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日益强大的作用。此外,区域性法院如欧洲联盟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等司法机构都具有 自身的管辖权,是相关国际法规强有力的执行机关。这些法院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国际法在执行与实施方面的强制性与权威性。 再次,国际法的系统化与法典化。基于国际社会一体化对法制的需要,国际法的领域不断扩展,内容更加细化具体。国际法许多原则已逐步具体化,并由此发展成为国际法的一系列新领域,如国际组织法、国际环境保护法等。与此同时,为达到国际法规则的稳定与明确,国际法的法典化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联合国以及专门性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国际法编纂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使国际法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加强。 最后,国际刑法的发展使国际法的强制性特征得到了最为突出的表现。1998年在罗马外交会议上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按规约设立的刑事法院对规约所列的罪行享有普遍性管辖权,对许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大帮助;2003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生效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顺利通过又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公约的出现在诸多方面体现和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显示了国际法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法强制性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法产生于17世纪,以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标志,距今不到四百年的历史。与国内法相比,它是相当年轻的法律部门。对此,我们应该承认,传统国际法呈现出的“原始性”是国际法在其不完善阶段的必然表现。这种原始性集中体现在传统国际法中武力自助、自行裁决、自动解释等方面。时至今日,国际法的原始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相互频繁往来的必要性和战争的残酷性使人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需要相互合作和团体的努力,这就使得当今的国际法强制制裁体系亦随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而趋向制度化和多样化。 而众多国际组织的兴起也为国际法的强制体系添枝加叶。1995年1月,对国际贸易新秩序有重大影响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其争端解决机制是有一定强制性的。首先,对有关上诉机构的规定。尽管上诉机构的管辖权具有严格的限定,其结论报告不是一种真正的司法机关的裁决,但是它的复审结论,一经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争端当事方应无条件予以接受。其次,在裁决或建议的执行方面建立了一套监督程序。并在裁定和建议未在合理期间执行时,有关机构可以授权有关补偿和中止减让的贸易报复措施来保证其实施。 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性组织,欧盟对国际法的强制执行方式更有了新的发展。欧盟法律体系以欧盟法优先和直接适用原则,并以欧盟法院的判例为保障。在一定条件下,欧盟法直接为个人创设权利和义务,他们可以据此在国内法院进行诉讼,要求国内法院保护他们的权利,并在欧盟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优于国内法适用。 四、结语 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可以看得到的强制执行国际法的制裁体系正在形成,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国际法强制力的有关内在因素的完善,已使得国际法得到了更有效的遵行。国际法的强制力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并处在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之中。 不可否认,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中,霸权和强权肆虐,但国际法律秩序被严重破坏的同时也是重新构建更有效的国际法律新秩序之契机。因此,认识和澄清国际法的强制性对正确看待国际违法行为以及努力地去进一步完善国际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篇3
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列举生活中真实的事例,让学生充分讨论,透过实例,掌握法律知识。例如,我利用《法在我们身边》这一课的事例:我们社区有一个叫玉娟的同学,今年11岁,父母下岗后,家庭生活困难,因此,家里的人不打算让她上学,要让她到大伯开的饭店里打工。让学生讨论后说出自己的看法。首先,我问学生: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玉娟的父母让孩子辍学打工这种做法对吗?孩子们都说不对,玉娟应该上学读书,但是,至于为什么不对,孩子们就说不上来了,于是我就相机给孩子出示有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玉娟的父母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其次,玉娟的大伯也违反了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规定: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这样一说,孩子们都明白了自己原来享有如此重要的权利。就这样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法律知识深入到每个学生的心里,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篇4
由于日本现行司法体制受美国法律文化和制度影响最深,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不仅大量引进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制度和原则,让国民参与司法,并在具体制度层面上增设了多种民众参与司法过程的途径,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制度中对于民权和民主的特别关注。以日本的参审制度为例,200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裁判员参与刑事裁判的法律》,规定通过选拔普通国民担任裁判员,与法官一起共同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以此加深民众对司法的理解和信赖。日本的参审制较多吸收借鉴了美国陪审制的陪审员选拔方式和欧洲参审制的参与审判方式,以从有选举权的民众中随机抽选参审员、同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共同讨论来认定案件和适用法律的方式,使得民众得以参与司法过程。对于日本的专门审判人员如法官而言,他们在法律研修过程中只注重对专业知识的获取和运用,但随着社会关系尤其是日本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日本法官太过脱离民众、脱离普通生活导致他们不了解基层民众的情感需求和价值选择,在审判过程中单一地采用纯粹法律思维去审判案件,极可能会得出与普通民众基本价值观念不相符的结论。以中国人在日本日本军的案件为例,有很多中国人因受过日本军伤害而向日本法院要求获得公正赔偿,然而此类案件中的很多审理结果都令人非常失望,因为日本法官们基本都是匠人式的、机械地适用法律,没有适当地考虑政治性需求。对这样的审理结果,日本很多普通民众感到不解,认为这与他们认为的公平、正义等理解是相悖的。因此,强调民众参与到司法过程中,以发现、纠正这些类似的错误显然很有必要。近十年来,日本的司法改革动态也显示出了日本已经逐渐意识到民众民权的重要性,如参审制、调解制等制度的设立,也在逐渐扩大对民众司法参与权的实现方式和途径范围。
3严格的法律人才筛选和培养制度
日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资格实行的是终身制,因此极其讲究法律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和任职资格认定的严格性。日本习惯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种职业统称为“法曹”,其任职有着严格的人才筛选制度和相当培养过程。在日本,对于大多数大学院校的毕业生而言,要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首先必须通过日本司法考试,每年都有数万人报考司法考试,却仅有1500人左右被录取,并且每人只能考三次,三次未通过司法考试者,其法科大学院校的学历就作废了。正因为司法考试的高难度以及通过后良好的职业前途,其也被称为“现代的科举考试”。以2007年司法考试结果为例,当年的最终合格率只有1.3%,最终合格人数大约只为300人,其通过难度可见一斑。此后,只有经过激烈竞争获得考试合格者才能被录取为司法修习生,进入司法研修所进行为期一年半的一体化集中研修。这样严格的筛选法律人才机制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每年可以获得日本具备最高法律素质的适格从业预备人员,当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浪费了一定的人力财力资源。此外,司法研修所实行的一体化研修方式也能够最大程度地促使日本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在一年半的集中研修期间,通过共同学习、讨论和交流从而形成较为一致的法律观念和职业一体化意识,以图日本法律能够在理解和适用方面获得和谐统一。然而,日本这种近乎严苛的法律人才筛选和培养制度也导致了其司法人员的严重匮乏和司法效率的极其低下,在经济界和产业界的要求下,日本终于推出新司法考试制度,新旧司考制度并行,以弥补社会对法律从业人员的强烈需求。但是,从猛然扩大到10倍的司考合格率可以预见,日本法律从业人员尤其是律师其职业竞争也将日趋激烈。
篇5
西汉冀州广川人士董仲舒提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对儒法合流、礼法并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这一指导思想一直指导和影响着冀州封建法制建设的走向。到了隋唐时期,冀州儒学家推动法制建设的发展,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理论原则。礼与法走向了统一,古代冀州德礼的法律化正式完成,从此,冀州“礼法合一”的法制思想就深入人心了。虽然冀州法学家提出的这种“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原则把“礼”当成主调节器来调整社会关系,把伦理道德摆在最高位置,当作是指导原则,而忽视“法”的作用,认为“法”只是实现“礼”、“德”的工具,这一思想固然是与现代法治所提出的法律至上、依法治国是相背离的,但是,冀州的法学家们并没有全面否定“法”在治国中的作用。冀州法学家们认识到法律应该与伦理道德相辅相成,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共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所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冀州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当代法治建设中有积极的作用
冀州大地可谓人杰地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豪杰冀州出,丹心照后人”。正因为冀州人重信义、轻名利的美好品质,故体现在冀州的法制中表现出了“重义轻利”的法律观。这一法律观包含“取利有义”、“见利思义”等思想,看到利益,首先应该想到道义。这一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人格品质,还是作为一种商业精神或立法指导原则,都给人一种积极的正能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导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地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效应也有消极的一面。“重义轻利”的观念可以使人们在面临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冲突时,能够舍己为人,能够为了尽到法律义务而忽视或放弃个人利益,这种高尚的品质在如今更是值得提倡的。
(三)冀州“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对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有正面影响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习惯法还未产生,冀州先民就形成了对自然的崇拜,人们敬畏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有天神的存在。发展到封建社会时期,冀州人民讲究“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指人与自然相统一。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非常强,冀州人民只能靠天吃饭,人民的生活完全依赖大自然,风调雨顺可以使他们人寿年丰、平安无事,人们才能幸福的生活下去。旱涝不均的恶劣自然条件则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问题,因此他们懂得珍惜保护自然[1](P146-147)。当今我国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导致了对大自然的过渡索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森林减少、资源枯竭、沙漠化严重、自然灾害频频不断,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今,人们在大自然的惩罚中觉醒开来,国家提出了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政策。所以现在重新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科学发展观,这一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
(四)冀州人“无讼”的法律价值观念对我国特色调解制度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古代冀州人历来追求和谐、安定的大同世界。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人们相处应遵守礼节、互相谦让,将人们之间没有争端的和谐状态看作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因此,一直以来,“无讼”成了冀州传统法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实现“无讼”的目的,人们宁可委曲求全、丧失公平、曲解法律。当然,这种一味地强调调解的做法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存在很多的消极因素,与现代社会的调解制度并不相符。但是,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形式,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管辖面积辽阔、地区差异大,公民文化素质和法律保护意识不是很高的、法律基础薄弱,法律专业人员与司法人员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2](P57)。我们应该继承吸收古代冀州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构建一种公平、自愿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的建立能够起到重视人权、减少诉累、提高办事效率的目的。
二、冀州法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尽管冀州古代法制在当代现实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冀州古代法制观念受到等级制度、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等影响,更多地是为维护封建皇权贵族的利益的,反映了封建法律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缺乏公平公正。另外,因为时代的变迁,当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些迂腐顽固的法制思想以及其保守、非理性的残存陋习已不再适用当今社会,反而给如今的法制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所以,我们应该克服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弊端,摒弃这些传统迂腐的法制思想观念。
(一)冀州法制受传统“礼治”和“人治”观念的影响,而忽视了“法治”
在古代,冀州人民主张“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认为人在治国安邦中起主导作用,法律不过是人治的附庸。并且,冀州的法学家多是名臣大儒,他们把儒家的“礼”发挥地淋漓尽致,把“礼”当作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工具,认为“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冀州早期存在的各种礼仪,例如,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等这些构成冀州人民早期的日常行为准则,而忽视法律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认为法律则是道德的附庸,是居于道德和“人治”之下的。这种顽固的思想一直影响至今,造成了现代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没有按照法律的适用处理,而是按照上级的指示来处理,更有甚者,对案件的审理是按照道德习俗来评判的。这种轻视法律的现象违反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应为我们所遗弃。
(二)冀州古代“亲亲互隐”的观念延续至今,造成包庇犯罪,阻碍案件的侦破
冀州的法学家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制定法律,依然是从维护礼教原则出发,为了维护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儒家礼制,他们肯定孔子提出的“亲亲互隐”的原则,同意“事亲有隐而无犯”的思想,认为亲人犯罪,对其包庇,为其隐瞒,则不构成犯罪,允许亲属容隐制度的存在[2]。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今。现如今很多人都不赞同“大义灭亲”的行为,认为亲人是不可背叛的,这一思想助长人们相互包庇之风,袒护犯罪分子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阻碍案件的侦破。所以这种“亲亲互隐”的原则是我们所不提倡的。我们应该将法律放在第一位,为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为了社会的和平安定,我们应该维护法律,不避亲友,并及时劝阻亲人正视罪行、承担罪责、投案自首。
(三)冀州自古形成的“法刑一体”的观念,使公民害怕法律,难以自觉守法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律》中就制定了残酷无比的刑罚,即使在汉代以后,“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开始提倡,但刑与法始终是分不开的。“刑”本身不是一种规范体系,而是法律的附属,仅仅是国家用来保证“法”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从属于“法”的。这种情况导致冀州人民形成了畏惧法律的心理,对法律不够信任。这种观点根植于人们心中,至今仍有些人抵触法律、害怕法律,没有将法律当作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工具。然而,现代法治对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仰法律、拥护法律,公民的信仰和拥护构成当代法治最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每个公民都应该明确理解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工具,最终产生对法律由衷的赞叹和深厚的感情,自觉遵守和维护法律。只有这样,法治有可能实现。
(四)冀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法制思想,不利于创造公开的法制环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原是指国家对人民进行统治,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需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做和在做什么。后唐朝冀州法学家孔颖达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提出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今制法已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故民皆不畏上[3](P135)。认为应该保持法的秘密状态,不向社会公开,以便“临事议罪”,使民畏于上。这是儒家“人治”思想的突出体现,构成冀州法制的特点之一,在当时封建社会或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观念违背了法律的“可知性”和“可用性”原则,不利于建设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丧失了正面意义,是我们所摒弃的。
篇6
(三)法制内容的继受一是,西夏法典将“八议”、“上请”、“例减”、“官当”、“收赎”列为定制,直接承袭唐宋法律赋予贵族官僚的各种特权。贵族官僚犯罪,只要不涉十恶,可享有议、请、减等特权,奏请朝廷议减或免罪。《天盛律令》卷二“八议门”规定:“自帝之姻亲至八等宾客一样,犯死罪时,奏议实行。自长期徒刑以下依次当减一等”;“罪情与官品当门”规定官员犯罪可以官品抵罪,“诸有官人及其人之子、兄弟……除十恶及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犯各种杂罪时与官品当,并按应减数减罪”。官员犯罪还可用罚缗或马来代替应受的刑罚,谓之“收赎”,交20缗钱或罚一马折抵降官一级。二是,在刑事法律领域,西夏不仅照搬唐宋法律中一些既有的罪名和刑名,而且还汲取其刑事司法经验,继受其科学的刑法原则,如区分犯意的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公罪与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同犯罪区分首从以及法律类推适用等。三是,在婚姻法制方面,中原律典中的具体规范也被参酌吸收到西夏法制中,如“同姓不婚”的禁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成立要件,须经“六礼”的婚姻缔结程序、“七出三不去”的婚姻解除原则等。四是,西夏的诉讼法制亦受中原法典的影响。《天盛律令》卷十三“许举不许举门”规定了举告制度,“举虚实门”规定了举告不实者应反坐的原则。卷九共7门90条,详细规范了案件的类别、审案的时间、方法、程序和监督、刑讯和监禁、审判制度等内容。例如:“事过问典迟门”规定了级别管辖,中央司法机构和地方司、州、县有着不同的审判权限;“越司曲断有罪担保门”规定了上诉和申述制度,囚人及亲属不服一审判决或已生效判决,可以上诉或申诉,但必须逐级申请,否则予以处罚;“行狱杖门”规定了刑讯制度和司法官员的责任,其借鉴《唐律疏议》“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的规定,并严格每次拷讯的限数,统一了杖、枷等刑具的规格,囚人被拷打致死,未有异议,杖数未超不治罪;超过杖数,拷问者要受徒二年之刑,若随意拷打或因有私怨不该拷打而拷打者处罚更重。
(四)法制特征的继受首先,维护专制皇权统治。与唐宋法律基本精神一致,西夏法制的首要任务即是捍卫至高无上的皇权。将谋危社稷、背国降敌、危害君主安全、有损君主尊严以及图谋毁坏宫殿、皇陵、祖庙等行为列入“十恶”,科以重刑,同时连坐亲属,其罪不得容隐,不在八议论赎之限。不仅如此,西夏秉承中原法律“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5](刑法志)的宗旨,严惩威胁王朝统治秩序的“盗贼”、“群盗”以及私匿武器等行为。其次,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与中原王朝相似,西夏也是一个等级身份森严的社会,表现在法制上公开宣称贵(贵族、官僚、僧道)、良(农、匠、商)、贱(使军、奴仆)法律地位不平等。头监(主人)可以随意支配、处分贱民,禁止卑幼举告尊长,良贱不可通婚,良贱同罪异罚。例如:同是伤人,若庶民伤官人则处斩,而官人伤庶民仅服徒刑。最后,立法权和司法权集于中央。中国自古以来“法自君出”,君主掌握最高立法权,可对现行法律立兴改废,而且司法与行政不分,“狱由君断”,皇帝亦是最高审判官。西夏法制延续此一传统,建国之初就将立法权收归朝廷,并且皇帝执掌案件终审权。西夏仿唐宋法律实行死刑复奏制度,强化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凡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要案、疑案,须上报朝廷直至皇帝对案情复审,且反复奏请三次,经核准后方可行刑。
二、西夏法制对中华法系的创新
(一)编撰体例的创新代表西夏法制最高水平的《天盛律令》从形式到内容深受中原律典(特别是《唐律疏义》和《宋刑统》)的影响。与此同时,西夏修订的律典也彰显出独特个性,在法典体例上与唐宋法律很是不同。1.统一的律令条目。西夏立法者汲取唐宋法典编纂的经验教训,《天盛律令》既没有《唐律》条后附赘的注疏,也不似《宋刑统》条外另加格、式、敕、例,而是将所有律、令、格(官吏守则)、式(公文呈式)条分缕析地汇编在一起,使之成为整齐划一、条理清楚、较为完备的法典。《天盛律令》修订时,正值南宋高宗、孝宗之际,其时南宋法律庞杂混乱,难以掌握和实施,往往以断例(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汇编)行事,出现“以例废律”的情形。《天盛律令》采取统一的格式条目,实际上把中原法典中割裂开的内容有机融为一体,不仅使律文明确清晰、方便查找,而且避免了轻视本律、律外生法的弊病。这样的编纂形式在当时达到了很高水准,大大增强了法典的系统性、指导性和实用性。2.法条分层次书写。中国传统法典每一条都顶格书写,这种不分层次的形式不便于对法条的掌握使用。西夏法制打破此一格局,进行大胆尝试,创造了近似现代的纲目分明、层次清晰的书写格式。《天盛律令》中每条第一行顶格书写一个“一”字,其下为条目内容,第二行降格书写。若同一条中包含不同内容,则分款书写,每款下再分若干项目,仍依此类推,分项降格书写。3.条文结构由三要素构成。西夏律令的条文结构与同时代的中原法典不同,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法律条文不是两要素结构(罪状、制裁),而是三要素结构(假设、罪状、制裁)。[8](P531)以《天盛律令》卷三“群盗门”第二条为例,[3](P169)“群盗数往盗窃”是罪状,表明法律规范的内容;“畜、物未入手”和“已谋而未往”为假设,说明此法律规范适用的不同情形;“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和“主谋徒十二年,从犯徒六年”乃制裁,根据不同的假设对违反该规范者科刑。西夏律令在法条中直接规定假设,可以避免司法活动中因为立法纰漏,司法官通过逻辑或上下条文内容比附类推假定的做法,从而减少了司法的任意性。
(二)法制内容的创新《天盛律令》中除“十恶”等10余门基本因袭唐宋法律外,其余40余门与唐宋法律相关联的内容均依据本国实际情况作出变通。例如:附会汉法的同时兼顾党项社会风俗,缩短了服丧时间、违反服制的处罚也不及唐宋法律严格;对父权、夫权的维护逊于唐宋法律,增加对子孙、妇女财产权利的保护;婚姻方面参酌党项民风,扩大了祖父母、伯叔、舅姨的主婚权。不仅如此,即便是对唐宋法律因袭较重的部分,律令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八议门”扩大了议亲的范围,包括皇帝之族亲、妻亲和姻亲;“罪情与官品当门”细化了以官当徒条款;“老幼重病减罪门”严格了免罪规范,唐律规定若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而《天盛律令》则依成人论。西夏法制在继受和变通唐宋法律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中华法系的创造与革新,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1.增加了唐宋律典没有的全新内容。有学者将《天盛律令》与《唐律疏议》、《宋刑统》逐卷对比后发现,两者内容相近的部分仅占约39.3%,其余60.7%的内容都是唐宋律典中所没有或属于敕、例、条、格的范畴。这些崭新内容包括官牧管理、畜牧税收、盗窃牲畜;农户登记管理、地租分成;官吏品级编制;兵器供给和校检、战时动员与边防法规等。2.形成了独具西夏特色的法律领域。一是独特的畜牧法。西夏位于农耕和游牧过渡地带,畜牧经济远比中原发达,因此其法制一改唐宋法律的农本主义色彩,体现出农业与畜牧立法并重的特征。《天盛律令》中畜牧法内容详备,其条目和字数分别是唐宋律典中《厩库律》的5倍和10倍,对牧场划分、管理,畜类的牧养、供应、校检和疾病防治以及牲畜课利等进行了细密规范。律令突出对牧场和畜类的保护,侵害他人草场者,按强盗论处;随意屠宰牛马骆驼、用活畜陪葬和擅自外借官畜者处徒刑。二是独特的边贸法。西夏法制中经济法比重较大,举凡农牧、酿酒、池盐、租税、库储、市易都有详细规范。西夏边境贸易活跃,边贸法比较发达。内容大致包括征税、查辑违禁走私等。三是独特的军事法。党项民族骠勇尚武,西夏又以武立国,险恶的战争环境使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法规建设,律令之外颁行专门军律《贞观玉镜统》,规定了军事责任、边防、军需、赏罚、以功折罪及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其完备程度在中原律典之上。四是独特的宗教法。西夏宗教繁荣,尤以佛、道为盛,为此在律令中制定了较完备的宗教法规。律令维护寺院、道观、僧道的权利义务及其享有的特权,同时规定了宗教管理制度,包括僧人封号、赐衣、试经度僧和度牒制度。3.进行了独创的刑制改革。唐宋延续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西夏虽实行五刑制,但差异较大。囿于疆域狭小,流刑难以实施,故统治者只保留中原律典中的杖、徒、死三刑,而将徒刑按服刑年限分为三种:短期徒刑(3月~6年)、长期徒刑(8年~12年)、无期徒刑。此刑制乃中国刑法史上的首创,是西夏法制对中华法系的贡献。与唐宋法律相比,西夏法制有轻刑化倾向。例如,死刑仅保留斩、绞二等,宋代的刺配、枭首、凌迟等酷刑并未影响到西夏刑制。4.保留了党项民族习惯法。游牧部落时期的民族习惯法也是西夏法制的重要渊源。律令中的“大人”即由先前党项社会“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诉之曲直”的“和断官”演变而来。《天盛律令》卷三“自告偿还解罪减半议合门”规定,盗窃之人一月之内,心悔送状,自首求解罪,若所盗之物全部归还物主,且催促同伙将赃物归还物主时,当全解其罪;若仅归还部分赃物,则依偿还多少依次减罪;盗窃人在规定期限内将赃物如数归还物主议合后,物主不得再行举告。这种独特的刑事和解制度和以牛、羊等实物赔偿人身伤害都体现了党项民族习惯法的遗风。另外,西夏法制本身就具有多元性格,家法族规、乡规款约等民间规范与调解机制,收继婚、赔命价等民族习惯以及民间道德教化等都在律令之外发挥着重要的指引和规范功能。
三、西夏与唐宋法律文化交流的初步探讨
由上文所述可见,西夏与中原法律文化交流中,西夏立法者不是机械模仿和简单移植唐宋法律,在有选择的吸收中原法律文化的同时,立法者对法律有着独特的继受能力和创新精神,结合西夏社会现实和党项民族特点,依据自己的取舍标准,融入民族自身的法律元素,对唐宋律典的形式和内容做出了大量的变通与革新,为中华法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质。西夏法制在调整当时社会关系方面应当说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发挥了终西夏之世的功效,而且其影响力已超出特定时空,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绚丽华章。后世对西夏法制之所以给予高度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其对唐宋法律富有成效的继受和创新。西夏对中原法律文化的继受是建立在法律文化发展不平衡基础上的。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因素,各民族和国家法律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而这种不平衡正是引发法律文化交流的源动因。不平衡就会存在压力,而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压力又往往转化成变革的动力,促使劣势一方学习和仿效优势一方的法律文化。中华法制肇始唐虞,规模宏大、源远流长,远非党项民族习惯法可比肩,是故自党项内附中原时就开始了继受汉法的历程。史载,李元昊曾长期派遣使臣暗中了解宋廷法令典章,还用重金买来宋朝遣返的宫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宋廷的刑赏典式,作为自己建法立制的参照。[15](卷13)这些史实正是西夏继受中原先进法律文化的缩影。西夏和唐宋法律文化交流可划分为继受和创新两个侧面。继受过程乃是受法律文化同一性原理的支配。一方面,人类生活本质上具有相通性,不同法律文化实质上都表达着人类追求社会正义和秩序的本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普适价值,法律文化的同一性奠定了西夏和唐宋法律文化交流的可能。另一方面,日渐强盛的西夏为统治征服土地上众多汉人的需要,不得不认同和采用更高层次的经济形态、政治模式和典章制度,所谓“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立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衣服,行中国法令”。
篇7
【论文关键词】宪法私法化 基本权利 宪法解释 论文论文摘要:所谓“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诞生,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热烈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就是宪法在私法领域的适用。本文将在前辈讨论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中国宪法私法化的必要性、私法化道路上的障碍以及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法,并将重点讨论宪法在私法领域内适用的必要步骤之一——宪法解释体制改革。 对于“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究竟是否名副其实,理论界还有不少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在受教育权有具体法律法规保护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2oo1)法释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是有问题的,此案并不能成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暂且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单就最高人民法院这一批复的意义而言,其重大影响是无可厚非的,它实质上允许了司法实践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保护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也难怪理论界,司法界以及社会舆论反响剧烈。 而从我们想要讨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批复首次允许了宪法适用于解决公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与权利之间的纠纷,即中国宪法正式进入了私法领域。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担忧甚至恐慌的态度,因为这可能预示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严重干涉。 一、公私法划分传统 首先从历史看,“宪法并不能适用于私法领域”是有着世界范围内的深远渊源的。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认为宪法作为公法,确切的说是公法之首,应当首先成为公私法化分支价值的约束对象。宪法本身主要规定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而对私人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无意调整和干涉。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这样的规定也是基于对公权力侵犯的防卫。“依据此时代的思想,国家之权利行使,须与节制,而人民的(自由)基本权利,原则上是无所限制的”,“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于是,宪法的公法属性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消极防卫性,成为宪法私法化的一大理论障碍。 但是,笔者认为用一个“时间差”就可以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诞生于古老的罗马法时代,而近代宪法与宪政精神则诞生于距罗马法时代1500多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众所周知英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并没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传统,也就是说英国资产者立宪之时并没有意图将其明确归于公法,更莫说“公法之首”。当然,《权利法案》以及初期的一系列法律文件制定的目的明显是用于限制王权,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其立宪目的完全排斥宪法对私人领域的干涉。而对于大陆法系后来坚定不移地将宪法锁定在“公法牢笼”,则仅仅是因为英国宪法精神的适时体现恰好与传统公私法划分理念几乎完美契合。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们终于发现这样的契合是有着很多不完美的缝隙和漏洞的,这也成为除了“时间差”以外宪法进入私法领域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二、立法崇拜 宪法是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及国家机关权限的根本性大法。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决定了宪法规范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这就与法律的可操作性之间存在矛盾。宪法基本权利需要具体化,德国宪法学者称之为“宪法委托”或称“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是谓宪法在其条文内,仅为原则性之规定,而委托其他国家机关(尤其以立法者为然)指特定的、细节性的行为来贯彻之”。<立法委托,就立法者而言,不仅是立法授权,不仅是立法者由宪法直接获得的立法权限,同时也是要求立法者制定执行性法律。据此,立法者就应该酌情在一定的期限内制定相关的法律,履行立法义务。如果立法者不履行此项义务,则为立法不作为。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接受了“宪法委托”这一理论,但是却走进了危险的误区——过分依赖立法,以为立法可以包治百病。而事实上,“立法本身并不全面,因为它不可能全面”⑦,不全面性、滞后性、模糊性等不可避免地缺陷使得仅仅依靠法律来达到充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之目的成为不可能。而且,将基本权利保障完全寄托于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是不合理甚至危险的,因为:第一,在权力救济责任已完全归属于国家的现代社会,如果立法机关没有将基本权利具体化,那么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形同虚设;第二,立法机关的权力严重扩张,而又缺少违宪审查机制,很有可能导致“立法机关的独裁”,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则有可能遭到削减甚至取消;第三,这种完全由立法机关决定 公民权利存无、多寡在理论上就会得出公民权利源于国家赐予的荒谬结论,严重违背了宪政精神。 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社会经济生活状态的急剧转变,以及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中日益出现强势权利对弱势的侵犯与欺压,这种侵犯在很多时候是隐性的,因而也是无法用具体法律规范来调整的。事实上,这是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而对传统宪法仅适用于公权力之间,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这一理论的变革,也是各国司法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诸如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等。 三、对司法解释的僵化理解与不合理宪法解释体制 将概括性、抽象性的基本权利适用于司法审判,必然涉及司法机关对宪法的解释权限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由代表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因而不具有宪法解释权限。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规定进行立法解释,即对宪法条文的含义或界限的进一步说明,并据此否定宪法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实施后仍有效的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法律的立法解释或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对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由此看来,对宪法条文的含义与界限的解释权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对宪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问题,由司法机关解释是完全合法的。 也有人认为人民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也是宪法的制定者,也即是宪法文本的作者,而作者应当比其他人更了解作品的真正意图,又因为立法机关——在我国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因此也就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的权力。但是第一,这种观点的必然结果是导致“少数人的暴政”;第二,我们已经发现,“人民”事实上是不会自己统治的,人民更多时候是一个假想的统治者,而真正的掌权者——委托立法者——在对其没有任何监督与约束的情况下,就成为了事实上的独裁者,因为不受制衡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种“民主”的后果可想而知。当然,这不是单独民主理论可以解释或解决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建立权力制衡的机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也就要求宪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 宪法作为人民意志与自由权利诉求的圣经,能否由适用者及法院或法官做出解释的疑虑和困惑,其实自宪法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即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宪会议上就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固麦迪逊也从积极意义上阐释了宪法的司法解释问题。而到了1803年宪法审查的种子终于萌生,由此引发了波及世界的宪法司法解释的革命,直至当下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外,宪法的司法解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虽然各国的宪政社会背景和文化不同,但是,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选择了宪法的司法解释。这无疑从实践上证明了我国实行宪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比较可行的改革方式是逐渐赋予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当中享有一定的宪法解释权。这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及时处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仅依靠普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有关裁决的公正性,而且司法机关专职司法,在实践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有效的解释制度没有助于宪法规范的正确使用。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空作的决议》中对法律的立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中所提及,目前的宪法解释只能是司法机关在司法领域内进行的应用具体解释,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法机关实施的抽象的宪法解释。随着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不断发展,宪法解释原则的逐渐确立,直到有效的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建立与完善,再将解释权完全转归专门机构,这将是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建立发展的可行之路
篇8
大致而言,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与文学、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等等。但是,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建设。
一、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主流宪法学
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来带动整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各自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
就近五年中国的宪法研究情况来看,宪法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对宪法理论体系的研究(宪法哲学)、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宪法解释学),以及从国家建设角度对宪法政治的研究(宪法政治学)。这三种研究构成了目前宪法研究的主流。大致讲来,其共同特征是关于宪法的规范性研究,关注的是“宪法是什么”的问题。
宪法理论体系研究关注方法论、基本范畴以及宪法理论体系的解释力。[ii]构建宪法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宪法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宪法文本研究的问题则集中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修改)权力、宪法文本的内容、“宪法修改”的活动、[iii]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iv]宪法文本的解释、[v]宪法的实施或适用(宪法监督、宪法诉讼)。[vi]
对于一个学科建构而言,规范宪法研究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宪法学的独立和自治,形成宪法学专业的体系和术语。但是注重规范分析和体系化分析的宪法研究同样存在弊端,它可能带来的是宪法学共同体更排他的话语,宪法学知识的更自给自足,法学内部引证网络的更加增强,和宪法学对外部学科知识影响(或者“帝国主义”)的更成功的驱逐。宪法学研究发展与封闭同时进行。[vii]也正是由于从体系出发,或者更注重对语词和概念的诠释,宪法学研究的范围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很多研究领域,宪法学者往往并没有发言权。比如,司法改革这个本属宪法领域的问题,却一直由法理学者主导研究的方向;[viii]而关于私有财产的入宪问题的讨论最早或者说最有影响的,不是宪法学者,甚至不是法学者,而是经济学者。而另一方面,目前宪法学研究的人员力量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又比较落后,远不如法学理论、民法学,甚至不如最为相近的行政法学研究力量。[ix]
有关宪法政治的研究不仅包括宪法学专业学者,还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以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宪法政治研究,即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思想来建构主义,也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更多的包含了宪法的政治权力构成以及宪法的政治制度理念,并反映在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务实的宪法政治研究将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违宪审查制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但更多的宪法政治研究侧重于价值判断,比较理想化。强调宪法研究与政治理论(法律理论)研究的结合,研究宪法与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x]进而,主张在中国宪法改革的过程中贯彻这些政治理念。[xi]在宪法的实施或适用中,宪法诉讼、或者宪法监督、或者宪法司法化都需要理论的支持。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讲,宪法政治研究虽然是将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忽视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在我看来,宪法政治研究必须要回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才会有意义,否则,不免会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非主流宪法学
相对于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主流宪法学之外,目前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宪法学研究,比如宪法经济学和宪法社会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更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色彩。相对来说,研究群体很少,亦缺乏知识积累,因此学科发展比较弱。
宪法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宪法规则体系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在个人只掌握有限知识的情况下,哪些宪法规则在协调个人的活动上对个人是有益的?特别是,哪些宪法条件最有助于确保竞争和创新?第一个问题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实证宪法经济学);而其余问题则属于规范宪法经济学的范畴。总的来讲,聚焦于宪法经济学已经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在既定规则之内作选择转向了在不同规则之间作选择。”[xii]目前,经济学界有一股力量是研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而中国法学界极少有人研究。
宪法社会学更关注如杉原泰雄所提倡的“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界目前更重视研究“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而“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研究是以解释论为中心的规范的宪法研究。杉原泰雄认为,过去日本的宪法学是以解释论为中心、与国民生活脱节的宪法学,它对探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是极为消极的。正是因为这种宪法解释论没有把国民“放在心上”,与国民的实际生活脱节,自始自终只是从法学技术上对宪法问题进行解释,所以时至今日,宪法学仍没有能像政治学和经济学那样,在国民的心中得到一种亲切感。[xiii]这个基本判断是适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如同冯象所云“它没宪法”。[xiv]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理论的宪法问题,归属于规范的宪法研究(宪法解释学)的内容。而“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经验的宪法问题,归属于宪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独立的宪法理论,但它一定存在着宪法的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的实践,有制度意义的宪法,或实在的宪法。因此可能进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这种研究更强调历时性,真正关心一个具体国家发展的问题、实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xv]
宪法社会学研究提倡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宪法问题。
宪法问题也并不必然与宪法文本相联系,并不以宪法条文规定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的标准。也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宪法问题。比如,基本权利研究中涉及“乙肝歧视”、“身高歧视”、“高考移民”、“迁徙自由”等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尽管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可以归入部门法问题,但仍然可以上升为宪法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来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是要看这个问题的现实影响力,这个问题是否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中具有可争论的、重大的意义。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宪法问题,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未必。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在中国就不是。因为堕胎在美国涉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而在中国则成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普遍做法,为大众所认可,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族群对立问题在中国大陆不够成一个宪法问题,而在台湾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权以及涉及各地高考分数线差异过大、高考移民、“齐玉苓案”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失业机会越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xv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是一个宪法问题。
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只是宪法问题的构成的一个事实要件,构成宪法问题还有法律要件。而宪法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部门法来解决。宪法问题也可以是部门法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筛选机制将部门法问题选择成为宪法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分析对于目前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说,是另外一种解读,[xvii]就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因此,法学界包括法律界主张法律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解决,部门法解决不了才会成为宪法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人为划分公私法来决定宪法适用可能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来选择问题,因此,从法律制度而言,是否构成一个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国家的法律筛选机制。不是首先进行部门法归属判断,而进入由法律组织机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断程序。比如,在美国,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case都能够成为宪法问题。而美国所谓宪法性问题如涉及经济规制、税收、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财产权等都是通过最高法院作出判例才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进而作出宪法性问题的判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有关宪法问题研究的知识分野(比如规范分析抑或实证分析),并有了比较多的知识积累,但是并不意味着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当然建立。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通过学科制度建设将这些不同取向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和人员组织化。
学科制度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xviii]从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来看:从事中国宪法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有专业的中国宪法学会;能够培养宪法学的硕士和博士生,象中国人民大学还招收宪法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出现了专业刊物《论丛》等以及各种评奖活动来评价学术成果;有诸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海外基金会资助研究等等。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制度的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除去一部分传统分支学科如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特征。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除了要依靠宪法学的学科制度之外,还要看相应的其他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情况。宪法政治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人类学分支学科制度也要依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当然本学科的知识积累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沟通与融合。以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为例,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宪法学和社会学双方的共同力量才有可能发展强大。
但是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最根本的是,分支学科制度体现出来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包括其主张、活动和结构,它是对正统的挑战,是变革的力量。[xix]比如,以实证和经验分析为特征的宪法社会学就是对以规范分析为特征的正宗宪法学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规范宪法研究占据宪法学学科的主导,面对宪法学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专业的宪法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因为目前宪法学科培养出来的学者,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并在各自的研究机构形成学术梯队群。这些学者与所培养的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关系,而不是学术上的相互竞争和批评关系。在这种“忠诚”关系的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老师与学生合署名以及尊师“祝寿”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学术声望制度越完善的地方,给老师的“祝寿”活动要相对少的多。[xx]因为,通过“祝寿”等活动,可以变相提高与老师有关的一批人的声望,而这种声望恰恰不是通过其学术水平来提升的。在现有宪法学学科制度已经促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与主流宪法研究差异显著的分支学科研究,往往会被视为“学术越轨”和“学术异端”。具体而言,在课题资助、博士点评定、文章刊登等具体的学术生产环节,由于评审人往往仍是主流宪法专业训练的人士,相应的,从事与主流宪法研究对立明显的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分支学科的研究必然会被边缘化。
具体而言,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宪法学分支学科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由于在教育部的专业名录中,宪法学卡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而是与行政法合称“宪法与行政法”作为二级学科。而作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多数也没有列出来。由于专业名录涉及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先天不足。
第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要比跨学科的宪法学分支学科,更有建设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法律社会学要比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可能。因为,法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制度,知识体系和人才,而宪法学只能算上二级学科,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与法学相比,因此,建设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更具有可行性,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完善将会对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宪法社会学更有理由纳入到法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制度中,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没有建立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必要。宪法人类学也是如此,它与法律人类学有更多的同质性,整体的(holistic)观念、比较分析和田野民族志调查,因此,应该成为法律人类学学科的一个方向,似无独立的必要。[xxi]
第三,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的“专业同人刊物”,或称“旗舰刊物”(flagshipjournal)。它反映本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旗舰刊物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刊物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学术影响,而旗舰刊物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成果来提升刊物的声望。[xxii]实际上,象宪法学这样的大学科还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更不能奢望宪法学分支学科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即使有,刊物能否保持连续性也值得怀疑。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如法律社会学亦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实际上,如果象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有了专业同人刊物,积极刊登宪法社会学和宪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会极大的促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
第四,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的重要一环是学科评价机制。就学术成果来看,匿名评审绝大多数都没有实行,关系稿、人情稿、编辑一人决定稿等现象非常普遍。而不论是职称评定、研究课题、重点学科、博士点等评选,多是由外行人评议乃至行政权力插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发表出来的宪法文章的质量难以迅速提升,宪法学教授越来越多,而学术水平却未见提升。当然,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与历史原因和学术管理体制有关。如果仅就宪法学分支学科评价机制建设而言,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应当让与分支学科相关的外学科人士参与到学术成果的评价过程当中。更进一步,法学院特别是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国内一流的法学院,应当培养更多的学术人才,而师资的来源不应当仅限于法学背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均可引进到法学院来。
总的来看,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特别是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建设,并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资源,重要的在于两点:
第一,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各自独立,而恰恰是要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是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如同苏力对以跨学科为特征的社科法学的评价,“社科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促使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向”,“把社科法学视为传统法学的天敌不合适,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知识加上可能获得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共同推进,把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向前推进”。[xxiii]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i]如,2005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门召开了“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研讨会”。
[ii]如,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赵世义:《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中国宪法学通向成熟之路》,《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叶必丰:《论依法治国与宪法学的新体系》,《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秦前红:《评法权宪法论之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iii]以1999、2004年宪法修改为例,在此前后主要法学核心期刊纷纷推出“宪法修改笔谈”,比如,《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的“宪法修改问题笔谈”;《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世纪初的发展”;《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3期的“修订现行宪法完善制度”;《法学》2004年第4期的“世纪之初中国宪法的修改和发展”;《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的“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
[iv]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v]如,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苗连营:《中国宪法解释体制反思》,《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vi]如,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vii]对整个法学学科研究封闭的批评,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viii]如,贺卫方:《司法制度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编,“司法制度”。
[ix]一个佐证就是,1998-2002年中国大陆法学著述他引前50位学者中,只有一位纯粹的宪法学者(童之伟),然而这位学者在那几年写的更多的是法理学的论文;与此相比,民商法者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15人、行政法4人(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王名扬),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另外,从五年的法学论文产出数量来看,纯粹的宪法学者也几乎没有,姑且可以算作是宪法学者的有童之伟、郭道晖、周永坤、杨海坤、蔡定剑(他们兼跨了宪法、行政法或法理学),参见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
[x]如,程燎原:《关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杨君佐:《共和与民主》,《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杜承铭:《论的人性基础》,《法学》2000年第4期;王人博:《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xi]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xii]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407页。
[xiii]参见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xiv]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它没宪法”。
[xv]苏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重读〈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xvi]温辉:《“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解读》,《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xvii]更多的宪法的私法适用的分析,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xviii]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ix]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xx]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二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篇9
一、宪法基本权利能否被限制?谁来限制?限制到何种程度?谁来审查?
孙志刚案的实质是对公民宪法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问题,这涉及到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能否被限制及与其相关联的一系列宪法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可以限制的。作为最高法的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们是政治社会中个人所应享有的,也是国家必须给予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不是绝对的、排他的,也即并非不可以限制。虽然在理念上,这些权利是最高的,是天赋的,受宪法保障,但在实证的意义上,各国宪法基本权利均采相对保障主义,而非绝对保障主义,即基本权利可以依法限制。限制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是个人权利与其他法益冲突的客观存在。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人有相互依从性,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有可能侵害他人的权利或者社会利益,须在不同权利之间进行适度平衡,这就是限制宪法基本权利及基本权利相对保障主义的理论基础。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自由和结社自由、通讯与住宅不受侵犯这些传统的基本权利来看,其中没有一项是可以不受一般性的法律规则限制的绝对权利。言论自由不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造谣、诽谤、欺诈、教唆犯罪或以报警来制造混乱。人身自由也如此,当人身自由与紧急状态之下的国家安全、公共卫生与社会秩序相抵牾之时,人身自由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根据最早则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四条规定:“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力。因此,行使各人的自然权利只有以保证社会的其他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为其界限。这些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这一规定既是法治原则的具体体现,也包含了基本权利可以受限制,并且只能由法律加以限制的内涵。因此,从理论与法律两方面来看,宪法基本权利都是可以限制的。
其次,宪法基本权利由谁来限制?宪法基本权利可以受到限制,这已确凿无疑,问题是由谁来限制?现代政府构造主要由三个部门即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组成,是否这些机构都可以限制基本权利?答案则是否定的。在民主法治及基本权利的发展进程中,各国无一例外地明确了一点,这就是只有“法律”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前述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这些界限只能够由法律确定”已清晰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公民基本权利都以明确的方式或者明文规定的方式受到了宪法保护,“除非依照法律”,否则不得对上述权利做任何限制。“依照法律”即意味着只有法律才可以限制,其后,该理论发展为法律保留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分立或者分工的政府机构中,“法律”并非指一般法理学教科书在阐述法律渊源之时所指的不同位阶的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内的所有规范性文件,而是仅指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并颁布的法律。因此,此处所指的法律,必须具足法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否则便不可以称之为法律。
再次,宪法基本权利限制到何种程度?既然法律可以限制基本权利,那么限制到何种程度才最为相宜?在限制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以限制基本权利为借口,虚化或者抽空基本权利的内涵。果如此,则宪法基本权利无疑会沦为一纸空文,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就丧失其实际价值与意义。从宪法理论与国外的审判实践来看,确立了基本权利的基本内容或者核心不可以限制的原则。德国宪法第十九条(二)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危及基本权利的实质”。意指理论上,承认每一个基本权利中有一些核心内容,是任何法律所不能加以限制的。否则,限制这些核心内容的法律将被宣布为无效。但是,究竟如何掌握核心标准?从实践来看,主要有三个,即残余论、利益论和折衷论。[1]例如,在有关死刑违宪审查理论的讨论中,其中有学者所持的观点就属于此例,认为刑法规定死刑属于违宪,因为法律规定死刑,是法律剥夺个人生命权,生命权处于个人基本权利的核心地位,属于基本权利的实质,受宪法保障,因此不可以被法律剥夺,而规定死刑剥夺生命权的法律也在此意义上构成违宪。
最后,谁来审查?如果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超过了宪法所允许的限度,则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中,或者通过抽象审查,或者通过具体审查,有可能启动一个合宪性审查的程序,对这一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以确定其是否应在法律秩序中继续存在(在抽象审查当中),或者在个案中不适用这一法律(在具体审查当中)。这一审查通常是由法院或者中立机构进行的。并且,在具体审查当中,这一审查是由普通法院在适用法律裁决纠纷的过程中进行的。通过法院或者中立机构的审查,不适当地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被认定违宪而被撤消,个人宪法基本权利得到维护。
二、只有具备形式与实质理性的规范性文件才可称为“法”,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
在前述问题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即“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或者“法治行政”中的“法”为何物?在孙志刚案和其他一些类似案件中,看似主管部门是依据规范性文件做出的决定,但是,仔细考察,这些规范性文件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只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性法规。如果按照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它们无权限制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那么,什么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
前文已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法必须是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具备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规范性文件。所谓法的形式理性,指必须是立法机关按照程序通过的法律文件,法律的成立必须符合包括立法主体合法在内的法的程序要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意味着非立法机关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因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质内涵之一是确立了人民也即立法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因此,限制基本权利必须是狭义的人民代表机关-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才可以做的事情。进一步而言,也即只有在经过人民的同意之下,并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宪法基本权利才可以受到限制,
否则,其他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不可限制基本权利。考察法治与权利保障的历史,其一直是对抗皇权与行政机关的专横的过程,因此,法律限制基本权利,也是人民自身对其权利的限制,这一限制具体由人民的代表机关-立法机关-以制定法律的方式进行。
在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程序要件还暗含了这一问题,亦即并不是立法机关或者代议机构以适当方式通过的每一个决议都可以称之为法律,而仅仅是意指那些在符合狭义的条件基础之上通过的文件才可以被称为法律,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因为,法律与决议是不一样的,法律的通过需要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如提议权、三读通过、表决等,而决议则是一个简单程序,其通过并不像立法程序那样严格。这一点,对于考察我国的法治实践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属性具有重要价值。
所谓法的实质理性,是指立法机关按照程序所通过的法律必须符合法的一般要素,如法律必须是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没有追溯力的。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必须不能是针对个案,也不能是对具体事件的处理措施。在限制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严格禁止“个案性法律”和“措施性法律”,[2]因为这样的法律或者是针对具体人定订的,或者是针对具体事件制定的,它们不具备抽象的普遍约束力,不符合法的实质理性。其他实质要件也各有自己的针对性,如法律不得溯及既往。
因此,法律可以限制基本权利,意指只有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它排除两方面的认识:一是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机关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其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一是并不是立法机关通过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称之为法律,都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只有立法机关严格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并且这一规范性文件必须在具备形式理性的前提下,符合法的实质理性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只有这样,“对各种基本权利所施加的上述那种限制才会具有意义,同时才不至于使‘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受’立法机构‘的干扰变成一句空话,完全丧失作用。”[3]以此观照我国国务院颁布的限制公民人身基本权利的规范性文件,由于其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法规,故都应属无效。不独《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办法》,就是有关限制公民其他基本权利的规范性文件,如有关大学生不得结婚、劳动教养等规定,因其在性质上都属于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违反了权力分工原则,行使了本应由立法机关履行的职责,属于宪法上的越权,故都不具备合宪性基础。
将“法”限定为狭义的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在我国还有重要意义。从法治的历史看,法治是在抵制王权擅断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代议机关-立法机关-法律-权威的过程,亦即确立人民意志主宰和决定国家事务权威的过程;民意机关的意志以法律形式表现,此即为“法治”而非人治。当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此处的“法”既有实定法意义上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人为法的含义,也包含超越人为法意义上的抽象法包括自然法与神法,且人为法还需要接受后者的评判与检验,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实证层面,各国在总体上依然确立了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权威,管理国家的过程也是“法”的统治过程,不管这一法律存在的哲学与道德基础是什么。而反观我国的现状,各界包括法学理论界、政府机关及司法实务界对“法”的理解始终未形成明确、坚定、清晰、统一和无误的认识,这并非凭空臆断,而是根源于对现实中一些现象的观察与判断。例如,“依法治国”在实践中作为一种口号不断被扩充和庸俗化其内涵,出现了“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照此类推,“依法治国”势必发展为“依法治人”。果如其然,则“依法治国”这一崇高目标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可悲的自我否定式的悖论,而如此庸俗化与可能的自我否定式的结果出现的原因正是基于意识上对“法”为何物不甚明确而产生的、从而消解“法治国家”内涵的表现。
此外,法学教科书在此方面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翻阅目前的法理学教材,几乎所有有关“法律渊源”的阐述都不加区分地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一概称之为“法律”,并对此不加以说明与分析。也许,在西方,这样的表述并不会产生误解。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议会最终成为国家立法机关曾经经历的艰辛斗争过程,使得上至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清楚地意识到“法律”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认识到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产物,是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但在我国,这却是一个应引起高度和充分注意的问题。因为中国封建传统是有法制的,且有所谓“法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法律体系-“中华法系”。“中华法系”自成体系,源源流长,持续了几千年并广泛影响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但是,“中华法系”在性质上属于封建法律体系,其名称虽冠以“法”,但此法非彼法。无论在理念、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等方面,此处的“法”(经、律、刑)都与西方意义上的法相去甚远。首先,在理念上,封建法律不是人民意志的产物,而是君主意志的表现。在封建政治法律制度之下,君主言出法随。其次,在形式理性上,封建制度没有立法机关,封建法律既不是立法机关的制定法,也没有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再次,在实质理性上,封建法律可以不公开,可以朝令夕改,甚或具有追溯力等。因此,如果将一切人说得话都称之为“法”,则“国王在法律之下”这一经典表述也就失去其意义,而倡导“法治”也与“法家”的严刑峻法没有二致。具体到限制基本权利的问题而言,如果不明确法的内涵与外延,则任何一个规范性文件都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宪法基本权利也就失去其意义。
三、行政法规只具备有限的“法”属性,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或者根据
在孙志刚案的讨论过程中,问题还集中在行政法规可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这就需要对行政法规的“法”属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各国行政机关在实施宪法、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可以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虽然对人民也具有抽象和普遍约束力,但是,由于其不具备法律的形式理性,亦即它并不是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颁布的,故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将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统称为“命令”,以区别于立法机关制定与颁布的“法律”(司法机关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则为“规则”)。如日本、德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并且,将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称为“命令”,有助于与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相区别,亦有助于突出行政的机关特性。
以台湾地区为例,所有行政机关制颁的规范性文件都称为命令。具体而言,命令又可分为外部命令与内部规则,包括法规命令、职权命令、行政规则、紧急命令与特别命令。规范外部活动、有法律授权为依据的又可分为“法规命令”(相当于大陆地区的授权立法),和不待法律的授权,依据其组织法上的职权而制定的“职权命令”(相当于大陆地区的行政法规)。职权命令一般是为了执行法律的需要所制定的,通常是为了填补法律的真空、补充法律的不足所制定的对外的行政命令,对人民也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规范行政体系内部行为,如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长官对随员的规范则为“行政规则”。此外,还有“紧急命令”与“特别命令”。[4]这就是说,按照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性质,三机关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分别为“法律”、“命令”与“规则”。如日本宪法第七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内阁的职权为:“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规定之需要制定政令,但政令中除有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政令即是内阁为了实施宪法及法律之规定而的命令。[5]第八十一条规定:“最高法院为有权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以及处分是否符合宪法的终审法院。”其中法律是指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命令是指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也即政令,规则是指法院的规则。总体而言,行政命令具有抽象性和普遍的拘束力,其具体的名称则有规则、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要点、注意事项等。我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一)规定的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这一权力的根据。但是,在理论上,我国却并未明确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命令”性质。
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虽然具有抽象的普遍约束力,但颁布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命令”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相当程度的专断性,因此,其内容既须符合宪法的一般原则,也不得违反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即行政法规须具备合宪性与合法性,特别是有关限制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除非有法律依据或者法律的明确授权,否则,不得有限制基本权利的条款,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是保留给立法机关的法律所为的事情,此即为法律保留。我国这方面还有许多待检讨之处,行政法规中有大量关于限制公民权利的规定。除《收容遣送办法》以外,其它如国务院制定的《社团登记条例》,关于劳动教养等方面的行政法规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法规之中包含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内容的规定。
以劳动教养为例,劳动教养的实质是行政机关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按照我国国务院197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至四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这一期限与刑法规定的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最低刑期-拘役-的期限15天至六个月要高许多,因此,劳动教养是一种较为严厉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分。我国目前有关劳动教养的依据分别是:1957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由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是由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行政法规,而《试行办法》则属于部门规章。无论是按照行政法治的一般原则,还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既不合宪,也不合法。
法治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只有法律才可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行政机关不可以对此加以限制,其实质是除非经人民自己同意,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可以由行政机关加以限制与剥夺。依法行政原则也要求行政法规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特别是有关限制公民权利方面的内容。我国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这一点。200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此外,国际人权文件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也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这些法律规定都说明,行政机关不得剥夺或者限制公民权利不仅是法治原则的一般要求,也有制定法上的依据。在此情况下,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方面的行政法规就不具有合法性。同时,《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法律规定与本法不符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国务院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明显与本法不符,因此,应按照《行政处罚法》法的规定,修订国务院颁布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颁布的《试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这既说明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法规违反了法治原则,不符合权力分立或者分工原则,不具备合宪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也说明这些限制基本权利的行政法规违反了法律,不具备合法性。
因此,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只是在对人民具有抽象与普遍约束力的意义上具备“法”的属性,它并不具备法的形式理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不可以规定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的内容。具体到限制基本权利而言,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同时具备合宪性与合法性。首先,行政机关必须符合宪法基本原则,如法治原则,权力分立与分工原则。这些原则要求只有立法机关的制定法才可以限制基本权利;其次,必须坚持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原则。前者要求同样的事情,如果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有规定,应以法律优先;后者要求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必须保留给立法机关及其制定的法律。再次,限制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者法律根据。
四、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可否限制公民基本权利?
孙志刚案暴露的行政法规限制人身自由的现象只是冰山之一角,除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以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规与规章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据统计,在该案出现以后,国务院法制局收集了相关法规规章,发现有191个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立法。[6]如北京市、广东省、河北省等都有类似的收容条例。具体而言,这些地方立法就是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它们分别是由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这些法规的内容也有一个合宪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在厘清该问题之前,首先须区分地方性法规与地方规章的性质。
地方性法规是地方立法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其效力只及于地方,且不得与国家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至于地方性法规能否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则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曾就地方自治条例、规章是否可以限制人民权利义务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既是一个法律保留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探讨与界定地方立法机关立法范围与效力的问题。依据法律保留理论,应该以“法律”规定之事项,不得以命令规定。而所谓的“法律”,仅指“中央”或者“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地方自治条例与规章。但是,根据台湾地区以往地方自治实务的例子来看,如果不允许地方对于一些重要事项有独立立法且能够限制人民权利义务的权限,则在自治行政上就无法产生因地制宜的功效,所以,其后“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若地方自治团体欲制订限制人民自由或权利之法,须以自治条例之名义,且限于罚款与其它种类之行政罚,而其它种类的行政罚则限于勒令停工、停止营业、吊扣执照或其它一定期限内限制或禁止为一定行为之不利处分。依据“明示其一即排除其它”的原则,这就是否定其它相关地方自治条例可以对人民自由以及权利加以限制。就地方立法机关立法范围与效力而言,该问题的实质也是地方自治条例不得侵犯“中央”立法机关的权限。各国宪法相关规定一般都可以引申出这一原则:限制人民权利的法律只能由中央立法机关立法决定,地方自治条例不属于法律,无权对此做出规定。如果地方制定了这样的条例,无疑是地方立法机关侵犯了中央立法机关的权能,该条例无效。从两方面的理论来看,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都无权限制基本权利。如果要限制的话,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
大陆地区虽然在理论上不认为下放权力属于地方自治,但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与地方自治条例在性质上并无实质差异,其也是效力只及于地方的,由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地方性法规有其特殊的立法范围,关于限制公民权利的内容不在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范围之内,原则上,地方性法规不得限制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地方性法规不具备合宪性。当然,如果承认地方性法规限制公民权利是开展地方自治或者地方自主的辅助手段,实属必要,那也应该明确那些可以受到限制的权利的范围及幅度。这一问题随着我国地方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活跃,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和必要。
地方规章是指一些地方人民政府的规范本地区事务的规范性文件,它属于行政法源的一种,其效力低于行政法规,也低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7]作为行政法源的一种,地方规章服从行政法制的一般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地方规章不得与法律及上位行政法规相抵触,还特别指地方规章的制定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公民权利的内容与条款,地方规章不可染指。我国宪法原则规定了对地方规章的审查。宪法第八十九条(十四)规定:国务院“改变或者撤消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实践中,以地方规章限制甚至剥夺公民权利的规定时有出现。2001年4月3日,经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商,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文件(渝劳社办发[2001]79号),就重庆市关于养老保险争议的受理问题做出决定: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没有缴纳或用人单位没有足额缴纳养老保险金,由劳动者要求补缴的申诉不属于司法管辖的范畴,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规定对此类争议,劳动者可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举报。该文件的最后还写有:抄送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总工会、市经委。2002年5月14日,律师周立太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向重庆市政府法制办提出了撤消这一文件的相关规定的申请,认为79号文只是行政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却排除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违反了《宪法》、《民事诉讼法》、《劳动法》、《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8]
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第79号文件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根据法治原则,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只能由立法机关依法予以限制和剥夺,地方行政机关不得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诉请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是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地方行政机关不可以擅自剥夺和限制。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只是一个地方行政部门,其所颁发的79号文件在性质上属于地方规章,它无权剥夺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其次,根据法治行政原则,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须有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根据或者授权。如果法律规定或者授权劳动局和社保局可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诉讼权的权力,则它们可以制定这样的规章,而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在制定这样的规章时,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法律授权,这不符合法治行政原则。最后,该文件的制定过程违反了权力分工原则。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是地方行政机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互有分工,二者之间不可以以协商方式,在缺乏宪法和法律根据的前提下,以规范性文件方式剥夺公民诉讼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
结语
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其限制的实务,需要有坚实的宪法理论作为分析与判断问题的理论指南。同时,尽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进宪法,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而是需要进一步认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或者“法治行政”之中的“法”的属性。这无疑是在启示我们,我国的宪法与法治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行固难,知岂易乎?
参考文献:
[1]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368页。
[2]关于“个案性法律”与“措施性法律”,可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364—366页。
[3]参见[英]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4]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38页。
[5]参见[日]三浦隆著:《实践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篇10
在我国,起源于英美日的信用卡系统正在普及之中,各种信用卡的发行数急速增加。目前在市场流通的信用卡有长城信用卡、牡丹信用卡、金穗信用卡、万事达信用卡、维隆信用卡等数十种,信用卡破产的高潮也许很快就会到来。对个人破产的处理也将成为将来破产制度的中心课题。我国历史上曾经对个人破产实行过宽容的免责主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它符合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协力经商的良好传统。我国原来的破产免责主义主要是参考英美的破产法而制定的。现在,在国内法学界也有学者对破产免责主义表示出肯定的意见。[55]因此 ,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破产立法中,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研究世界上有代表性的英美破产法,特别是应对英美破产法的灵魂,即破产免责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制定和利用破产免责制度方面则可同时参考战后日本的做法。一旦我国的个人破产或信用卡破产成为社会问题时,可以考虑引进破产免责主义,对善良但不幸的事业家或消费者进行一定的债务免责,以便让他们尽快获得新生,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繁荣。 (日)加藤正治:《英国破产法的特征》,载《破产法研究》第6卷,有斐阁1927年版,第191页。(日)霜岛甲一:《英国破产法制的现状—续英国破产法的特征》,《判例时报》1975年第319号,第3页。 (日)齐藤常三郎:《破产法及和议法研究》第9卷,弘文堂书房1934年版,第69页。(日)中野贞一郎:《关于美国破产法的免责》,《法学论丛》1951年第3号,第102页。 加拿大破产法第142条规定:个人在破产后的3个月到1年中,破产财产的受托人可以为破产者提出免责申请。免责可以被法院拒绝或中止,也可以无条件或附有条件地被认可。参见A. Mears, D. Flaschen, E. Powers, International Loan Workouts and Bankruptcies.Vol.1,1988, pp.209-210. 在澳大利亚破产法中,免责被认为是破产法的主要目的之一。个人破产者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取得免责:一种是根据破产法第149条,从破产之日起满3年后,自动取得免责;另一种是根据破产法第150条,按照法院的命令给予免责。参见D. Rose, Lewis Australian Bankruptcy Law , 1990, pp.215-217. (日)上原敏夫:《关于西德破产法的修改草案》(下),《判例时报》1989年第694号,第38页。 李永军:《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T. Eisenberg, Bankruptcy Law in Perspective, 28 UCLA L.Rev., 1981, pp.983-985. S. Harris, A Reply to Theodore Eisenberg's Bankruptcy Law in Perspective,30 UCLAL.Rev., 1982, pp.350- 351. L. Zubrow, Creditors with Unclean Hands at the Bar of the Bankruptcy Court: A Proposal for Legislative Reform,58 N.Y.U.L.Rev., 1983, pp.1451. T. Jackson, The Fresh-Start Policy in Bankruptcy Law,98 Har.L.Rev., 1985, pp.1393-1448. T. Jackson,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Bankruptcy Law, 1986, pp. 225-252. M. Howard, A Discharge in Consumer Bankruptcy,48 Ohio.L.J., 1987, pp.1047-1065. &n bsp; (日)伊藤真:《破产免责的再构成》,载《债务者更生手续的研究》,西神田编集室1984年版,第3页。(日)宫川知法:《破产制度债务者更生目的素描》,《熊法》1986年第49号,第327页;同1987年第52号第1页;同1987年第54号第1页。(日)佐藤铁男:《多重债务与消费者破产》,《法律家》1991年第979号,第26页。 (日)栗田隆:《关于破产免责制度》,《民诉杂志》1986年第32卷,第74页。 (日)井上熏:《破产免责概说》,行政社1992年版,第183页。 [12] 耿云卿:《破产法释义》,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500页。 [13] 8 W.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1972, pp.236-238. [14] Dawson, The Privy Council and Private Law in the Tudor and Stuart Periods, 48 Mich.L.Rev., 1950, pp.410-416. Treiman, Majority Control in Compositions: Its Histor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24 Va.L.Rev., 1938, pp.512-516. [15] 1 W.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1972, pp. 470. J. Moore & V. Countryman, Debtors' and Creditors' Rights, 1951, pp.3. [16] 11W.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1872, pp.446. C. Tabb. The Scope of the Fresh-Start in Bankruptcy: Collateral Conversions and the Dischargeability Debate, 59 G. W.L. Rev., 1990, pp.62. [17] K.Lipstein, Jurisdiction in Bankruptcy, 12 Mod.L.Rev., 1949, pp.457-458. [18] J.Conhen, The History of Imprisonment for Deb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scharge in Bankruptcy, 3 J.Legal. Hist., 1982, pp.164. [19] Hunter & Graham, The Law and Practice in Bankruptcy , 1979, pp.121-122. J. Bowman, Halsbury's Statutes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4, 1985, pp.541-548. [20] Fletcher, The Insolvency Act 1976,40 Mod.L.Rev., 1977, pp.194-195. (日)霜岛甲一:《英国破产法制的现状——续英国破产法的特征》,同注第6页、第23页。 [21] 参见J. Farrar, Insolvency, J. Bus. L. , 1980, pp.136-137. C. Schmitthoff, The Reform of the Law of Insolvency, J. Bus. L., 1980, pp.309. [22] N. Aminof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d English Bankruptcy legislation—From a Common Soures to a Shared Goal, 10 Stalu. L. Rev, 1989, pp.129. Lord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 Halsbury's Laws of English , Vol.3(2)(Bankruptcy and Insolvency), 1989, pp.336-337. [23] J. Olmstead, Bankruptcy Commercial Regulation, 15 Har.L.Rev., 1901-1902, pp. 833. [24] V. Countryman, The Dischargeability Law, 45 Am. Bank. L., 1971, pp.37. F. Kennedy, Reflections on the Bankruptcy Laws of the United Sates: the Debtor's Fresh-Start,76 W.Vir.L.Rev., 1974, pp.435. [25] V. Country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Bankruptcy Law, 81 Com. L. J., 1976, pp.299 . [26] Riesenfel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Bankruptcy Law, 31 Min. L. Rev., 1947, pp. 407. [27] Honsberger, Bankruptcy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and Canada, 63 Cal. L. Rev., 1975, pp.1518-1520 . [28] C. Tabb. The Scope of the Fresh-Start in Bankruptcy: Collateral Conversions and the Dischargeability Debate, 59 G. W. L. Rev., 1990, pp. 64-65. [29] J. Koffler, The Bankruptcy Clasuse and Exemption Laws:A Reexamin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Grographic Uniformity, 58 N. Y. U. L. Rev., 1983, pp.53 . [30] T. Sullivan, E. Warren & J. Westbrook, Limiting Access to Bankruptcy Discharge: An Analysis of the Creditors'Data, Wis.L.Rev., 1983, pp.1100-1101. [31] V. Countryman, The Bankruptcy Boom. 77 Har. L. Rev., 1964, pp.1452-1456. [32] J. Sommer, Consumer Bankruptcy Law practice, 1982, pp.6. L. Jordan & D. Warrren, Bankruptcy, 1989, pp.24-25. [33] D. Baird & T. Jackson, Cases Problems and Materials on Bankruptcy, 1990, pp.749-751. J. Ventura, The Bankruptcy Kit , 19 91, pp.83. [34] A. Sullivan, E. Warren & J. Westbrook,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Bankruptcy and Consumer Credit in America,1989, pp.20. [35] D. Baird & T. Jackson, Cases Problems and Materials on Bankruptcy, 1990, pp.1131-1132. [36] A. Rainer, Abusing Chapter 13 of the Bankruptcy Code: The problem of Nonrepayment, 55 N. Y. U. L. Rev., 1980, pp.942. [37] (日)加藤正治:《破产法研究》第1卷,严松堂书店1912年版,第91页。 [38] (日)花冈敏夫:《破产法案与债务免除主义》,东京大学馆藏1918年发行。(日)齐藤常三郎:《破产法及和议法》,弘文堂书房1926年版,第200页。 [39] (日)加藤正治:《破产者解放论》,载《破产法研究》第4卷,有斐阁书房1930年版,第339页、第369页。 [40] (日)三ケ月章:《破产法改正审议会议事录》,载《会社更生法制定及破产法和议法改正立案经过》(一),北海道大学馆藏,第2-3页。 [41] [日]兼子一:《强制执行法•破产法》,风间书房1979年版,第264页。(日)三ケ月章:《破产法改正的诸问题》,载《会社更生法研究》,有斐阁1982年版,第172页。 [42] (日)兼子一:《破产免责的法理》,载《民事法研究》第2卷,酒井书店1977年版,第139页。兼子一:《破产法》,青林书院新社1970年版,第272页。 [43] (日)山木户克己:《破产法》,青林书馆1974年版,第294页。(日)谷口平安:《倒产处理法》,筑摩书房1976年版,第336页。 [44] (日)青山善充、田中康久、宫川知法:《破产免责制度的趣旨与运用上的课题》,《法律家》1992年第1014号,第8页。 [45] (日)经济计划厅国民生活局消费者行政第一科编:《消费者信用的新课题》1984年版,第9页。 [46] (日)青山善充等:《破产免责制度的趣旨与运用上的课题》,同注[44]第10页。 [47] (日)加藤正治:《读清国的破产法》,载《破产法研究》第1卷,严松堂书店1912年版,第105页。 [48] 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023页。 [49] (日)齐藤常三郎:《中华民国的破产法》,载《破产法及和议法研究》第11卷,弘文堂书房1938年版,第118页。 [50] 参见“中华民国破产法草案说明书”,转引自耿云卿:《破产法释义》,同注[12]第447页。吴学义:《中华民国的新破产法》,(日本)《民商法杂志》第2卷,第875页。陈计男:《破产法论》,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18页。 [51] 李傅唐:《破产法论》,正中书局1958年版,第209页。钱国成:《破产法要义》,著作人发行1971年版,第172页。 [52] 参见1982年台湾司法院院字1927号第3项解释。台湾民法第180条第3款规定。李肇伟:《破产法》,著作人发行1971年版,第 237页。刘清波:《破产法新铨》,东华书局1974年版,第262页。柴启宸:《破产法新论》,宏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53] 陈荣宗:《破产法》,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277页。 [54] D. Flaschen & B. Desieno, The Development of Insolvency Law as Part of the Transition Form a Centrally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26 Int.L., 1992, pp.669—670. [55] 潘其:《美国破产法》,《法学研究》1987年第52期,第90页。付洋、吴高盛、刘新魁:《企业破产法简论》,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柴发邦编:《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篇11
论文摘要:市场规制法是市场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本文在对当前我国有关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考察之后,着重论述了作者所界定的市场规制法三大基本原则,即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社会公益原则。论文关键词: 市场规制法 基本原则 国家干预适度 保护公平竞争 社会公益引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决不仅仅是市场机制独自运作的结果,只有靠法律保驾护航的市场才能无“悖论”、才能不“失灵”。政府一方面要给予人们最大限度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为此,首要的是制定民商法等架构,保障私人交易制度得以有效运作;而后还必须建构另外一种法律规范体系以弥补民商法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不足①,使民商法的在此的作用得以正常发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十分相似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法律规范的存在是必要且有效的。美国称之为反托拉斯法;德国称之为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反对限制竞争法;日本称之为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禁止垄断法;英国称之为限制性商业行为法、公平贸易法;欧洲联盟称之为竞争法;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公平交易法。我们称之为市场规制法②。市场规制法是调整在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市场规制法就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认为,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必将为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②。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问题概说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该部门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③,是该部门法的灵魂。当前研究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其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重新整合④、市场规制法律体系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二,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能够弥补市场规制法律规范和条文的缺陷⑤,指导市场规制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以及市场规制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概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市场规制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学者们多是从具体的法律制度研究着手,因而在市场规制法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就略显不足,专门讨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文章就更加寥寥。目前,关于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1、“李说”①,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有四,即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以及维护市场秩序原则。2、“杨说”②,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是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3、“刘、崔说”③,根据该说,各国市场规制法基本都遵寻相同的原则,即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以及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4、“徐说”④,该说认为,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包括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二)研究概况简析笔者认为,上述对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表述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也有些是可采信的。摘要分析如下:1、值得商榷者。如“诚实信用原则”、“自治(自愿)原则”有将民法的基本原则错位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之嫌。按照该原则,市场关系中的当事人在进行市场交易活动时必须具有诚实、善意的内心状况,讲求信用、不欺诈对方等,这是对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及与财产有关的人身关系的基本要求,用于市场规制法对市场规制关系的调整似有不当。再如,“中立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等有将非法律原则认定为法律原则之嫌。又如,“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和“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原则”有将具体法律规范的原则扩大使用之嫌,因为单就上述两原则而言,无一能涵盖市场规制法之全部和整体。还有如,“维护市场秩序”应是市场规制法的一个具体任务,虽然法的原则应该体现法的任务,但二者毕竟不能等同。最后如,“保护国家利益”则是所有法的一般性共同价值目标,并不能确切体现市场规制法的特殊性。作为经济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市场规制法,也当然具有社会本位的性质,它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绝非同一概念(虽 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多数情况下其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相一致的)。2、可以采信者,如“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社会利益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它们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市场规制法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市场规制法的任务,因而是可以采信的。二、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有密切的联系,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来源①。法律原则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②。任何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的确立都应遵寻一定的标准,市场规制法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这些标准应该包括:1、法律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可以作为执法和司法的依据。2、抽象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归纳和演绎出来的一般的具有抽象性的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不是仅顾及那些特殊的、具体的情形和细节。这也就说明了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只作类的调整而不作个别调整,只作高度概括而不作具体规定。3、表征性标准。即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要体现该法律部门的基本内容,反映该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征。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其基本内容的集中体现,也是构建部门法体系的基础。不同的社会关系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的独特性,也是与其它部门法基本原则的区别所在。4、统率性标准。即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应该统率该部门法的具体制度,是其具体法律制度的渊源,它们是纲与目、源与流的关系。市场规制法各具体法律制度只不过是其基本原则的展开。此外,作为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不宜过多,否则纷繁复杂的表述只能损害基本原则的权威性,使之在实践运用中难以真正奏效。基于上述标准,笔者认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有三: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社会公益原则。三、市场规制法三大基本原则解读(一)国家干预适度原则①1、含义。国家干预适度原则,就是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把握适度、得当②。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市场失灵”要产生效率损失,国家干预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挽回这种效率损失。但是,由于国家也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它在干预经济活动挽回一部分效率损失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效率损失。当国家干预能以最低的效率损失挽回最大的效率损失时,就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国家干预,即国家干预的适度。2、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之解读。③首先,自亚当·斯密后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蕴育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经济理念。斯密时代,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因而其经济理论核心是解除对“看不见的手”的禁锢,将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其后,李斯特经济理论充分注意到了国家干预职能的积极作用,但他的国家干预思想实际上主要是贸易保护主义。再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极力推崇国家干预优越性的理论在北美和西欧二战后经济恢复中得到各发达国家的认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后,再推行这种政府意志主导的经济政策,就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了。因此,从70年代开始凯思斯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供给学派正是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诞生的,它主张削弱国家干预,重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迎合了回归自由主义的思潮。总之,这种态势体现出一种弹性变化:反对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宣扬国家干预(李斯特)鼓吹国家干预(凯恩斯)削弱国家干预(供给学派)。与之相应,各国经济政策总是围绕着国家干预这根轴心线上下波动,始终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试图实现对国家干预经济的适度把握。其次,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史暗示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形成。国民经济一体化形成以后,客观上要求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然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时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这使得国家必须干预市场机制,维护市场自发调节。因此,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已成为时代的必然。民法调节经济活动游刃有余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干预成为经济运行的时代特征。各发达国家调整经济运行的经济法律无一例外地围绕着是削弱国家干预还是加强国家干预而有所不同。从市场规 制法来看,因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各国对垄断组织或采用打击、限制或采取扶持、纵容的两手作法;因国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各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与打击方式也有所区别。然而,不论是反垄断立场上的左右摇摆,还是反不正当竞争的大同小异,国家干预经济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度”,“适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度”(干预过度或干预力度不够)则会影响经济前景,十九世纪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变迁暗示人们: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国家干预适度则是经济长盛不衰的秘密。再次,发达国家的经济立法昭示了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的成功运用。以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德为例,其经济立法的发端都是市场规制法,虽然两国的立法实践轨迹不同,但对国家干预适度的把握均较为得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绩效。美国干预市场自发调节的初衷是反对托拉斯,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似乎关注并不很多,或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列入反托拉斯法中调整①,并且其市场规制法的反垄断立场基本上一直未变。德国干预市场自发调节的最早动机是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卡特尔基本采取放任态度,后来甚至转向扶植。二战后才回归世界反垄断的潮流,现在基本形成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并存的立法态势。总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忽视过国家干预的作用,只是干预的出发点和目的因各国国情、所处时代、国际国内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最终目标都是试图通过对国家干预适度的把握,以保障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充分实现。(二)保护公平竞争原则1、含义。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是指,国家要为当事人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使他们能够在相同的条件和外部环境中参与竞争,促进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原则中,我们对公平竞争加上“保护”之修饰,表明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表明市场规制法所保护的公平竞争决不是法对市场主体的一般性要求②,而是从宏观层次追求充分、适度的市场竞争,通过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的竞争以实现宏观的公平竞争①。同时,“保护”公平竞争也表明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义务,表明政府在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时的政策性和强制性,以及法律对国家或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限制。2、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之解读。②首先,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是在市场规制法受命于危难,弥补市场的缺陷、克服民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局限性的过程中确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不正当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化为泡影,经济关系走出了民法所维护的秩序范围,时代呼唤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市场规制法作为一种崭新的法律形式,从创设之初就以创造市场平等竞争条件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己任,它超越了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生活的民法传统,改变了民法对社会关系采取的自由放任的态度,在民法肯定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运用国家之手,强调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世界各国大都以国家干预的方式制定了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这些立法虽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不同而相异,但其精神实质却是相同的。从美国的《谢尔曼法》至今,公平竞争法已途百年,其间也历经修改,但其立法宗旨中渗透的保护公平竞争理念却始终如一。法律原则是对法律价值的反映和提炼,正是由于保护公平竞争这一市场规制法的基本价值目标在人们的观念层次及整个市场规制法的运转机制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将被作为市场规制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次,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作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当然具有国家干预性和社会本位性特征。国家干预性是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最明显的特征。市场规制法在本质上就是国家为弥补民商法调整的不足而自觉地干预市场的产物。国家干预性特征使该原则与民法的平等互利原则区别开来,两者分别代表了社会整体调节机制和社会个体调节机制。社会本位性是保护公平竞争原则的另一大特征。市场规制法保护的既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的市场个体利益,而是同这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社会公共利益。市场规制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通过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来实现的,无论是对垄断结构和垄断行为的规范,还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止,以及对消费者权益的特别保护,都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保护公平竞争原则的这一特征实际上是对国家和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和限制,要求国家和市场主体都必须对社会共同尽责。再次,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在现代经济繁荣过程中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保护公平竞争不再是要完全消除垄断,而是要将 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内市场上非法垄断的抵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要利用规模经济等合法性垄断来克服国内市场上过度竞争的无效性以及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相得益彰。由此可见,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在内容上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初期,这种新变化已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在自二战以来直到当今的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保护公平竞争原则所蕴含的这一新信息正逐步得到全面体现。(三)社会公益原则1、含义。社会公益原则是指,国家规制市场经济生活要以社会公益为基本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说,在国家干预市场,调整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2、社会公益原则之解读。首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市场规制法领域,一切价值判断都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应当贯穿于整个市场规制法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并且是各种市场规制法的法律规范不得违反的。不论是反垄断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原则上都要依据供求规律、市场竞争规律等经济规律,来实现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维护有效竞争,但对符合经济规律却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酿成弊害的垄断和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法律必须加以限制,以保护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有违经济规律却能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必要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法律则必须予以保护和鼓励,如危机卡特尔、不景气卡特尔、出口卡特尔等。从而实现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稳定,最终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同样,在判定一个行为究竟是不是垄断、是不是不正当竞争,应不应该进行规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就是看该行为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这一点,世界各国也都是这样规定的。①其次,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保证社会整体效益的不断取得,始终都是市场规制法所要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自市场规制法诞生以来,它就以鲜明的整体效益价值倾向与传统法律部门相区别,并在协调市场经济中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的矛盾时,以维护社会整体效益为根本指导准则。传统民法理念认为,个体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会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效益,但其调整经济关系的历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无限制的个体效益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导致垄断的出现,市场失灵,扼杀了其他个体的效益追求,最终牺牲了社会整体效益。因而,市场规制法只有在国家干预适度的前提下,以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为宗旨,才能补充民法调整的不足,真正协调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之矛盾,为市场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凡是制定了市场规制相关法律的国家,其立法的首要政策目标无一例外的是要通过禁止垄断、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排除市场竞争的障碍,维护自由、公正、民主的市场经济秩序,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整体效益②。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协调一致,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必然会并且经常会产生冲突,那么“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与“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何者更为先呢?笔者认为,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③结论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和社会公益原则是市场规制法的三大基本原则。首先,它们揭示了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过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的变迁;其次,它们反映了市场规制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市场规制法的价值取向;最后,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法哲学、经济学信息,是极富有弹性的、具指导意义的法律原则。总之,国家干预适度原则是市场规制法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和前提;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反映了市场规制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手段和过程;社会公益原则是市场规制法立法、执法与司法的最高标准与最终归宿。市场规制法的这三大基本原则是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支撑起市场规制法的规范体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三者都相得益彰、缺一不可。Abstract The ma rket regulation law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fter the reviewing of the several representative domestic viewpoints, the author makes a statement on the thre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arket regulation law──the "proper state's adjustment principle", the "equal competition protecting principle" and the "social benefits principle".[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① 民法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调整市场交易关系过程中必然产生诸多缺陷,例如,它是确权法,不是限权法,因而不能通过对行为人权利的限制来均衡各方利益;它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社会为立法本位,因而不能抛弃个人利益而从全局的高度直接考虑社会利益;它是私法,不是公法,因而当交易行为有直接负外部性(即强烈的社会危害性)时,由于该交易不直接涉及特定的第三人,既无法依据合同责任也无法依据侵权责任对其起诉,此时的民法调整或者力不从心或者成本过高,等等。② 即便是国内,“市场规制法”在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公认的、统一的称谓。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为“市场调控法”,即调整市场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为“市场管理法”,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还有学者认为这部分法律规范应称作“竞争法”,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现代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刘剑文、崔正军:《竞争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钟明钊:《竞争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虽然这部分法律规范被学者们冠以不同的名称,但其内涵大都指与市场机制的维护和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笔者认为,“规制”之义并不等同于“管理、调控和调整”,它包含有“规整、制约和使有条理”的含义,表明外部力量对某一事物企图达到一定状态的矫正设计。规制的发生是以规制对象的偏颇为前提的,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市场自身以及民法调整市场的偏离,新的法律规范才应运而生,所以“市场规制法”这个称谓更能精确地反映其所包含的具体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手段及本质。实际上自20?兰?0年代以来,“规制(Regulate)”一词就已反复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法令和学者著作中。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将在论述过程中统一使用“市场规制法”这个称谓。① 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参见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②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讨论与研究从未间断过,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例如漆多俊先生的“一原则说”、邱本先生的“二原则说”、史际春和邓峰先生的“三原则说”、李昌麒先生的“七原则说”等先期的早已为人所共知的成果;再如“国家适当干预与合理竞争二原则说”(参见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10月)、“维护社会整体效益与维护社会公平二原则说”(参见刘桂清、佘胜勇:《论经济法基本原则》,《当代法学》2000年第5期)等最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直接从经济法总论下手,采用演绎法得出经济法的基 本原则,不免流于空泛,说服力不强。笔者认为法律原则的讨论还有另外一种进路,即采用归纳法,先分别对经济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基本原则进行研究,之后再将所有下位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归纳总结和升华,最终提炼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例如,民法的“诚信原则”,起初就只是合同法所遵寻的基本原则,进而成为债权法的基本原则,直至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并最终被奉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这样得到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更具有说服力,因而这种研究进路也应当被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所借鉴。③ 孙国华:《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④ 法律是典型的上层建筑,因而它必然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不断调整自己以与之相适应,在此过程中为之服务。因而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律被打上了深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化,我们必然要对已有的法律规范做大幅度调整,对应有而又没有的法律规范做新的立法尝试,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都要进行重新整合以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⑤ 法应当是确定的和精确的,但在一定时期内,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作为法律载体的语言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立法者即使制订再多的法律,也必然会有遗漏;即使采用再准确的语言,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立法意图与法律文字表现的背离。在实践中,对于成文法而言,其自身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原则来弥补的。① 参见李昌麒:《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页。② 参见杨紫火亘 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③ 参见刘剑文、崔正军:《竞争法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④ 参见徐士英:《竞争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页。①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参见[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② 在法律英语中,“原则”(Principle)有下列含义: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的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布莱克法律辞典》“原则”条,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转引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① 应当认为,这里我们将“国家适度干预”这个学界常用的提法置换为“国家干预适度”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意义的。与英语相反,汉语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将所要强调的部分放在句子的末尾,而将所有的修饰语往前提。例如,“保护公平”强调的是“公平”,是保护“公平”,而不是保护别的什么;相反的,“公平保护”强调的是“保护”,是以公平的方式进行“保护”,而不是以其他方式进行“保护”。具体到该原则中,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适度”,而不是“干预”,国家“干预”经济是早已为经济法学界所共同认可的,当前的任务只是要论证国家干预的“适度”性问题,而不是强调“干预”性问题,因而,应该将“干预”放前,“适度”放后,这种语序上的差别是不应当被忽视的。所以,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认为将该原则称为“国家干预适度原则”更能精确表达其深刻内涵。② 此外,也有学者对该原则进行过另外的解释,认为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切内涵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鲁篱:《经济法基本原则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10月。③ 相关资料可参见李建人:《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山西大学2000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① 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12——14条, 对虚假广告的规定。② 譬如民法的公平原则,它只要求稍稍超出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之形式平等,在微观层次上略微实现某种实质的平等。① 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双方企业和股东皆大欢喜,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由微软对Intuit注资,并由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获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份额的Quicken软件。就此交易本身而言可谓平等互利、公平绝伦,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后微软会独霸全美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挫败了此项交易。参见:《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Intuit之举提交法院》,《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第39版。② 相关资料可参见赵剑飞:《试论保护公平竞争原则》,山西大学2001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① 过去只讲国家利益,而将社会利益包含于国家利益之中,这是过去“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反映。只知有国家,不知在国家之外或之上,还有与之并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和社会利益,社会的一切由国家代表或包办,社会淹没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之中。虽则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二者利益不能等同。象自然资源与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城乡公共设施的兴建与维护,社会医疗卫生、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安置以及社会互助等,都是相对于国家和集体、个人的特殊的独立的利益形态,即公共福利。确认社会利益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并在立法上予以单独保障,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国家过多负担社会事务,或过多干预乃至侵犯社会利益;一方面也可防止或遏制某些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非法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② 比如,我们在具体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或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范的过程中,有时是纯粹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但有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对外政策或者国内各地区间、各民族间利益协调等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到此种立法将对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产生何种影响等道德上利益的得失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得失问题。① 英国法官麦克奈顿勋爵在1984年的一个判例中对贸易限制问题的阐述就表明了这一点:“一切贸易限制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无效的,这是基本原则。但也有例外,在某些具体案例的特殊情形中,贸易限制和对个人行动自由的干扰被认为是正当的。其前提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贸易限制是正当的,如果它既对缔约各方有益,也对公共利益有益,事实上这也是唯一的理由。”这个判例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公共利益的概念已成为控制贸易限制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陈有西:《反不正当竞争法律适用概论》,1994年版,第150页。②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德国1989年戴姆勒—奔驰和MBB的合并案。德国联邦经济部长以合并改善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批准了一个大象联姻。其理由是,合并将使戴姆勒—奔驰承担对MBB研制空中客车的财政资助,促进MBB公司的私有化,将国家在研制空中客车中所承担的风险和费用逐步转移给企业界,从而减轻联邦财政在这项常年支出中的沉重负担。据估计,到2000年,联邦政府因此可减少50亿马克的财政支出。此外,该合并还可加强德国企业在航空航天领域,特别是在空中客车的生产和研制以及在军备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案例引自王晓晔:《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问题》,1996年版,第115页。③ 例如德国的Thyssen/Hueller合并案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Hueller是一家出口外向型的有限责任公司。从1973年以来,这家公司出现了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甚至不能按时交付职工的社会保险费和企业所得税。因此,它急迫想接受一个有潜力的康采恩的兼并。1975年,Thyssen 股份公司取得了Hueller有表决权的全部股份。因为 Hueller有限责任公司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Thyssen康采恩又有着雄厚的财力,联邦卡特尔局认为,这个合并将会显著加强Thyssen集团在相关市场的市场支配地位,从而禁止了这个合并,1977年,这两个企业向联邦经济部长提出了合并申请,联邦经济部长对此给予附条件的批准。所附的条件是,Thyssen股份公司最多只能取得 Hu eller有限责任公司的45%有表决权的股份。联邦经济部长解释其批准理由时指出,这一合并不仅可以保住Hueller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的就业机会(典型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笔者注),可以使这个有着不寻常技术潜力的且以高技术的专业队伍装备起来的企业继续生存下去,而且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考虑到联邦德国对出口有着很高的依赖性,也不能放弃这个高效益的企业。在这个案例中,保证职工的就业机会被看成是维护整体经济利益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德国的?梦榷ㄔ龀しǖ?条,高就业率是德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案例引自同上王晓晔书,第113页。
篇12
一、法制与法治
“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对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在我国,“法制”的用法首见于《礼记•月令》:“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邪。”此处所谓法制,乃指国法、或典章制度,强调法律制度的形式意义。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只要是国家(或官府)创造的,即使是酷法、恶法,或专横之法,也属法制,具有一律遵守的效力。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制不过是人治之下的一种法律统治形式。这种人治之下的法制(“专制的法制”),与近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法制(“民主的法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近代意义的法制概念及思想,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它强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和遵守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界对“法制”这一概念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基本观点有三种:“一种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法律制度’;一种从动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严格遵守执行和遵守法律与制度,依法进行活动的一种方式,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体;一种则简化为依法办事的原则,即一定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国家管理的原则。”③从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学者趋于赞同从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将其定义为,“所谓法制,是一国法律制度的总和,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合法性原则、制度、程序和过程。”④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对法制的含义的解释,都是和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的,如有的主张君主立宪制,有的主张三权分立制,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制,有的主张“议会至上”,有的主张自由,有的主张福利国家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对社会主义法制如何界定?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社会主义法制即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环节的统一,核心是依法办事。其基本要求为“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关的。
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概念。在西方学说史上,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最早论述法治问题。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⑤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人们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讨论法治问题,而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依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其内容大体包括:法律至上,权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开;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权利和自由;实行正当程序。二战以后,在国际上,法治的思想和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了三项原则,即立法保持“人类尊严”,防止权力滥用、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可以看出,法制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不可或缺。其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综观法治一词的使用状况,其具有如下意义:它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方式、依法办事的社会状态、一种价值取向或一种政治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的、原则、制度和。”⑥其基本内容包括:“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⑦
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追溯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在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之上形成的,“废除旧法和对旧法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辩证。”⑧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法制”被确定被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⑨然而,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停滞和落后,同时也导致“特权”的急剧膨胀。“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⑩之后,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最终被叶利钦窃国期间,其法制建设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则无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前苏联被葬送掉。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法制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时期”。11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观轮廓予以确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随之,1957年“反右运动”,停止了继续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从而宣告了法制大转换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滞和大滑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十年法制建设的总纲领和总目标才得以确立。同时,形成了以多样化的法律价值、法律的主导性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为特征的党的法治观。12
三、社会主义法治——法制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论探索有着较为漫长的过程,其既体现了我党的孜孜实践,又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1.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需要我们的法治。”13然而,其对法治的进一步内涵并未申明。
2.从同志到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异同和发展。
同志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为主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运动,在“”中发展到极端,使“”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还革“法制命”的大灾难,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目标性机制的重大作用,仅把其当作一种手段。14由于这些思想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了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
3.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实践
邓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17这预示者: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发展过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及价值标准来看,具有: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18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也应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为依托,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从法制到法治——性的飞跃
(一)性向传统的突破。
主义法治建设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传统。在我国历史中,一直未出现以商品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法制的“专制”,使人民从心理上疏远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语。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主张走法治之路,但终是自觉不自觉的蒙上“人治”的色彩,的十年浩劫,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设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准备了基本备件,如法制体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学界在立法中的广泛参与,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大转变等等。
1.对“人治”之彻底否定
“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19人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法制”侧重于静态制度的描述,虽然也有动态的内涵,但其终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中,出现了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威,而造成众所周知的许多恶果。“法制”与“法治”虽一词之差,但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对“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20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也是柔性的、劝导性的;其维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会、风俗环境熏陶、道德榜样感染、社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则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律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因而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强制,也是刚性的。可以看出,法治与德治作为两中不同的社会治理方略,各有其特点。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其本质要求统治者要爱人,方能使国家大治。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后,同志紧接着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将“德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两种治国方略并用,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这既是对“德治”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
3.对党的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从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国家的政权得以稳固以后,如果将党的地位再置于法律之上,那么难免会出现唯党的意志是从的局面,长官意志将成为最终的权威,发展的结果是党内部的严重腐化,苏共的发展结果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强调“法治”,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是,党仍然须作为一般的政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邓小平同志曾说:“美国有个尼克松,日本有个田中,都得上法庭,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不能上法庭呢?党组织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执政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则,社会之中就存在一个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特殊集团,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荡然无存了。”21由此看出,邓小平同志肯定了法律的最高权威,法治核心之一的法律至上原则。这可以看作是邓小平中“民主法治”思想对我党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的十年是唯党意志的十年,甚至出现了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经法定的任免程序的情况。如果在“法治”的建设中,没有对党的领导方式进行明确界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或许又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二)现代化向“西化”的突破。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由于先天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22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形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3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来说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24所以,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一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议,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种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法治原则。25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方式处理事务。26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27
社会主义法治在中国传统的背景条件即如上所述,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法制现代化发展中,既体现对西治文明的继承,又在本土条件下,完成了质的飞跃。
1.对资产阶级现代法治思想的移植。
现代法治思想根源于西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能完全排除“西化”的倾向。在以“法制”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基本是排斥“西方”的,仅将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层面,而未当成一种价值追求、治国状态。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法学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会主义法治在某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化法治思想。譬如,著名的法学理论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的思想中蕴含着许多现代化法治的理性的东西,其“人民”、“法律至上”、“社会契约”、“权力制约”等主张包含着相当的合理内核,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财富,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对其优秀的成分加以承继,并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扬弃。由于西方法学家和社会实践者的合力,使得西方的法治思想具有了取得广泛认同的基本内涵,而这种以民主为基础的法治思想正是社会主义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或缺。
2.结合本国实际的重新定位。
“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化,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的法律变迁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法治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28这样,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着本土化和国际化(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重构自身法治文明的要求,同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先进法治文明之后,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再定位。
⑴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基础。“大家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理性文化是法治的文化基础。”29由于“中国领导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法治融入了下列因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并且市场的成分在逐步增加,但较之其他经济制度,国有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对人权的理解上强调稳定,主张集体权利优于个人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可以看出,其社会基础包含如下因素:
a.“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推进力量。1987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成效,这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深刻性和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源泉。”31
b.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有力政治保障。没有中共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其仍然是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
c.中西人文精神的合璧:重构法治的精神基础。同志曾在五十年前说过,“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32这启示我们: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在内的一切制度都是以彻底解放人作为最高宗旨的,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相依相生的关系。黑格尔也说:“历史对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历程,法律所表现的风格、礼节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33社会主义中国在法制建设中,在反思自身历史的同时,在人文精神方面,应吸取西方之长,以补己之短,达到精神文化及理性文化的交融。
2.社会主义法治的标准和要求。总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立法上讲,建立民主合理的立法秩序,立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最核心的是:
a.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34其构成包括“内在品质要件:公民权利神圣和外在形式要件:规则至上。”35法律至上原则是内在品质要件和外在形式要件的统一。有学者更指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更重要,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36所以,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党派、社会组织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
b.权力制约原则。在国家机关之间建立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权力制约的理论不能不深入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讲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讲了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另一方面也讲了党权与政权要分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37无论是、,还是广西玉林四个市委书记“前腐后继”,从制度上看无不是因为权力太大,没有制约机制造成的。所以,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应该对权力的监督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
c.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共同特征。其含义是赋予法官以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的独立的自由裁判权。在“法制”的背景条件下,虽然赋予司法机关以独立的地位,但实际上司法机关成为其他国家机关的附庸,在人事任免、财政制约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职能无法依法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其他国家机关的特权思想。在“法治”的背景下,应当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司法制度,同时,对一切由法官说了算的职权主义司法制度依法进行监督,防止司法专横。
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过程,并无所谓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我们践行的差异。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行的发展历程,既要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又要结合社会的广泛参与,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等仍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下的法治进程会有序展开。
及注释:
①《从法制到法治》程燎原,出版社2000版
②④《法•宪法》舒国滢、周叶中编审法律出版社2001版
第95、102页
③《法理学》李龙主编武汉大学1996年版第214页、第239-240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学》商务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⑥《法理学》葛洪义主编政法大学1999年版第258页
⑦《法理学》蒋晓伟主编同济大学1999年版第266-269页
⑧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17页
⑩《苏共亡党十年祭》黄苇町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02年第3期第95页
1114《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刘作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第138-145
12《法治论》王人博程燎原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第292-294页
13《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夏禹龙、顾肖融主编重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页
15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332页
16《略论中国法制化的指导》沈晶载于《行政与法》2002年第1期第25页
1718《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张文显载于《法商》2001年第1期第35-36
1920《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焦国成载于《中哦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6
22232425《现代中的法律》(中译本)[美]昂格尔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86、96页
26《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译本[美]高道蕴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
27《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杜宴林原载《法制与社会》(长春)转引在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2年第4期第27页
29《中国法治与行政立法改革》[美]裴文睿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9页
31《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刘瀚原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转引在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2年第2期第22页
33《》黑格尔著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34《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王利明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篇13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加以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努力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田克勤:《邓小平理论概论》,高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教育部:《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童星:《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处版;
[6]赵洪海:《中小学素质教育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