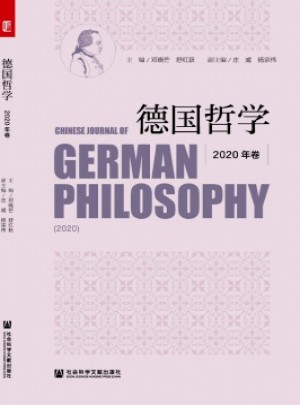哲学人生论文篇1
二、人生鹄的
哲学人生论文篇2
1 探究生命和人生的真谛
周国平说:“人生最重要的是充实,不管你感到的是痛苦还是幸福,人生应该是有内容的、充实的人生。”于是,他用文字记录了自己一段段人生经历。
周国平的散文中满溢着对生命的敬畏感,他鼓励人们要积极地面对人生,要饱含热情地好好活着。他认为人生或许是徒劳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正因为这样,回过头我们再来看《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时,生命的悲欢离合,借助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以妞妞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凄美娇艳的生命得以深刻地表现了出来,这不仅仅是痛苦,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种永恒的渴望。
周国平不过是用文学的方式在谈哲学,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中,所表达的感悟仍是围绕着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意义、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和超越等等。
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谛与哲学的关系,这是周国平一生所追求的;而生与死,正是这两种思想的终极命题,让周国平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人生和生命过程中的哲学意义。把情感升华至哲学的高度,把哲学融入情感世界之中以文学散文的形式阐释出来,如果用泡一壶茶来做比喻的话,哲学散文是那沸腾的水,其间所包含的思想就是那浓郁的茶香。这样的表现方式,使得哲学思想增强了理趣,哲学也将变的深入浅出,人生的意义得到升华,生命也因此得到人们的重视和珍惜。
2 生活化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书对改变读者的精神结构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过,使周国平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以诗和哲理一样的文笔,深入生活的哲理散文:充满了对生活的悲欢离合的哲学思考,荡涤着人们的心灵。
我们只要留意那个时代处的周国平对哲学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周国平的哲学散文所具有的独特艺术特色――生活化。
“哲学的写作可以分为多种,其中一种写作是学院式的,喜欢资料的收集和堆砌。这里不需要感性语言和形象思维,不需要与当下的结台,而更在意哲学的历史性,文章的抽象程度越高、术语的密度越大,这个人的思想就越坚实和丰富。还有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文风活泼,并融人了鲜活的生活场景,它常化艰深为乎易,如细雨滋润万物一样,发生得悄然而广泛”。
他的散文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的哲学散文是众多写作方式的融合与升华,形成了他独特的写作特色,他的哲学散文和纯学院不同,更侧重于把哲学生活化或者应用化,然而并不是刻意去生活化。他的哲学散文也包含了哲学学术,因为哲学是一个知识积累和整理的过程,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也需要知识的搜集和整理,但是哲学如果仅仅是以学术的方式出现,这就是离开哲学的根本了,所以周国平的哲学散文就采取另一种表达方式,把哲学学术和现实生活相联系,脱离了哲学家和散文家的界限,把对生活中的欢乐、痛苦、还有坚强和执着等等生活感悟通过哲学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
周国平说:“研究哲学,其实有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要对哲学有种领悟的能力,没有领悟的能力也可以做学术,但我可以肯定你不会有大成就;另外一个就是学者的功夫了。你首先要选择你的问题,哲学的看法必须是以问题为主,问题是核心,你要找出哲学中什么问题是一个重要却多年来没能弄清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让你产生兴趣,然后你要发挥你作为学者的功夫,把古今中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找出来,去收集整理资料,看看这个问题有哪几种论述方式,然后你要进行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不难发现,周国平可以让他的哲学散文深入生活,做到哲学的生活化,和他亲身去收集哲学资料,认真的学习,刻苦的钻研,系统的分析是分不开的。然而,这些只是基本条件罢了,最关键的是在这些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周国平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对所遇到的人,所碰见的事,所观察到的现象,所听到的话中,都加入了哲学的思考,透过现象,认清事物、现象等等的本质,并加以理论化的总结,从而,得到生活的真谛,这些哲学认识都是和日常的生活密不可分的。
3 展现真性情
他的散文或平实或素雅或优美或哲理的文字中所透露出的个人的思维光辉的东西,或者个人魅力,让人着迷。特别是他在散文中流露出的真性情。可以说,在人心灵最微妙的地方,大都是注重性情的。不管你是有名的文人,还是无名的老百姓。性情,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思想;性情,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性情,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形象。
“我没有任何办法留住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只能把它转换成所谓的文本,用文本来证明我们曾经的拥有,同时也证明我们已经永远的失去”。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智性与情感生活,是一部完完全全的真性情的表露。这本自传包括两条主线,一是智性生活,一是情感生活,二者大致体现了周国平的个性面貌,也表现了作者的性情。
文人大都是性情中人,周国平也不例外。做一个性情中人不难,但做一个诚实的性情中人却很难。“我唯一可以自许的是,我的态度是认真的,我的确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周国平先生,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一个敢于面对自己的哲学家,他不回避,不隐藏,而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同时,坦然用哲学散文这一形式记述着全部的经历。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我们的家庭关系,从表面看是稳定的,其实像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因此,多少对看起来情投意合的夫妇,一时间离婚的传说满天飞,可是不久,当妻子讲起丈夫或丈夫谈起妻子时,又变得那样柔情似水”。在周国平的文字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周国平是客观地公正地看待这一切,所以我们读到这些内容时,感受到最多的是温情,是默默的温情,充满感激之情。
在周国平哲学散文中有这样的观点“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他就会和世俗的竞争拉开距离,借此为保存他的真性情赢得了适当的空间。而一个人只要依照真性情生活,就自然会努力去享受生命本身的种种快乐”。
性情,则是一个人的性格的外在表现。在周国平哲学散文中,看重的是生活的意义、内心的感受,这就叫“真性情”。不管是为人还是为文,这都是他最看重的。穿梭于周国平语言与文字上,在素面朝天的文字里面,我们能缅怀到
一些欢乐或疼痛,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和收获,我想这也只有周国平的真性情文字才能做到吧。
4 哲学思想的自我消费性
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中有着类似的观点:思想,是具有“自我消费”性质的东西。
在周国平的哲学散文里,哲学思想首先是他的爱好,也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学者周国平本人就是一本书,那么他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就是周国平。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哲学家,开始都不是为了一定要弄出一个经天纬地的理论而进行研究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明白些生活或人生,是缘于对思想和理论本身的兴趣和魅力,而全身心投入到某个领域的。可以说,人类历史上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是思想家在不经意间发现的。尼采的《看哪这人》,卢梭的《忏悔录》,再到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与其说是写给世人看的,倒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文学艺术领域里有这样一句话:思想也是是自己的,然后才可能是大众的。
哲学家和思想家,并不一定都有系统的理论和著作,甚至“不一定要拿出作品来,哲学家本人的生活和生命,就是哲学本身”。
尼采就是一个典型,他被许多人列为20世纪哲学巨匠之首,可尼采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几乎没有一本专门的哲学著作,其大量作品是一些警句、格言、随笔、杂感等,可以说既无体系又无范畴,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形态作品的人,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在20世纪,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一个主要哲学流派,跟尼采的名字没有关系;也可以说,在20世纪,几乎没有哪一个重要人文科学领域,没有尼采思想的影响。
孔子,一位影响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思想家。我们也找不到他的系统的哲学著作和理论文章,几乎家喻户晓的《论语》,还是其弟子们整理的一些他的“只言片语”和对话,可是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力量和影响,没有一部哲学书能与孔子的这些“只言片语”相比,没有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人们的思想,对一个国家甚至对世界的影响,能超过孔子的。
在思想的自我消费、享受上,周国平和希腊的尼采,古代的孔子是一致的,周国平的生活岁月形成了他独特的性情,这种性情本身就是哲学,比那些所谓的貌似高深的哲学要深刻的多。他是站在上帝面前,讲出自己的所思所想的,他那种“倒着活”的思想很让人震撼。
哲学人生论文篇3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哲学人生论文篇4
一、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及其现实关照性
叔本华告诉我们:“在本质上,人生就是一个形态多样的痛苦、惯常不幸的状况。”在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宿命论和决定论的基调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得出他对人生的参悟、洞悉和明察。这一绝对到让我们不敢报以丝毫怀疑态度的坚定陈词,开启了我们隐蔽的、被驱逼已久的灵魂,带领我们去挖掘思想体系中几近消失殆尽的精神援助、自我确认和解脱以及反省启蒙。尼采曾经这样评价叔本华:“你想知道叔本华对我的帮助吗?他使我有勇气并自由地面对人生,因为我的脚发现了结实的地盘。”
在他的世界里,人的生存意志,就是一种欲望。生命意志束缚了理性与行为,肯定了无止境的欲求。一方面,人在争夺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欲望的满足,而当一个欲望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欲望,人总会有新欲望的产生,所以就一直处在不断的痛苦之中。另一方面,当人的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因此,不管欲望是否得到满足,世界对于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人生就是在痛苦和虚无这二者之间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当你需要为生存而劳作奔波时,你是痛苦的;当你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你就会感到无聊。”这就是叔本华的钟摆理论。
叔本华是一个把人生看透了的人,他对人生的分析鞭辟入里,直抵骨髓,也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做到如此。当然看透人生的人不止他一个,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用独立的哲学体系阐释出来。叔本华终生未能当成大学教授,而是以“个体户”的身份从事哲学研究的。正因如此,他的著作少了许多晦涩与玄奥,多了几分明快与清新。也正是在这种明快与清新中,他对我们的生存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准确的透析的揭露。
二、叔本华“宿命论”、悲剧文学和作家宿命一脉相承
叔本华给我们勾勒和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悲观和宿命的生命图景。生活对我们的许诺如此之多,然而真正履行的又寥寥无几。在这一世上,无论是谁,都得为自己的存在遭受惩罚。许多人一提起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就通常认为与其性格有关:愤世嫉俗、傲慢狂躁、狭隘自私、孤僻冷漠、偏执少爱。因此他的思想经常受到排斥,特别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通常将其论调归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化身。但实际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绝不是失望无聊颓废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哲学的智慧的悲观主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具有反省人类自身、提示人性自身局限、关注人生自我拯救功能的作用,基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私和贪婪本性,从个别到一般而引起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不妨回到悲剧文学和文学家的命运这两个视角当中,在这里他的观点又何尝不是得到了切实的认证。
文学家多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敏感的发现,因此更容易看透人生,从而想通过文学这一角度在心灵的层面去消除和解决问题。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岁月中,悲剧一词始终都是漫漫文学长河中无法被替代的一种文学样式,悲剧文化现象是人类创造中最具魅力的部类之一。那些悲天悯人、呼天抢地的悲剧作品,一直被视为雅正而崇高的体式,被称为艺术海洋中的艺术之冠,文学宝山中的文学之塔,是一切文学艺术和全部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是全部人类心理与生存状态的直观呈现。
文学的目的在于推动我们的想象力,为我们启示“观念”。换句话说就是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生和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成为一名文学家的先决条件是首先要洞悉人生和世界。他的见解深刻与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作品的深度。真天才和大作家们往往要陷入一段长期的绝望生活。文学和人生有着近亲联姻的关系。文学就是人生的写照,文学中反映出人的宿命,叔本华的诸多观点都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得到了证实。人为了揭示宿命而创造文学作品,人看透了宿命所以企图从文学中寻求解脱。比如,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一生对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研读不已,并深受叔本华悲剧意识影响,认同近代科学思想上的怀疑派论调,悲观宿命的人生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本是一个集美丽纯洁、善良质朴和仁爱容忍于一身的少女,然而在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无情的践踏后,不得不饮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正如说本华所说:“我们总是生活在一种期待更美好的状态之中,同时又长长后悔和怀念往日的辰光。”道路的坎坷和曲折是一个既定的并且恒久的事实,当很多作家发现通过文学表达的方式也不足以消除心中的苦闷,不足以改变人生的悲剧终结时,便选择了自杀。纵览古往今来风云叱吒的文坛,已有多少才子佳人因为文学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海明威,老舍,傅雷,杨朔,三岛由纪夫,海子,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毛,顾城・・・・・・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文学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不能治疗人沉浸在痛苦中的感受。文学家本身的实际生命再一次证明了悲剧文学和人生宿命是互相映射的关系,文学作品(包括悲剧和喜剧)证明了人的悲剧宿命。
三、对悲观人生的解决之道
叔本华认为人类为了摆脱痛苦而不断地寻求解脱的方法。解脱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意志的暂时否定――艺术;二是意志的绝对否定――禁欲。艺术正是人类获得精神上暂时解脱的最好方法。真正的艺术是超功利性的,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着都超出生存意志和功利主义的要求。艺术的作用在于使人获得短暂的解脱,尤其是作为诗的顶峰的悲剧和作为艺术最高形式的音乐。
那么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应该怎样具体地改变悲观主义宿命对我们的影响呢?首先,人要获得自主闲暇,但又不觉得无聊,必须自愿节制欲望,随时养神养性,最好的方法就是艺术创造。这个艺术创造不是为了某种商业目的或是利益,而是纯粹的艺术。其次,懂得遗忘。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当人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财富和时间后,往往更容易生出很多事端来。再次,学会孤独,叔本华认为孤独是天才者的表现,是一个人内心丰富的象征。一方面可以减少交际带来的无聊,另一方面避开和那些讨厌的人见面,更少地引来敌意或者恶毒者的攻击。
哲学人生论文篇5
[4]王中江,高秀昌.冯友兰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丁灵平.从中国哲学的精神追求看中国哲学之特点[EB/OL].百度文库,2011-03-04.
[6]辞海编写组.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7]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哲学人生论文篇6
什麼是「生命的意義
在探討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之前,首先必須要澄清的是究竟什麼是「生命的意義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在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也不是在問「生命是什麼。「生命是什麼是有關「生命的本質是什麼的詢問;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是在追問「生命本身有什麼意義。本文所要探討則是「生命的意義本身是什麼。人的「生命從人類受胎開始就已經存在了,但是「生命的意義並不是始於人的受胎成形,也不是天生現成的,而是人在有所自覺之後才開始自己構畫賦與的。誠如諾齊克(Nozick)所說的:「生命的意義:一個人根據某種總體計畫來構畫他的生命,就是賦與生命意義的方式;只有有能力這樣構畫他的生命的人,才能具有或力求有意義的生命。(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2001,頁596)「生命的意義是人類自我所賦與的,是在人們根據某個總體計畫,或者說是依照某個總體的生命藍圖來構畫自己的生命方向時才賦加上去的,也就是說隨著每個人所選擇總魯生命藍圖的不同,所構畫出的「生命的意義也有所差異。在這層理解之下,當我們面對生命,或許不必先急著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要先問:「人應該如何賦與生命意義,或者說:「人應該如何去構畫出生命的意義,只有人們開創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而後才能去追問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去對人所建構出來的生命意義進行肯認。因此不必惋歎生命沒有意義,畢竟「生命的意義是在每一個人如何去構畫自己「生命的活動中賦與的,責任在每一個賦與生命意義的人,只有人們去構畫自己的生命,並努力成就自己的生命,生命才活出了意義。
如何活出有意義的生命
一個人想要活出生命意義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要自我立定志向、目標去找尋一個總體計畫或是總體生命藍圖,依照這個總體生命藍圖去構畫自己的生命,同時能夠貫徹實行自己的構畫,才能活出自我生命的意義。一個有的人可能會根據宗教的計畫來構畫自己的生命,並活出具宗教意義的生命;一個注重傳統的人,可能選擇根據傳統的計畫來構畫自己的生命,並活出承襲傳統的生命意義;一個凡事要求合理化的人,可能根據各種不同的理論模型來構畫自己的生命,過著他所認為的合理的生活;……。無論我們從事什麼樣的選擇、找到了什麼樣的總體生命藍圖;然而依照該計畫來構畫生命,進一步活出有意義的生命,並不是件簡單的工作。因為總體生命藍圖不是現成的羅列在眼前,任由我們隨意去評比揀選,就可以對我們的生命活動產生影響力的;總體的生命藍圖必須要內化為自己堅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才能影響生命的方向。
一、總體生命藍圖的內化與建構--一種永恒的追求
總體生命藍圖在內化為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的過程中必須經過漫長而艱辛的磨鍊:人必須經過一段不斷選擇、結構、解構、重構的接受過程。這個內化的過程從人們還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從我們開始會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去詢問「為什麼並努力找尋解答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從事一種建構的謀劃,至於說要到人生的那個階段才構畫冗成滿則不得而知,或許可以說人終其一生都在構畫一個總體而完整的生命藍圖,這是人終極的追求。這並不是說要構畫完成一個最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人的生命才有意義;事實上,隨著個人生命的成長與發展,隨著個人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之增廣,個人所構畫出的總體生命藍圖有其廣度及深度上的差異,每個階段的完成,對個人而言都有其階段性的意義;只不過對一個追求成為完備的人而言,永遠不會停滯於現階段的完成,因為他明白只有不斷地開拓總體生命藍圖的廣度與深度,個人的生命意義,才能不斷地開展。總之,內化到個人心中的總體生命藍圖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是開放的,一個可以不斷擴展與加深的內在世界,所以人與其說是在找尋一個總體的生命藍圖,不如說是人在心中不斷地調整與構畫著一個較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而正是因為這個永恒的追求,使人生命的意義具有了無限開展的可能性。
二、建構內在總體生命藍圖的重要性
人究竟該如何在心中建構總體的生命藍圖呢?簡單地說,就是「即事而問,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中,不斷地去扣問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及問自己「為什麼如是存在、「為什麼展現如是的生命現象並積材地去找尋解答。在人生過程中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問「是什麼,與問「為什麼是兩個不同的發問。「是什麼的發問,主要意味著我們想要進一步瞭解所遭遇到的事物本身的結構如何?這個事物本身有那些特性?這個人事物本身之所以為人事物自身的本質又是什麼的問題;而問「為什麼的問題則並不只是想要去認識人事物本身是什麼而已,「為什麼的發問是人們企圖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進行解釋與理解,企圖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納入到他個人內在意義世界時的一種提問。接觸過小孩子的讀者,大概都領教過他們每事必問的工夫吧?!一連串的「為什麼時常會問到大人們無力招架,或感到困窘,甚或有時會因為不耐煩而惱怒。小孩子真的是每事必問,這為什麼這樣,那為什麼那樣,何止十萬個為什麼!孩子這一連串「為什麼,意謂著在孩子的小腦袋瓜子裡正在尋求一個解釋、一種答案,以便去編織一個對自我而言充滿意義的世界,他必須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一一在他腦袋中加以編碼連結,使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都能納入到他意識中原本已經自我建構的意義網絡中而得到安頓與理解,才會使孩子暫時的停止發問。若是面臨到無法理解的人事物,也就是無法將現實中所遭遇到的人事物納入原先已經構成的內在意義網絡,孩子們就會又開始進行這個「為什麼的提問過程。在詢闆與找尋解答的過程中,孩子不只是將獲得的答案納入一己原先構畫的網絡中,同時也開始去對原先建構起來的意義網絡進行解-相應新的人事物,調整自己原本建構起來的意義網絡,直到重構出一個可以將所遭遇到的、新的人直物一一納進來的意義網絡為止。這個相應於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不斷地追問「為什麼並找尋解答的過程,並因此而建構起來的內在意義世界,就是一個已經內化為個人世界觀、人生觀或人觀的總體生命藍圖。
人的真實生命是在與情境的互動中展開的,相對於人的內在世界,外在世界雖然是被給與的,但是外在世界也必須被人的內在理智所掌握,並稚有經過人的詮釋才能被人理解。人雖然是世界的一個部分,但是人必須經過不斷的與世界交往互動,並經過人不斷地去向世界追問「為什麼,從而為自己的提問找尋答案,再三琢磨確認,才能消除內心對世界的陌生感,有了這種確切的認知,人在生存世界之中,才能逐漸獲得一種安居其中的熟悉感及確定自己該如何行事的方向感。如果仔細觀察,或許會發現當孩子們面對新的環境,接觸新的人事物時,「為什麼、「是什麼的發問特別多,多到令大人們覺得有些聒噪了,換個角度想想,似乎這也意味著這個孩子急著重構自己內在的意義世界,因為他原本建構起來的內在意義世界,無法安置所面臨的哀的人事物;孩子的聒噪,顯示了孩子無法將新的人事物納人內心意義世界時,內心引發的焦慮不安,及不知所措、失去行動方向感的困窘。所以說對所遭遇到人事物去追問「為什麼的問題,並找尋解答的努力,絕不只是哲學家們無聊的思想遊戲而已,基本上這種活動,是參與生存世界中的人,企圖在心中構成總的生命藍圖,活出生命意義的嚴正活動。有意義的生命,意味著我們可以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都轉化成為可理解的,並且能運用在實際生存情境中,去獲得一種熟悉戊及決定行動的方向感,讓人安居在生存世界中而不致焦慮不安、不知所措。
三、建構內在總體生命藍圖的可能方式
如前所述,人是在日常生活的遭遇中,不斷地去扣問「為什麼並努力找尋解答的過程中建構起生命藍圖的。根本而言,找尋解答的方式非常的多,比如我們問說:「為什麼我會感到痛苦?一方面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提出生理學角度的解釋,亦即把痛苦當作一種生理現象,並去描述痛苦的生過程;另方面我們也可以提出宗教上的解釋,將痛苦解釋成源自人本身的無名;或者也可以從心理的角度來理解,將痛苦理解成是某種心理狀態;……總之,找尋解答的方式可以是多樣,同一件生命事件,放在不同的脈絡中則展現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生命的意義是如何的,決定在我們將生命現象放在什麼樣的脈絡背景中去理解。
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乃至哲學,所有的知識都足以提供人們作為理解生命現象的背景。所以廣讀這些學科的知識,可以幫助人們走出狹隘的認知,而廣泛的理解生命現象,從而在其中揀擇、構成總體的生命藍圖。但必須要指出的是,無論我們採取那一個學科領域對人的研究成果來理解生命現象,所構成的總體生命藍圖,仍只是一種思想的存在或是意識的存在。這種思想的或是意識的生命藍圖,所能解決的不過是我們理論理性的要求,滿足我們知性上合理化的需求而已。不可諱言的,凡事要撾有一個合理化的解答,對人類的生存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我們總是不可避免的會去思索「為什麼的問題,而各種知識性的理論模式,都是勇於嘗試解答者,儘可能的為我們提供一種可能的、理解生命現象的途徑。然而人類的認識能力終究是有限的,生命對我們而言永遠是個待解的謎,我們似乎永遠無法知道生命「為什麼如此,對一個明白自己認識限度的人而言,再完備的理論體系,都無法完全安頓他對生命的提問。如果他還堅持要問「為什麼,那麼似乎要尋求其他的解答途徑了。在這種狀況下,訴諸傳統、信仰都是可以嘗試的途徑,也是一般較熟悉的途徑。
不過以下所要討論的並不是傳統的或是信仰的答解途徑,而是較為人們所忽略的另一種途徑,亦即人透過身體與周圍的一切保持不斷的互動關聯時,身體所體會和感受到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四、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綜觀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可以發現,西方傳統哲學雖然早就開始研究人,但主要的觀點卻是採取身心二元的理解結構,以致忽略了人的基本生活體驗,受這種理解結構的影響,造成身心的疏離,人們與自己的身體失去了緊密的聯繫:或有人視肉體是罪惡、痛苦之源,肉體是心靈的牢籠而不重視肉體;或認為我們要追求的是心靈的滿足而把肉體放在一邊;或是否認在身體內發生的感覺,以為這些是不好的、有害的,以致逃避而不敢面對自己身體的反應(瑞尼.威爾菲爾德,2001,序言)。廿世紀以來存在主義的發展,促使人們重新開始重視人的基本生活體驗,到了廿世紀中葉,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Merleaau-ponty)創立以身體為基礎的存在現象學,詮釋了身體在世界構成中的基礎作幅,更進一步提昇了身體在當代思想中的地位,引發了人們轉回對身體的關注,並意識到身體是人構成世界的原型這一事實(梅洛.龐蒂,2001)事實上早在一八九六年,柏格森林(H.Bergerson)出版的《物質與記憶》一書中,就已經非常注意身體的問題,指出了身體會選擇一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儲存它所發現的東西(柏格森,1999,頁8-9)。有關身體的研究到上世紀八年代以來,更整合為對身體的跟學科研究,在西方並已獲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研究、精神分析學、主姓主義等都把它作為主要的研究論題。
其實從遠古時候起,神話、巫術與瀰漫下的人類,就是以自己身體的原型去構想宇宙的形態、社會的形態、乃至精神的形態,但西方人卻走了那麼遠的路,到了十九世紀末、廿世紀才回頭重新開始注意到這種現象;相較於西方,或許可以說中國人老早就有意識的、自覺的注意到這個現象了,例如,漢朝的董仲舒就曾經提出了「察身以知天的說法,不僅意識到,更進一步反省與考察人是如何以自己的身體為原型去構想天地萬物的形態,指出想要知道在人們構想中的天地萬物形態究竟是如何的,就必須反身自省,由考察人的「身體入手。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所謂的「身體是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心合一的整體。所謂的「察身,並不是把人從具體的生存情境中抽離,孤立地去研究人類自身內在的事物,如思想、靈魂和肉體的作用如何?而是把人納入實際情境中加以掌握;中國人也觀察人,但是中國人對人的觀察,是將人置於現實生存情境中,所掌握到的是人相應生存情境而產生的一種動態關聯。這種人與情境相關互涉的動態關聯,也可以作為我們構畫生命的總體生命藍圖。有關這種心想,可以在中醫理論中找到系統的說明,對於有興趣從醫學背景中來構畫生命意義的讀者,或許可以進一步去研究中醫理論,並從中發現與理解中國傳統醫學中所提供的總體生命藍圖究竟是如何的狀況。此非本文所探究的範圍,不遑多論。
在此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關「察身的另一層意義──「察身不只是對身體作對象化的觀察,「察身也可以指人們在自己的生存情境中,對自己身體活動的整體知覺,或稱之為身體的知覺。這種身體的知覺不是把身體當作一個對象化的客體,不是從外部來觀察自己的身體,而是「以身觀身(《老子》),回返身體本身,從內部感受身體自己在運動時的震顫狀態。
(一)如何構成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
誠如德國哲學家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Schmitz)對哲學所下的定義,以為哲學可以界定為「人對自己在遭際中的處身狀態的沉思(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現代身體現象學的主要意圖,即在試圖揭示性的和理性的去接近身體無意識的生活體驗(赫爾曼‧施密茨,1997,頁IX),而傳統中國思想不僅只是教人揭示性的和理性的去接近身體無意識的生活體驗;更要進一步的教人在生活情境中調整無意識的身體活動,使其能展現理想的活動狀態,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同時也教人開發身體的各種感知能力,去感知原本是無意識的身體震顫。這種以人的身體去建構總體生命藍圖,或生命意義的方式,有其特殊性與簡易性,以下即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主,詳細分析中國傳統思想是如何教人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調整自己身體的活動,使身體向所遭遇到的賽事物開放,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以及如何教人用身體去感知身體的震顫;希望由此引述,指出這種構成生命意義方法的特殊性。
(二)論「心齋,「坐忘
大體而言,《莊子》書中有關「心齋、「坐忘的敘述,或可視為瞭解中國古人對於如何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開發身體知覺等相關問題,相當典型的範例。為了清晰的說明上述經由身體構成總體生命藍圖的見解,首先得分別解析式的揭示在《莊子》中有關「心齋、「坐忘描述。《莊子‧大宗師》說:
然日:「何謂坐忘?顏回日:「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日:「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在(大宗師)中,莊子借孔子與顏回的對話來闡述何謂「坐忘,根據其中的對話可知,所謂的「坐忘,就是要使自己「同於大道;而「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所描述的是人處於「坐忘狀態中,人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體與外物的認識關係如何。
首先要說明的是所謂人自己必須「同於大通的意思,基本上指的是《莊子》所認為的一種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所謂的「同除了具有「會合、「淵的意思之外,還有參與共謀以及和諧的意思,循著這些意義,「同於物或是「同於大通(大道),主要是說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應廳是指與天地萬物會合,與天地萬省以一種相互關聯、相互配合的方式,構成一種相反相成,共同謀劃的、共在的、和諧關係(林文琪,2000)。
其次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依莊子的看法,主要在說明人應該要如何調動自己包含感官、心知、百體在內的身體,去完成理想的身體活動狀態。有些人以為(大示師)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主要是指人應該要去情去我,而抑制形體、感官、心知的作用。若依照一般的看法,那麼所謂的「坐忘豈不就像是《莊子.天下篇》所記載的慎到之流的人物,追求「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莊子‧天下》),如草木樹石般無情、無知之物的生命狀態?!其實莊子並非如此之主張,反而以為這根本是「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莊子.天下》),由此可見《莊子》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並不是要使人的生命「至若無知之物的狀態。那麼竟究該如何理解(大宗師)所謂的「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呢?本文認為應該回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等「墮、「黜、「離、「去在人身體上所發生的活動狀態如何,來作重新的反省。(林文琪。,2000)
「墮字,有「易,轉變、簡易的意思:之有惰的意思。循此義衛伸,則「墮枝體,並非要放棄身體的意思,而是指轉變肢體本身的運作方式,使其由繁而簡,讓肢體的運動回復到最簡單、基本的運作狀態:而「墮作「惰的意思,則是指調整肢體相應外界的反應方式,使其由積極主動的活動方式,轉而採取一重被動因應,「待物而動的活動方式。(林文琪,2000)也就是要調整身體的活動使其展現「聽之以氣的狀態。《莊子.人間世》說:
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之。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莊子》指出,人與外界的人事物相遇時,若只是開放我們的耳目口鼻等身體的感官去接受他們,那麼就如「聽止於耳般,我們只對所遭遇的人事物開放身體的感官而己。《莊子》以為人與外界的人事物相遇,除了引發我們感官的活動之外,還會進一步的引發心知的成活動-「聽之以心:但是「心止於符,心知構成活動,容易將外物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物來觀察,因此如果囚對所遭遇到的人事物進行心知的構成,亥即囚對外界人事物進行知識性的理解,如此一來,心知所建構起的內在生命藍圖,不過與外界的人事物有一種相符合的關系而己,並沒有產生具體的、存在上的關聯。因此《莊子》進一步指出,理想的人與外界人事物的互動方式,是「聽之以氣。所謂「氣,主要是指身心合一的身體在參與情境互動中所展現出來的總體活動狀態:「聽之以氣,則是說我們在與外界的人事物交接互動時,必須整個身體參與到情境中,以整個身體向情境開放,展現「虛而待物,讓身體活動展現「應物而動的狀態,才能與情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協作關係。
「黜與「屈相通,具有收斂的意思。如《國語.周語下》:「為之六閒,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工引之的《經義述聞》說:「引之謹案:黜,讀之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氣之。……沉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所以聞陽律,成其功也。發揚與沉伏義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從身體活動的角度而言,「黜是一種反向的調整活動,亦即收斂呈現散越狀態的氣。在這個理解之下,所謂的「黜聰明,是指調整耳目的運作狀態,亦即收斂耳目指向外界,逐物而不反的狀態,轉成為一種「反聽內視的狀態。這就是《莊子.駢拇》所說的:「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己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己矣。「黜聰明就是指調整感官知覺的作用,使其成為「反聽內視的自聞、自見,回返身體活動本身來加以感受。(林文琪,2000)
「離具有兩行並立,以及明的意思,循此義而論,所謂的「離形,並非說「坐忘時要超越形體,心靈脫離形體而進人出神的狀態,而是說「坐忘時人不僅從未超越形體,反而在坐忘狀態的當下,人的身體本身對自已所展現的形體,有一種與形體活動兩行並立的自知之明,亦對活動中的身體形成一種身體的知覺,感受到形體活動時的震顫狀態。(林文琪,2000)
「去具有「人相違、行的意思。循此義而論,則所謂的「去知,人是人用心知、脫離心知的意思,而是「違其心知而行的意思,亦即調整「心知的作用方式,使「心知的作用方式與一般主動構成的用方式相反。例如,相應於我們與物交接時,心知指向外物去認知外物的指向活動而言,所謂的「違其心知而行(「去知),就是說要調整心知的指向作用,使其由向外物的意向轉而成為一種對「思的活動「反躬個省的意思:另就心知的構成活動而言,心知的構成活動,主要是先將外物與我對立,而後去對外物進行批判性的考察,使外物脫離直接經驗的或感知的所對,而成為一種可理解的、具有確定性的、思維的對象。相應心知的這種構成活動,「違其心知而行(「去知),旨在調整心知的構成成活動,使心知能以「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莊子.人間世》)的方式展開,亦即當感官心知「徇耳目內通,經感官、心知作用形成關於外物的知覺時,心知能發揮其「反躬自省的能力,自我調整,不以持有(having)的方式來固持心知構成之成果,不視之為唯一的真理,重反直接面對事物的交往活動。(林文琪,2000)
(三)小結
綜合前面關於「心齋,「坐忘討論中,有關身體活動狀態的說明可知,《莊子》以為理想的人與天地萬物互動的方式是,人整體身心的活動必須處於「同於天地萬物的狀態,亦即與天地萬物的活動相會合,與天地萬物形成一種相互關聯的、相互配合的、相反相成的、共在的、和諧的互動狀態。也就是說,人以實際身在情境中,以與情境融為一體的狀態,與情境互動,而在「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之後,與情境成為和諧共在的整體。
基本上,這種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是通過一種本體同一化的運作,向外物開放,以「虛而待物的方式,因應外物之動而動,與外物的存在活動,使人的存在活動與物的存在活動,在密切而具體的交住(communion)之中,相互諧調,和諧共動。這不只是一種理智的構畫,而是實際身體的活動,在身體實踐中完成的生命意義。
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就是在我們「虛而待物的身體活動中構成的。然而《莊子》認為我們不只要調整身體的活動方式來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而已,而且在相互諧調的互動中,人對自己理想的身體活動方式要有一種「反聽內視和「反躬自省。這種身體在活動過程中不斷地向內的「反聽內視和「反躬自省,就是身體構成自身身體形象的過程,或可稱之為形成身體知覺的過程。比如當自已在打字時,除了調整我們的身體,使自已身體動作都能展現與情境中的條件協調的狀態外,在過程中還要去感受打字時自己身體整體的震顫狀態,像:肌肉的收縮與放鬆,整個身體的運動方向,自己身體在整個環境中的位置等。身體知覺的開發,不僅使我們發現身體所構成的、理想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肯定、確認了自己所構成的理想的總體生命藍圖如何:而且可以讓我們感受到自己是身心合一的整體,引發一種與整個生存情境相互協調的、共同體的感受。這就是《莊子》所說的「物化。《莊子.齊物論》說: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人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所謂的「物化是人以其自已全身心的存在向物開放,讓自己的生命律動展現為因應外物之動而動的狀態,與外物形成一種交互同步、複調性的和諧互動。在互動中,人不僅致力於調整自己以與外物形成同步的互動,而且體驗著自己活動的成果,形成一種與外物合而為一的感受:但是這種一體的感受,這種與外物合而為一感受,不是自我縮減,放棄自我投入對象的密契經驗,而是如莊周夢蝶般,自己化作另一隻蝴蝶,栩栩然地與所交往的蝴蝶共舞,是一種與他物共在的感受,一種共同體的感受。所以「物化不是化身為對象,而只是調整自己,使自已與對象成為同一層次的存在,以與外物形成交互同步、複調性的和諧互動。雖然「物化時人是調整自已的活動使之與對象成為同一層次的存在,但是人在與物交互同步的互動中,是隨時保持著清楚的自覺,「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儘管在互動中會引發「人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密切不可分割的一體感,但是「周與蚑蝶,則必有分矣,人們不僅感受到整體,而且也能感受到自已是整體的部分,自已與共舞的對象是有分別的。(林文琪,2000)
此外,身體知規的開發,也使得人對自已與外在人事物互動時的身體活動婦身,產生一種全神貫注而且沒有外在目的性的知覺,以及引發「躇躊滿志的「自得之樂這就像《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故事所描述的,解牛本來不過是個技術性的操作而已,但由於庖丁不僅追求技術的純熟,而且對自已整個解牛的活動過程,有非常清楚的感受,且能欣賞自已所完成的動作,引「躇躊滿志的自得之樂,賦與了生命活動審美的性質。
結語
回到本文主要的論點必須再三申明,生命的意義人不是現成的某物,而是我們所賦與的看法。賦與生命意義的方式,主要在根據某一個總體的計畫或是生命藍圖來構畫自己的生命方向,並實踐這種生活,如此才能活出有意義的生命。
一個總體的生命藍圖,必須內化為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或是人觀,才能在生活實踐中發揮影響力。但是總體生命藍圖內化的過程,人是一勞永逸的追求,而是在與所遭遇到的人事物互動中構成的,隨著我們遭遇的不同、個人選擇的不同,所建構出的總體生命藍圖也會展現出不同的廣度與深度。
大體而言,我們可以持以構畫自己生命的總體生命藍圖有很多,比如各種理論模型,例如,醫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歷史學的、哲學的……等等;或影響著我們生活的傳統;或各種的等等。本文集中介紹較為人們忽略,但現在似乎又開始引起注意的一種方式,亦即透過身體來構成身體化、總體的生命藍圖。事實上,對身體而言,「生命藍圖的措詞並不恰當,因為身體化的生命藍圖並不是透過對象化的觀察所得到「視覺圖像,而是身體從內部感受到的身體活動狀態,亦即人們在具體的生存情境中,身體本身所感受到的、在身體中發生的、整體的震顫狀態。
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的建構方式與知識性的總體生命藍圖的建構方式人不同。知識性的總體生命藍圖是透過「為什麼的提問和解答的尋求在意識中這構起來的;但身體本身人問為什麼,身體構成意義的方式,是以相應情境作出不同的活動方式來展現的。也就是說身體會相應情境作出不同的反應,而這些不同的反應方式本身,就蘊含著身體對情境的理解。無論是意識所構成的知識性總體的生命藍圖,或是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化的生命藍圖,對追求完整的總體生命藍圖者而言,二者都是同樣重要的。本文所以特別著墨論述身體所構成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旨在起大家不要因為身體化的生命藍圖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建構,並在無識意識的狀態下影響著我們生命的展,而忽略它。
文中分析《莊子》所敘的「心齋、「坐忘,來進一步說明古人對於身體化的、總體的生命藍圖有何構想。「心齋、「坐忘的身體經驗,並不是一種脫離情境的、純粹心靈的活動,而是可以在日常的行、住、坐、臥當中發生的,關鍵在於我們要在日常行、住、坐、臥的當下,關注自己的活動過程,關注自己的身體如何相應外界的人事物來展現如此這般的活動方式;並開始有意識地調整自己身體的活動方式,以「虛而待物的方式向情境開放,展現應物而動的狀態,恢復身體與情境的直接交住;再則要有意識地開發自己的身體知覺,恢復我們與自已身體的關聯,從內部來感知自己身體的震顫狀態。如此,只要持之以恆,我們自然可以在自己日常的行、住、坐、臥中展現出和諧與平衡的身體震顫狀態,構成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並活出有審美意義的生命。
行文到此,熟悉傳統中國文化的者或許會發現:中國古代用來教育世之、國子的樂之教中,有許多演習禮議、樂舞的課程設計,這些課程至東周禮崩樂壞之際,孔子還依非常重視,並用來教育平民學生。這種重視身體操演的教育課程,意味著什麼呢?順著本文的脈絡,您或許會回答說:古人的禮樂教化課程,不正就是一套訓練學生如何在各種生存情境中做出理想的身體活動,建構理想的、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並開發學生身體知覺的課程(林文琪,20001)?沒錯!有與趣的讀者,不妨進一步去探究中國傳統禮樂教育的實質,或許可以從中解消您閱讀本文帶來的、有關如何建構身體化的總體生命藍圖的疑惑。
參考文獻
郭慶藩輯(1974),《莊子集釋》。台北:河洛。
〔德〕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Schmitz)著,龐學詮等譯(1997),《新現象學》,上海:上海譯文。
〔美〕瑞尼.威爾菲爾德德著,孫麗霞等譯(2001),《身體的智慧》。遼寧:遼寧教育。
〔法〕梅洛.龐蒂(M.Merleau-ponty)著,姜志輝譯(2001),《知覺現象學》。北京:商務。
〔法〕柏格森(H.Bergerson)著,肖聿譯(1999),《材料與記憶》。北京:華夏。
哲学人生论文篇7
文化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兴起,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显学,也成为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学界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和建构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如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所言:“有趣的是,如同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复杂多样一样,在对‘文化哲学’的界定上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在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下,其实主要呈现了对文化哲学的三重解读:作为元理论的文化哲学、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以及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三重解读的分析能对文化哲学的概念的厘清以及文化哲学理论建构有所裨益。
一、作为文化学科元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作为文化学科的元理论,实际上是从“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内在关系来把握文化哲学。有学者将“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关系理解成为“器”与“道”的关系。邹广文对其描述为“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超验的,前者所要解决的是‘现象界’(或称感性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要追求的是‘物自体’(或称宇宙本原的问题);前者涉及物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活技巧,后者涉及物的存在根据和人的生存意义”。“文化”被认为是人存在的外在形式,而“哲学”是人存在的内在向度,文化哲学则是内在与外在两种向度的统一,它最终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内在本质、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为文化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众多学者认同的一种解读,即使许多学者并不是从这一维度来诠释文化哲学的,但是他们也不否认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洪晓楠坚持从这一维度把握文化哲学,他认为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具有抽象整合文化人类学的功能,他说:“由于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理论都有着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哲学的抽象和概括,并试图为一切研究人和文化的人文科学提供研究的出发点,在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抽象完整的人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邹广文也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抽象性概括性方法,它应是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各门实证性文化学科的一般理论研究。”他强调文化哲学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直接联系,强调文化哲学对文化学科的抽象概括的功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简言之,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本体论基础,提供了对人类文化进行“总体性”把握的方法指导,而文化人类学则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形而下的研究资料,从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即文化哲学是从本体论层面来回答文化的深层问题,从这一点来区分文化哲学与具体的文化学科是这种解读的主要特征。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的。文化哲学自兴起以来,一直受到诟病的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视域与文化学的理论视域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有学者归纳分析了文化哲学的四种基本视野:“第一,强调文化哲学是文化学的元理论。……第二,认为文化哲学是对人类文化现象的总体性考察。……第三,不同文化圈和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第四,文化哲学是以文化为本体,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宽容的哲学形态。”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四种视野中的后三种视野其实都在文化学的视域之内,受到了质疑,但是即使是第一种也同样受到了质疑,邹广文质疑说:“既然界定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的元理论’,那么这种‘元理论’的视点应如何着眼?如果认为文化哲学讨论的是‘文化是什么、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等这样一系列问题,显然这属于‘文化学’视野中的问题。”邹广文的质疑是合理的,如果这样着眼“元理论”,的确没有跳出文化学的视域,那么文化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的那样,“这是元理论的工作,当人们正在倡导一种自己的独立概念之际,它试图抓住一种事业的前提”。文化学虽然回答文化的结构、发展规律等问题,但是它对自身学科的前提是缺乏反思的,文化学是以“文化”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对“文化”本质的思考与回答不可能在文化学内部得以完成,这一点是通过哲学实现的,这就是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在介入“文化研究”时首要的特殊功能。道格拉斯・凯尔纳这里不仅提供了解读文化哲学的一种路径,他还通过对“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论述提供了对文化哲学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方式。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文化研究与哲学:一种介入》一文开篇提到:“过去二十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的显学,哲学已经成为这一事业中一种非主流的并常常备受抑制的一维。”道格拉斯・凯尔纳实际上告诉我们三点信息:第一,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第二,哲学在文化研究的推广和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第三,哲学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抑制。这里道格拉斯・凯尔纳已经隐晦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需要哲学发挥更大的功用,哲学的功用不应该被抑制,而且应该积极介入到文化研究中去,接着他指出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三种特殊功用,论述了“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说:“我并不想夸大哲学的重要性,我的论点是今天的文化研究应该在发展一种适应现时代挑战之文化研究的努力中通过合并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和一种批判理论的多样性进行其跨学科计划。”他实际上论述了“哲学”与“文化研究”合流是一种理论发展趋势,也就是具有必然性。道格纳斯・凯尔纳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哲学”的概念,但是他在这里关于“哲学”与“文化研究”二者关系的论述从研究对象上将文化哲学与文化学区分开来,文化哲学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也得到了捍卫。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也是具有现实背景的。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发展,推动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人类学最初的研究视域非常狭窄,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的体质特征问题;后来,人类学逐步拓宽视角,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元素融入到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典型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就表达了早期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观点;进入20世纪,由马克斯・舍勒开创了哲学人类学,将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将人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后,文化人类学吸收和借鉴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将“哲学”、“文化”、“人”三者统一在理论研究之中,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哲学人类学”,这一新的理论形态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哲学的典型理论形态。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现当代文化哲学人类学就是文化哲学的典型形态之一,它实际上是对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部门哲学人类学的概括、总结和整合。”邹广文也将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学派归入文化哲学。这正说明当下一些学者对文化哲学的把握正是从哲学在文化学科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突显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不能离开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介入“文化”的特殊功用。
二、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
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对文化哲学的另一种解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从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对西方哲学史两种范式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援引了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的观点,文德尔班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传统,以哲学的对象来区分,第一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哲学家追求的是真理和知识体系,哲学“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这一传统就是思辨哲学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二种哲学传统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创的,哲学家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实践、价值和意义,哲学“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这就是所谓的实践哲学或者文化哲学的传统。而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将两种哲学传统的对立归结于研究范式的不同。
那么,何为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范式”一词本来是哲学家库恩提出的哲学概念,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重点阐释了“范式”的内涵,意指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在库恩“范式”的概念内涵的原有基础上,对文化哲学持这种解读的学者对“哲学范式”作了重新表述,他说:“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它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这就是说“哲学范式”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活动整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所具有的独特的哲学方法,那么对“哲学范式”的理解不能横向地比较,即不能从同一时期不同哲学流派的比较中去理解,而只能是纵向地历史比较,将后一时期的哲学活动与前一时期的哲学活动进行比较,两者在整体特征上的差异,就是哲学范式的内容,就是两者所各自具有的范式特征。
因此,将文化哲学和意识哲学作为哲学史上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范式,实际上并不是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哲学流派,也不是视为一种哲学思潮,而是一段时间内整个哲学活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文化哲学渗透在各种哲学理论中是当下哲学活动的主流特征。
那文化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范式呢?这需要在与意识哲学范式的比较中得以把握,意识哲学注重思辨,哲学活动在于追求牢不可破的知识体系和“绝对真理”,因而不关心现象世界,不关注入的生活世界,哲学理论局限在纯粹思辨的“理念世界”,那里是无“人”的世界。因此,文化哲学作为以意识哲学对立的哲学范式,它必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具有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境遇的特征,哲学活动不再是追求真理,而在于探讨人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应该坚持“日常生活批判”的方式。上述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江天骥在《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也认为“文化哲学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哲学肩负着将哲学从“无人”的思辨领域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使命。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它实际上完成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它意味着在当下和未来的哲学活动中文化哲学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而成为哲学活动的主流范式,任何哲学理论都不能忽略人的价值维度。这一场革命从康德就已经开始,康德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了“纯粹理性”统治一切的错误观点,为人的“实践”(在康德那里主要指道德实践)开辟了一块独立的领域,康德虽然有力地批判了思辨哲学,然而自身还是无法摆脱思辨哲学的幽灵,但是他的批判精神被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为思辨哲学的范式转换拉开了序幕,文化哲学这一过去长期被忽略和抑制的一维,被逐步认识和确立。程在论证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当代哲学在它内在逻各斯方面和外在的世界(社会历史)功能方面,都有一些导致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失语’状态的问题。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理路的提出,也就是力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并且“不少哲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新的追求:哲学研究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就是:从理性哲学向文化哲学过渡”。因此,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思路和方法”,是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哲学活动当下以及未来应该坚持和选择的方向。
三、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视作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将文化哲学的主要功用和理论使命归结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解读强调从文化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来把握文化哲学。“现代性”的概念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扩展而产生的,而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过程,现代性就是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意识,它坚持理性至上、个人主义、历史进步等观念,这些观念最初被人们热情拥护,是因为它促进了人们的自我觉醒,呼吁人们追求个人自由、解放,将人从原有的具有依附性、严格等级制的封建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现代意识破除了人们原有的神话、自然崇拜等意识观念,成为统治人们的主导意识,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除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张开辟道路。但是现代意识并不是人们应该永恒坚守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证明了它自身宣扬的那些观念所具有的欺骗性,人所获得的“自由”只是个人解放的假象,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反而是为生存物质条件所迫不断地出卖自身,让资本家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人类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而是又被纳入新的受压抑和束缚的社会环境中。
持这种解读观点的学者,往往是把“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理解为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生存方式,但它不拘泥个别的文化形式,而是侧重于这一时期内人们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领域,也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中,总之,它浸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哲学对“文化”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人生存方式的反思,由于现代性深入到人的存在方式――文化中,控制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处于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文化哲学,它企图对人类生活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反思深入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因此,文化哲学在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它批判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解读,许多学者并不认同文化哲学肇始于新康德主义的观点,他们根据文化哲学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本质,将文化哲学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因为“许多当代的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对现代性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真正的先驱者”。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也让众多学者将20世纪的批判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同时,基于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共同理论目标,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被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当中,洪晓楠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哲学运动。”
四、三重归一:文化哲学的合理内核
应该指出,上述三重解读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对文化哲学理论认同上的巨大分歧。比如,有学者对文化哲学持第一重解读,将它视作一种元理论,最后将文化哲学定位为一种和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等并列的一个哲学门类;也有学者将第二重解读庸俗化,抓住文化哲学范式注重人的价值、意义等特征,将所有与人及其文化形式相关的哲学派别和门类全部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文化哲学变成了集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多种理论的“学科群”;当然,还有学者将文化哲学视为批判理论,将众多的文化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等批判理论也归入文化哲学旗下。其结果毋庸置疑将是“鱼龙混杂”、“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局面。当然这是一种隐含危机的局面,“目前的问题在于,在文化哲学的旗帜下集合了无数差异颇大的理论学说,人们往往把文化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非反思’地冠以文化哲学的名义,而文化哲学的真正地平线则变得十分模糊、十分可疑,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地提及文化哲学,而细追问起来,却很难说清文化哲学的具体规定性”。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攻讦、文化哲学的丰富性看似不断扩展的同时,文化哲学自身的界限开始模糊,处于不断被消解的状态之中,在“无所不包”的外衣下是文化哲学合法性的危机,文化哲学想要统摄众多理论的雄心壮志与它理论建构中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的反差。
但是,在多重分歧的背后,存在着统一的可能性。其一是:统一的理论基础在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者不管持有哪种观点,最终都将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聚焦于“人”。其二是: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文化哲学的根本理论生长点。
李维武、何萍认为:“文化哲学所探索的主题,实际上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衣俊卿说:“人是哲学的根本,人是哲学的主题。”李成蹊论述说:“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人是文化哲学的本质和核心,离开了对人的研究,文化哲学的研究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邹广文也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在文化哲学研究的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上述解读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第一,将文化哲学视为文化科学的元理论,是将哲学的对象确立为人及其主体性。哲学的对象不是文化科学所面对的具体的文化形式,哲学思考的是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又是人的创造性成果,文化现象中已经蕴含了人的本质问题,文化本质的追问最终会变成人的本质的追问,文化科学的成果只是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料,而哲学思考的根本对象应该是人及其主体性,人是哲学的主题。
第二,将文化哲学视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立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在研究范式中确立了人的地位。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应该坚持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及其价值。文化哲学关注的世界与意识哲学关注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意识哲学的世界中是“无人”的理念,而文化哲学的世界中是现实的人。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把现实的人置于核心的地位,人才能真正成为哲学的主题。
第三,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是强调文化哲学的批判性本质,其最终将人的地位在哲学的理论旨归上得以确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是要将人们固守的现代意识予以破解,将人从现代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中解放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理论旨归是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解放。
哲学人生论文篇8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哲学人生论文篇9
一、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
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必然要体现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孕育和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种深刻的必然性与文化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样式”密切相关。所谓文化哲学的“两种样式”,一般认为是指“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和“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很实际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当其温良驯顺或无所作为之时,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通的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1]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这是文化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外在必然性。从军事文化整体来看。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军事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的转变,如果这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转变没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它便会整体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会发生逆转与倒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理论能够满足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呢?
传统军事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将“军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军事整体的哲学考察,实际上是以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考察作为核心。而军事文化哲学首先是将军事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活动,那么,在军事文化哲学的视野里,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也就成为对军事文化活动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三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的学科融汇与转型趋势。这是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所使用的哲学观点,就是文化哲学的观点。综观当前国内已有的文化哲学研究成果。有的自觉以“整体文化”作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2];有的选择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的批判视角[3];有的认为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结果的反思来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以实现人的文化自觉[4];有的立足从个体生存论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哲学[5];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6]。概括起来,文化哲学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融文化历史性于哲学的观点。
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军事文化”,就是指在整个军事历史进程中,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军事活动的发生、变迁和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武器装备、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所反映并展现出来的人类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所谓“军事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的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是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学。
先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哲学。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其实在军事文化哲学在以学科的可能形式出现以前就已经先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观点是指一种文化哲学的观点,而非“科学之科学”哲学的观点。传统军事哲学研究是持一种怎样的哲学观点呢?这种观点是:“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军事哲学的肩上。”[7]再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概论》已经先后问世,标志着军事文化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从文化学到军事文化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军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日益深入。对于军事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成问题性”,毕文波教授在为《军事文化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初步指出了这一点:“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在文化、军事文化系统构成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规律性理论,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畴又必然进入哲学和军事哲学,与其构成叠合的界面,而且该界面在所在层次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可相对独立,形成文化哲学和军事文化哲学”。
二、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不妨将其与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作一比较。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而军事文化哲学将军事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其研究领域应该是“军事文化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确定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考察“军事文化整体”。“军事文化整体”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两大方面,分别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从动态方面不仅仅是将“文化”理解为凝结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动态过程;从静态方面对于凝结成的“文化成果”分别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军事文化哲学能够弥补当前文化哲学研究中分支应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不宜发展成为具体的学科领域,它应该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是人类生存图式的深刻内在。我们认同这种观点,这些主张本身便是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有益尝试,但这种回归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哲学文化性的沉淀和应用。“军事文化哲学”可以说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军事文化哲学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够为现实的军事文化活动甚至军事实践整体提供深刻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内蕴于生存图式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同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并列的具体领域。
第三,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学哲学性的凸显和提炼。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军事文化学是用文化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军事活动领域文化现象及其特点规律的科学。军事文化学是军事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既是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显而易见,军事文化学用文化学方法研究军事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与交流、功能、价值判断等等;而军事文化哲学则是用哲学、文化哲学的方法来对军事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军事文化哲学研究能够对军事文化学研究起到指导作用,而军事文化学研究为军事文化哲学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
军事文化哲学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军事文化本质问题、军事文化运动问题、军事文化创造问题和军事文化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理论之外,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元理论也可以有选择性地作为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借鉴。比如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等,对我们研究军事文化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关于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发展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文化哲学关于哲学是从本质上来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场来看,军事文化哲学都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动态性展示这种哲学的生命力,开放性决定这种哲学的影响力,批判性体现这种哲学的创新力。这三种性质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要体现出这三种性质,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出人们在军事历史进程中所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们在这种生存方式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而研究这种军事文化的哲学理论也必然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包括军事文化本质论、军事文化运动论、军事文化创造论、军事文化价值论和军事文化方法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显示出军事文化哲学鲜明的学科特色,预示着该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天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J].求是学刊,2009(6).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0(3).
[2]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哲学人生论文篇10
文化哲学是文化时代精神的哲学表达,它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出发,为人类探寻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文化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论视野。
1.理性主义与价值主义的合流:文化哲学的诞生逻辑
文化哲学诞生在一个荒谬的时代,之所以说荒谬在于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由人自身创造的,人反对人,人压迫人,人创造的世界背离人,人进行文化创造不是成全人、服务人,而是压抑人、束缚人,人的异化与文化的异化相互表征,共同构成当代人生活世界的文化逻辑。就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看,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已发挥出各自的优势,但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推动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人本观念和价值理性维持着人的原始幸福感,却拒斥走向现代性的坦途。两种理论倾向的片面性已经在20世纪暴露无遗,人类能否走出这一文化异化的悖论,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良性结合,改变人及其文化世界片面性发展的厄运,成为文化与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理性主义与价值主义各自的片面性及互补性,使得二者的合流已经不可避免,文化哲学就诞生在这一哲学变革的运动之中。文化哲学通过对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的扬弃与整合,将理论基点建立在科学文化与人本文化的双重根基上,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探寻新的出路。
2.文化: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主要回答“文化是什么”以及‘‘文化为什么”的问题,这是人面对自己的本体、根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而与人生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生态哲学等其他哲学类型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文化哲学也与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文化科学等实证性文化研究不同,文化哲学是从整体性、批判性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的,文化哲学视野下的文化研究当然要研究文化的流行现象、本质属性、演进方式、发展规律,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哲学要通过研究文化,对人类的发展模式、存在状态、演进机制进行全方位地反思和批判,从而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文化哲学是对人的文化对象,也就是人的外在化存在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哲学属于对象意识,然而文化哲学对文化的研究不是纯客观的分析,而是把文化看做与自我高度相关的系统,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哲学又是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最高层面的文化研究和哲学理论,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的文化本性的理解和掌握,对人类的文化本体进行反思和批判,对人类的基本文化关系进行梳理和调适,实现解释和改造文化世界的目的。因此,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整体性、批判性的视角出发,对人之文化本体的理解、掌握、批判和建构。
3.人学:文化哲学的实质内涵
文化哲学主要以文化为研究对象,但研究文化也就是间接地研究人,因为所有关于文化的主题都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人类自我解放)的不同道路”,“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普遍的人类利益。”人是文化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关心人的存在与发展,追求人类的解放和进步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诉求。但文化哲学对人的研究,是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来展开的,这有别于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社会人类学,从一般文化学视角出发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从生理学视角出发的体质人类学等一般的人学研究,正如哲学家保罗海贝林所言“在一般哲学人学终止的地方,便开始了文化哲学。”[2]52文化哲学也不断在艺术哲学、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的批判中,归结于人本身,事实上,文化哲学只有建立在人的根基上,才足以真正展示文化的诉求和灵魂。‘‘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专门人学,它提出了人的文化可能性问题。”[2]因此,人学和文化哲学必然结合成同一哲学,文化哲学成为人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一句话,文化哲学归根结底不能不是一种人学,人学是文化哲学的实质与核心。
4.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问题: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人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文化哲学异于一般哲学的地方。对于文化哲学而言,仅仅阐述荒无人烟的物质世界的做法,不具有实质意义。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下,那种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的物质世界图景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人的世界”。所谓“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世界,即人所创造的世界“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所谓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创造物的关系,人与人化自然、人与文化传统、人与历史等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之总和。”[3]这样,文化哲学就将其研究领域,定位在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所及的范围。一方面,人与“人的世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同一性,因为“人的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对象化的存在形态或人的自我确证,人与文化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与自身的矛盾。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世界”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均等的,人是能够进行自我创造的能动的主体‘‘人的世界”则是人所创造的被动的客体,这就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人要对‘‘人的世界”也就是人本身负责。人与‘‘人的世界”的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统驭其他的关系和矛盾。关于文化的其他问题与矛盾,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入或展开,它们的发展与解决,也都以这对矛盾的发展与解决为前提。文化哲学的悄然兴起和广泛传播,对于拓展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促进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顺利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哲学意义:文化哲学的批判性价值就本体论层面而言,文化哲学具有本体论意义。文化哲学通过对人及其世界之间关系的把握,以及对人化和化人的文化生成过程的理解,系统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深刻完整地揭示出文化的人为性和为人性。文化与人是文化哲学的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强调文化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存在方式,是人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及结果;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人,是相对于物而言的,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其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文化哲学通过对自然和文化的严格划分,确立了一个大文化观,把文化和人内在地联系起来,这样既可以从人学的视野研究文化,也可以从文化的整体性视角研究人,从而对文化形成更加本质性的认识。文化哲学通过考察人与物的原则区别,形成了一个人学的视角,因而能够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把握人,从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把握人,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把握人,进而对人形成整体性的理解。
从价值论视角出发,文化哲学不乏价值论意义。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构成文化的基本内核,决定文化的根本性质。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不仅仅要对其技术和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更要看其价值理念合理与否。先进的文化固然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作为基础和保障,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有先进的理念与之相匹配。批判性是哲学的本性,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予以反思和批判,放弃人类不合理的文化价值观念,重新确立合理的适应时展和人的发展要求的文化理念。不难看出,文化哲学研究有助于合理性价值观念的确立,而合理性价值观念的确立,对于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以及文化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合理发展,有着积极的价值导向作用。
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化哲学的诞生为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具体文化学科提供方法论指导,从而推动文化研究由实证的经验层面向思辨的抽象的层面深化和拓展,促进整个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纯粹实证的经验层面研究往往缺乏批判思维和辩证眼光,容易陷入文化生态之镜,文化哲学以整体性视野审视文化的存在状态、发展规律、内在机制、动力系统、传播方式,从而更能够把握文化研究的终极诉求,真正解决文化研究中深层的重大问题。当然,文化哲学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乏指导和借鉴意义。
2.人学意义:文化哲学的主体性价值
文化哲学将文化看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了实质性提升“认识人自己”是人类自觉的起点,但一直以来,对人类本质的认识都流于现象或陷入片面,人的本质成为一个历久而弥新的斯芬克斯之谜。文化哲学把人定义为文化的存在,把人看成是自我创造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与神道主义划清界限,使人从上帝的宠儿变成人间的公民。文化哲学也抛弃了“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等片面性认识,而是把能涵括这一切方面的文化作为人的本质。文化具有历时性、累积性、创造性、多样性等特性,把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理解,将人的本质的动态性、独特性和丰富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化哲学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每一个文化个体都诞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教化,人在文化面前处于一种被决定地位,因此,人类对文化往往处于一种无意识、潜意识或不自觉的认识和理解状态,自从文化哲学产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开始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而充分认识到人于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样,人就不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受塑造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管理者、传播者、批判者、改造者。文化哲学引导人的行为越来越趋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学理路,大大地推动了人的文化主体自觉的进程。在文化哲学的指引下,人类逐渐摆脱文化决定论对人的误导,开始自觉地进行文化认识和文化创造。
文化哲学将人的发展的终点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活动,其初衷和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以分析文化创造活动为对象的特殊的文化理论和实践,更是如此,而且在文化哲学的视阈下,人成为文化的焦点,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成为自觉追求的最终目标。但由于人类所处发展阶段的阈限,现实世界的人们往往被私人利益、物质利益、眼前利益一叶障目。如何帮助人们摆脱和超越这些狭隘利益的束缚和限制,从而追求人类的长远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公共的利益,实现人类整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诉求。这对于人类文化个体的自觉生成和发展,以及人类理性地实现从“史前史”向“人类史”超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时代意义:文化哲学的历时性价值
作为人的深层存在方式的文化,引导人类从远古走向未来,从野蛮走向文明,可以说文化一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文化的真正发现、凸显、转向却是全球化以来的事情。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境遇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无论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和平主义还是恐怖主义……整个世界都将目光聚焦于文化,都试图用文化来大做文章,试图从文化中寻找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答案。于是,文化成为国际会议、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名人演讲的关键词,成为政府首脑政治作秀、邪教领袖迷惑人心、恐怖组织宣传动员的砝码,文化成为一张牌,大打“文化牌”变成一种时尚。这其中尽管有些许矫情,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所属时代的中心话题。
全球化时代是文化凸显的时代,是文化转型的时代,是人类文化生成的时代,因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时代。文化时代的到来,呼唤深化文化认识,从而再现文化时代的特征,形成系统地应对文化时代问题的机制。随着新的文化时代的生成和凸显,人类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改变趋势日益明显,当代世界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一种属于自己时代的哲学解释。对文化时代进行自觉地认识、反省、管理和规划,是时代向哲学发出的深切呼唤;关照文化时代现实,升华文化时代认识,实现哲学研究的时代转向,是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诉求。与此同时,哲学的创造性发展需要对文化时代精神和突出的文化问题,予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关注和思考,从而汇集不同文化化解文化冲突的思路和方法,探索人类的和平共处之道,促进人类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哲学人生论文篇11
一、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
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二、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三、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
“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四、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
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哲学人生论文篇12
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② 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③ 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三
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在他的讨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④ 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⑤ 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⑥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四
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五
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哲学人生论文篇13
“哲学”之名的引进,源于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用“哲学”来翻译西方的“philosophy”。西周先是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1]。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应该说,“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的特点。
将“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尚书正义皋陶谟》中“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而《尚书正义伊训》中“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在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据此,孔学亦可谓“哲人之学”。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如何处理这里的同异关系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已先有“中国哲学史”之名,如在北京大学哲学门讲学的陈黻宸著有“中国哲学史”讲义,谢无量亦著有公开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显然,这种讲法虽然用了哲学之“名”,但离哲学之“实”还相差甚远。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其“特长”如蔡元培写的“序”所说,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开始。但所谓“系统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4]。
冯先生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他在“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52-253。金岳霖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5]617_618。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比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的观点。因为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既然是“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如果能讲出中国哲学之“异”,那它就不仅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史”。
金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还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616。据此,上述金先生所谓“普遍哲学”,实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
张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
张先生针对“有许多人反对给中国哲学加上系统的形式”,指出“其实,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这段话在前些时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常被当作批评的对象,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在此后还有“至多不过如太史公作《史记‘分散数家之事'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7]4-5更重要的是在此书的“自序”中还有“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8]19在“序论”的第三节,张先生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这就是讲中西哲学之“异”,强调它是“中国系的哲学”,而非“西洋系、印度系”的哲学。
有了哲学的“类名”与“特例”之分,“中国哲学”之名方可安立。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9],所论甚精。显然,金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经不认为“中国哲学”的名称有“困难”了(最近,陈卫平教授撰文,认为金先生在40年代承认有“中国哲学”当是受了张岱年先生《大纲》“序论”的影响)。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首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10]。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首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的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11]。这也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上讲它仍堪当“哲学”之名。
二、中国哲学是“天人之学”
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这当然是“参用”了西方哲学的“三分法”_-249,但这种“三分法”是否就完全违背或曲解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呢?我认为,未必然也。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所注重的方法之一就是“察其条理系统”,亦即“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_-19。张先生也认为,中国哲学所讲的主要内容“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总此三部分,正相当于西洋所谓哲学”[7]3。这里所说的“相当”,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点”,或中西哲学共有的普遍性。如果中西哲学没有普遍性,那也就没有“哲学”这个类名,西周所谓“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也就不能成立了。
凡讲“系统”都要讲明系统中的“条理”或“部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可以说主要就是讲明“天道”与“人道”,中国哲学的主题就是“究天人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天人合一”。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天’与‘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以讨论‘天’、‘人’关系为己任。”
孔子所谓“智”在“知人”,相当于说“知人则哲”“哲”的字义就是“智”或“大智”,《史记夏本纪》将大禹所说的“知人则哲”记为“知人则智’)。但孔子所谓“知人”,其义不仅在于“能官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是孔子对于“知(智)的指点语,而非定义语。实际上,孔子所谓“仁者爱人”,是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其所谓“智”在“知人”,也是对于“人道)”的普遍之知。
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但儒家哲学又不仅限于“知人”和“爱人”。《论语为政》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可谓是“知人”的境界,而“知天命”就不是“知人”所限了。《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从“知”的范围来说,不仅是“知人”,而且是“知天”;从“知”的宗旨来说,“知天”也是为了“知人”。
《孟子尽心上》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忧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里所谓“无不知”,当然是既“知天”也“知人”,但当务之急是“知人”,尤其是知人之“性善”所谓“无不忧”,是要遍爱所有的人,但当务之急是“亲贤”,亦即“能官人”。从孟子对“尧舜之知”和“尧舜之仁”的表述中,我们仍能看到“知人则哲,能官人”的影响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14)。《孟子尽心上》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由“爱人”而进至泛爱万物了。
郭店楚简的《语丛一》云“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察天道以化民气。“《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易传系辞上》亦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周易》的这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学架构,是儒家与道家在思想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儒家的“天人之学”除受道家的影响外,也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如《孟子告子上》引《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接着引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虽然儒、道两家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他们对“天道”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他们的共同哲学架构。《老子》二十一章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庄子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也体现了道家的“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的思想特点。
《荀子天论》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儒效》讲“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这是道家之“天道”与儒家之“人道”相综合或嫁接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淮南子人间训》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这也有“儒道互补”的思想特点。尽管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互补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仍是共同的哲学架构。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先秦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就是说,先秦六家的言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务为治”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了各种学说,亦即在“究天人之际”的普遍模式中都是把“知人”、“为治”作为中心和宗旨。
汉代的儒学大讲“天人感应”,而主张对神怪“曼云”的扬雄《法言君子》也说“通天、地、人曰儒。”魏晋玄学家申论儒家的“名教”本于道家的“自然”,《世说新语文学篇》中何晏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后赞叹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这里的“学”虽然还不是“学科”的意思,但宋明理学家对“哲学”的精神确实有一种自觉的追求。清代的戴震《原善》卷上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戴震的宗旨是要追究“善”为何义,但“原善”必须讲明“天人之道”,这是儒家经书中的“大训”大义)。职此之故,我认为,儒学、经学中作为其“大训”的讲“天人之道”的那部分内容,就是儒家的哲学。统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哲学可称为“天人之学”。
从“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发展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实也就是天论宇宙论)和人论人生论)以及如何“知天”、“知人”的知论:致知论或方法论)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知人”是中心,“原善”善即“爱人为治”治即“安民”)是宗旨。这个“三分”架构的系统,既与西方哲学有着“相似点”,实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固有的脉络和特色。
中国哲学的“天人之道”,常可略称为“性与天道”,可见人性论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哲学所讲的“性”,是相对于“习”而言,“人性”就是人的生而既有、与生俱来的本性。《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正蒙诚明》“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性即理也”,可见“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性与天道合一”此在道家就是“德”与“道”合一,在佛教就是“佛性”与“真如”合一)。人性论既是中国哲学的人论的首要内容,又是天论与人论交揆合一)的一个枢纽。从性善论的传统说,“性与天道合一”也就是真与善的合一。
“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明人事”就是要确立一个行为的规范、价值的准则。有了这样的规范和准则,才能够“修己以安民”,“务为治者也”。因此,价值观或价值论:axiology)应该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宗旨。中国哲学表达哲学意义之“价值”的词汇是“贵”,所谓“和为贵”就是以和谐为最有价值,所谓“民为贵”就是以人民为最有价值,或者说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就是说老子、孔子和墨子的价值取向有不同。
人性论的理论形态是讲人的本性“是”怎样的,而价值观的理论形态是讲人“应该”怎样。人性源于天,且奠定了人将怎样生活或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基础。在“人性是怎样的”这个看似事实判断的命题中实蕴含了“人应该怎样”的价值预设。因此,除了“性与天道合一”之外,人性论与价值观的统一亦应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之后紧接着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所谓“立人极焉”,就是要确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开始,最终推衍出来的一个理论归宿或宗旨“横渠四句”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亦是如此)。周敦颐所讲的“五性”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此性是与他所要确立的“人极”相统一的。
 购物车(0)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