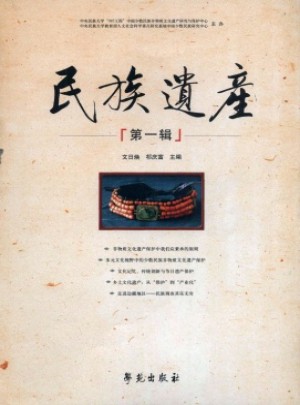民族与历史论文篇1
1.2历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教育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历史课的优势要由历史教师充分发挥出来,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及民族精神方面的教育,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培养出学生的优秀品质,来抵制外面世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学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自觉维护民族利益。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让学生学会认识历史全局和局部的发展关系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对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的内在联系要辩证的认识,从不同视角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弘扬民族精神要把学生培养出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提高人文素养,使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得以形成。
2在历史教学中培养民族精神的方法
2.1民族精神教育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的主要内容
一是要加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加强民族团结、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人类最古老、最高尚的思想品德、美好感情和政治职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应在历史教学中予以突出,使学生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二是要加强爱好和平、团结统一的精神教育。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了祖国的团结统一各族人民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正是各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中华民族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民族具有爱好和平、团结统一的精神,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并且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三是要加强实事求是、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教育。从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面对错误、问题敢于改正,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是要加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双手创造的,这使得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著称于世。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自强不息的精神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的精神动力。
2.2民族精神教育在历史教学中的实践
一是通过情境教学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根据具体的教学目的和内容,积极创设特定的教学情境,优化认知过程,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历史知识进行掌握,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得到培养。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授学生历史知识,还要对人文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渗透教育,培养学生从历史事件中分析并重新认识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正式讲授教学内容之前,进行与教材有关的问题情境创设,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思考,使学生的求知欲和认知兴趣得到激发。二是历史教材的内容丰富,通过一个个人物、事件表现出蕴藏在其中的丰富的爱国主义和思想教育素材,具体的历史事实是民族精神教育的根本,如果没有历史事实是不能说服人的,要做到寓教于史,让以理服人真正体现出实效来。在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中出现的任何困难都要勇于面对,出现的任何挑战都要勇于迎接,学生的忧患意思和使命感要以现阶段国情予以增强。三是要依据不同的内容来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可以运用名人名言。在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有许多深刻的民族精神教育内容。合理利用或补充历史教科书中许多杰出人物的至理名言来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操。四是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要结合时事热点,以古鉴今,培养出学生的民族精神,加深学生理解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帮助学生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和疑难,对学生正确人生价值观的选择起到引导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英雄人物的壮举来激起学生的爱国情感。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2
当人类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时,可以说就有了服饰。只不过,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是有着更郑重的涵义,那就是护佑生命,祈福避邪。尤其在科学尚不发到的原始社会,人们更希望能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保护着一个部落甚至一个部落的繁衍兴旺。因此,在现在这个以自然回归、绿色、环保为主题的时代,我们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主题,创造服装界新的历史篇章。
一、服饰与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关注原住民族的文化
泰雅族,这个在我国台湾宝岛人口九族中为第二多,分布地区最广的民族,拥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服饰历史。一直以来,泰雅族各社之间互相分立,没有施行统一的政治体制,因此各种争议最后都以武力解决。这不只是对异族,对邻近的同族也是如此。所以男子稍大之后,就执枪用刀。猎首时经常随行,以锻炼武艺及胆色。未取得敌人首级着不被认同为真正的泰雅族人,禁止施以种族象征的纹面。取得敌人首级着,还有衣服,手环,臂环等装饰品来表彰勇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服饰代表着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泰雅族的历史文化
(一)泰雅族的纹面文化
泰雅族生活中最具有特色的服饰应该就是纹面了。纹面文化其来已久,只能由神话传说来推测纹面的起源。其一,兄妹通婚:很久以前,一兄妹从裂缝的大石头中爬出来,长大后也要传宗接代,但妹妹担心哥哥不肯与她成婚,于是用煤炭将脸涂黑,哥哥见后不知道是妹妹,终于结成夫妻。此后,泰雅族的女性婚前必定在脸上刺青。当然,泰雅族的婚姻与其它文明国家一样,男女关系已非原始自由的状态,而是处于完整的婚姻状态。其二,避灾祸:以前泰雅族的年轻女子无故接连死亡,某日一女子梦见祖先告示她:纹面则可避祸。但无人知道什么是纹面,就将衣服上的图纹刺在脸上,果然不再有人死于不明原因,而且泰雅族人变得很长寿。现在泰雅族认为纹面乃祖先的训示,可以避免灾祸,延长寿命。纹面次数越多,颜色越深,花纹越美,死后能越早见到祖先。相传在死后会经过彩虹桥,通过此桥就能到另一个世界,若没有纹面或是生前功绩太少,就只能走桥下,要花较多的时间才能到,若有纹面者,就走桥上,不仅能较快到另一个世界,而且祖先会在桥的另一头等,陪伴你到另一个世界。纹面也是一种纪录泰雅族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方式。族中的男子必须学会打猎及猎到人头,才能纹面。而女孩子纹面后,方能学习织布。由此可知纹面代表了泰雅族人的心智成熟及经济自主。泰雅族认为纹面颜色越深,色彩越黑,越显美丽,可见纹面对泰雅族的审美观影响甚大。纹面所需的费用一般无法负担,因此纹面也为财富的象征。
(二)泰雅族的衣饰文化
泰雅族的纹面是特殊而美丽的,它承载着泰雅族的历史,也为泰雅族的衣饰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因为地域的不同,泰雅族的服饰也与别的族饰有所不同。
1、泰雅族的衣服分为长衣,短衣,裙子,披风,胸兜,绑腿,遮阴布等七种。其中兜档的款式男女完全不同,护脚布只有女子使用。此外头部则男子戴帽,妇女用头巾。男女脚上都不穿鞋。泰雅族的衣服,无论在结构上或衣服的种类上,男女的限制都很少,有很多衣服都是男女共享。除了妇女不穿无袖短上衣,遮阴布外,其它似乎都可以和男子共享。裙子本来以女性为主,但男性却又可以穿珠裙。童装形式和成人相同,但尺寸较小,花纹较简单。衣服分夏天和冬天的,但结构上相同,厚薄也一样,只有不同件数的分别,夏季穿较少件,冬季穿较多件。泰雅族的衣着也是随着场合而变化的,工作时,为保护皮肤与保暖,便于工作,男子上身穿无袖的工作服,下围遮阴布。女子下穿粗布白裙。庆典,交际及约会时,为了美观、正式,男女都穿礼服,只是女子穿的裙子以绒线织成的条状花纹为主,男女皆需穿肚兜。出征时,为了行动方便,鼓励士气,男子都穿战服及披肩,头戴熊皮帽。泰雅族人用他们久远的历史造就了他们灿烂的文化,以及他们美丽的衣饰、丰富多彩的生活。 转贴于
2、除衣服之外,泰雅族还有各种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有头环、耳饰、颈饰、胸饰、臂饰、手环、指环、脚饰等等。泰雅族的饰品有男女共享的,男性或女性专用的,特殊资格才能使用的和任何人都可以佩戴的。男人们佩戴的有男压发箍,菌形耳饰,贝钱颈饰,野猪牙臂饰,臂铃贝珠串腰和腿饰。女人戴金属手镯,贝片颈饰,扇形耳饰,梯形耳饰和女压发箍。男女可同用的有:贝珠串发绳,贝珠串腕饰和裸饰。泰雅族的饰品也有深远的历史及文化意义。泰雅族是以狩猎及猎首来衡量男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因此许多男人的饰品是以猎物的器官来制成,如兽牙,毛皮,拥有此类的饰品除了代表功绩,也显示对社会的贡献。据说,泰雅族的一种耳饰,也和传说中耕作的起源有关。古时粮食之携带极为方便。将数粒小米装入穿耳作为装饰的细竹管中携带即可。某处某头目于耳上穿洞,戴上竹管,且常将小米数粒放入空管内携带。大家起而效行,在耳朵上戴竹管,并将小米放入其中。后来,将小米粒放入竹管之风虽已绝,但却变为耳饰传至今日。即现在的耳管。
泰雅族没有具体的钱币制度的,他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以贝壳制成的衣服饰品,被视为是最贵重的东西,聘金就时常以若干件珠衣,珠裙来计算,如想成为巫医,拜师前也须付给师父一件珠衣。
三、泰雅族的织缝文化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3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中,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各种教材的局限,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民族问题总是意犹未尽,加之教材编纂过程中太过强调汉民族的中央政权,故涉及民族史部分的内容总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因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适当增加补充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要想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将一部多民族史面面俱到,恐怕难以完成任务。同时,汉民族及其所建立的中央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核心凝聚作用,在多元一体格局中起到网络骨架作用,所形成的文明史不但具有象征性,也是记述历史发展的标杆,离开了这些,就连最基本的历史时序问题都难以厘清。因此,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既尊重了历史实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导下得出的正确结论。如果不坚持历史主义,不坚持中国历史实事来讲民族问题,反而“会让学生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与判断”。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没有其讨论价值。中国古代史教学价值目标是:通过中国古代史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时序,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历史学科基本思维方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培养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正因此,中国古代史在书写时,“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都有相应分量涉及,但要达到深入探讨下去,仅靠中国古代史的教学难以胜任,必然会产生“意犹未尽”之感。同时,随着历史教学课程体系的改革,历史学本科教学中,已经将中国古代史的教学课时进行了缩减。一些重点院校将中国古代史教学“开设于大学一年级,分上下两学期讲授自史前时期至隋唐、五代至清前期的历史,共计144学时”,已经成为一种合理趋势。因此,在原有中国古代史整体编纂结构中,已经将少数民族史纳入到整体史内容中的现状下,再加大“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分量,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结构及教学实际等方面来看,都是难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民族史在中国古代史编写和教学中占有相应的分量,并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何进一步充分体现呢?本文认为,民族史除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按照教材编写规划进行充分讲授外,还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设立专门的民族史课程,供本科生选修或者必修。唯此,中国古代史内容和教学所谓的“民族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可以深入对“各民族友好交往”、“各少数民族文化介绍”、“少数民族政权”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可谓一举两得。
2民族史研究、教学的核心内容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
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3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4
伴随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高校历史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一些旧观念长期仍存在,往往给少数民族政权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忽视或抹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的特点。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偏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要特别注意。有学者提出,历史是多文本,多声音、多范式的。深化历史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秉承正确的民族史观。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话题,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教学改革中一个可以进行多维度认识和讨论的范例。本文试以此为实例,对高校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与民族史观的教学问题进行探讨。
一、由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的讨论讲起
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为大多数国人敬仰。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近数十年来在史学界争论不断,范文澜、翦伯赞、邓广铭等学者的观点也不甚相同。但在史学界内外被广泛讨论,始于2002年的,被多家媒体披露的新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本)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睨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说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和破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教育部随即声明:“媒体所传与事实不符,在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
从官方来说, 这一声明已澄清是非。然而此事件引发的史学界内外的讨论没有停止。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我们从岳飞身上能够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女真族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尽管在当时宋朝与金邦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金邦并不是外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代表了部分学人的观点。
二、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讲授
有别于中学历史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历史基本史实和方法,高校历史教学重在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使学生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因此,高校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突破教材束缚,不再把教材看成教学的法定依据,作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树立开放的教学意识,注意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鼓励质疑,激活学生的创新精神。开展“专题式”和“探究式”教学,教学中适时、主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背后,存在着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是民族英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一)“什么是民族英雄?”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民族英雄,是指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为了拯救全民族的生存和文明,与外族或外国进行不屈斗争的英雄人物。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在向学生讲授民族英雄的基本定义后,还可以介绍学界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或辩论式,适时启发学生:
第一,引导学生弄明白岳飞所处的时代和宋金战争的性质。向学生介绍主流的观点并进行讨论,如邓广铭先生认为“宋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军民们抗击女真铁骑的斗争,从政治意义上讲,乃是属于用反抗的手段以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的,亦即自卫性的战争,从而也就是正义性的战争!从经济意义上讲,则更是为了保障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要尽量使其免受破坏以致更向后逆转,自然也是属于进步性和正义性的战争”。
第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岳飞代表的民族英雄。作为教师,可以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既向学生介绍邓先生的观点:岳飞“始终笃实英勇地置身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尽最大的努力以抵御女真兵马的南进,及其在进军过程中的掠夺和屠杀,以求使东南半壁的各族人民尽可能免遭蹂躏和涂炭。这说明,岳飞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种种,固然符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确实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把他称作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也不回避部分学者认为的岳飞是“部分民族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抗金是为了捍卫汉民族和南方各族人民的利益,可以看成是汉民族和南方各民族的民族英雄”的观点。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可在教学环节设置交流互动。不仅能帮助学生深化历史知识,提高交流技能,也能开阔学生的眼界。
如果学生讨论的积极性较高,课堂气氛较活跃,效果较理想,还可以引导学生将这一讨论延伸至“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定义认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范畴认识”和“中华民族的忠与奸是非标准认识”等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观,从而提高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有效性。
(二)“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讨论,引出的新问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史学界的观点也不同:张子侠认为品评人物重在辨别是非得失,评断善恶功过,而要衡量是非功过,就必须确立正确的评判标准。这一标准有四点“立德、立功、立言和合其志功而观”。王沛林认为对岳飞的历史评价认识,有三个基准点:一是放在什么范围内;二是放在什么位置上;三是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坐标。因此,评价岳飞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应将其放到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分析,不能因为其历史局限性而否定其地位。
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把握展现历史人物的原貌,提供历史评价的多样尺度,组织轻松、活跃、自由的课堂讨论,避免简单、片面、毋庸置疑的历史评价结论等原则,丰富教与学双向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通过对岳飞的评价,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岳飞“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活动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岳飞的评价,肯定的声音如前所述,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已有精辟论述。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岳飞的抗金战争,只是维护了南宋统治阶级利益,并未代表人民的利益;岳飞是统治阶级内部“和”“战”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为中华民族英勇献身;岳飞的全部作为都是为了维护一个腐朽的即将灭亡的旧制度,他没有也不可能将历史推向前进。
另外,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渗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递正能量,教育学生用气节观品评历史人物虽不是唯一标准,但却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历史传承给我们的,大多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这也是史学界对于岳飞评价讨论的一个重点,即岳飞表现出的气节观究竟是“精忠” 还是“愚忠”,是不是爱国主义。在教学中不仅要传递对岳飞评价中的不同声音,而且要组织教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创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锻炼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历史教学中民族史观问题的讲授
通过讲授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争论,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等问题,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的本质是我们作为历史学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史观。
所谓民族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在史学活动、史学思潮及史家思想中存在的民族观念;具体地说,指史学中关于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属于历史观中民族观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刘浦江先生认为通过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在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在此环节可进一步升华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史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我们在评价岳飞时,要认识到中国是由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从岳飞所处的时代出发,具体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宋金民族关系的本质:宋金是并立的国家,岳飞的抗金斗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和掠夺的战争,是正义性的;要认识到宋金民族关系的主流:统一和融合;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在文化认同这种强力精神黏和剂的作用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民族的归属感和个人的献身精神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联合系统”;尊重历史事实,还要认识到岳飞的历史局限性,且不能因其局限性而随意贬低。
最后,让学生通过反思对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刻理解“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命题背后隐藏的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最本质的是坚持何种民族史观和历史观的问题。同时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岳飞评价问题的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史学界是否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采取正确的民族史观和方法论,才能最大程度上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在这场讨论中,双方都坚称是在遵循马克思唯物论的基础上得到的看法。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则是留给高校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龚延明.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J].学术月刊,2002,(4).
[3]李珍.民族融合与民族史观[J].史学月刊,2004,(9).
[4]张子侠.品评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月刊,2004,(9).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5
少数民族和汉族一道缔造了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史学是国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同时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过:“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2](P144) 可见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与国史相等。就历史地理学科鲜明的地理学特征而言,地方志的价值则更加突出。哀牢国历史是珍贵的地方民族史,对于了解秦汉,乃至夏商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源流及分布、交融和分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哀牢国族源研究历史回顾
及族属观点介绍 有关哀牢国的历史被记录的内容不是很多,由于时间久远,资料匮乏,围绕哀牢国文化出现的族属、疆域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争议。哀牢国族属的研究离不开学者前辈们的努力,任何有实质的进展都需要在他们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吸收继承和反思。
(一)“哀牢国”族属研究历史回顾
自明洪武年间,少数史家学者、命官使臣便已开始探讨哀牢族属,成书其时的董难《百濮考》,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等都是重要著作。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大批官修史书和史家著述,更多地涉及了哀牢族属,如朱希祖《云南濮族考》、章太炎《西南夷属小记》、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等影响深远。18、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有为数不少的英、法、美等国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译述和研讨哀牢史事、九隆神话,对哀牢族属也做出不同分析。正如王明珂所说,“20 世纪上半叶,早期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在西南地区汇聚最多,显示本地民族事务的重要和复杂”。20 世纪70年代下半叶和80年代下半叶出现了两次讨论热潮,参与的有知名学者方国瑜、江应梁、尤中、黄惠琨、张增祺、祈庆富、申旭、刘小兵。90年代有桑耀华、何平、何明、黎道纲、郭保刚、娄自昌、潘岳。还有以耿德铭为首的保山哀牢文化学派,他们对一手资料整理收集。这些学者对哀牢文化的研究推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3]
(二)“哀牢国”族属主要观点从一源说向多源说转变
从明至清代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濮人说为主,19 世纪至20 世纪前期,林惠祥、吕思勉和西方学者们的掸泰说影响也很大,近些年则以“哀牢夷是昆明族之一部”说较为流行。在20世纪30年代大泰主义流行和叫嚣的年代,国内资深的民族学家针对“大泰主义”种种漏洞提出了族源氐羌说。
1哀牢国族属一源说,主要有濮人说、越人说、氐羌说
(1)濮人说。明人董难在《百濮考》说“哀牢即今永昌濮人”。朱希祖《云南濮族考》认为澜沧江因仆族居住,原名仆水,至东汉时名兰仓水,仆加水旁而为濮,兰仓加水旁而为澜沧,濮族繁衍于濮水两岸。此观点为当代民族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所推崇。 方国瑜说:“哀牢为濮族,后称为蒲蛮,即今布朗、布龙、布饶(佤族)诸族古代的部落组织,哀牢部族应为古之濮人。”桂馥《札朴滇游随笔》引董难说,认为“濮与蒲音相近,讹为蒲耳”,即今蒲曼族,与崩龙族、佤族为同族属,即古之濮人之后裔。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诸书所载,“永昌郡风土,有称哀牢,有称濮人,其事迹大都相同,可知永昌濮人即哀牢人也”。王大道亦说:“‘哀牢’人即是‘濮人’。当是佤崩语支各族(布朗、崩龙、佤)共同的古代族称。”
(2)越人说,有三种认识。其一认为哀牢的主体族属有连续性。申旭先生以为,“哀牢属于百越,为滇越之后裔,是金齿、百夷、壮、傣民族的先民。在‘哀牢’的称谓出现以前,史称‘滇越’”。郭保刚说哀牢来源于百越系,经历了从滇越—哀牢—僚—傣的转变。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说哀牢是古越人,刘小兵先生也持此说法。二是直接认为哀牢是“傣掸族”。美国的“杜徳认为哀牢是傣族。陈序经也认为哀牢是‘掸傣族’。他说‘在东南亚的掸傣族所统治的古代几个国家,从地域方面来看,哀牢主要是位在我国的境内,这就是现在的云南的境内’”。三是认为哀牢是“瓯僚”。杨复兴说“哀牢民族——瓯僚”;严英俊也说“僚族在岭南、滇西永昌郡、夜郎、五溪、湘西的势力尤为绵远”。深思亦说:“‘哀牢’即后来的僚。” 石钟键说:“‘僚’是古代越人之后之称,由此看来, 哀牢语完全可以说是古代西部可能拥有先后承继的渊源关系。”
(3)氐羌说,氐羌说四种分别是“氐羌”、“昆明”、“怒子”和“彝族先民”四种。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主张“哀牢、昆明皆羌族”。黄惠焜在《哀牢夷的族属及其与南诏的渊源》等文中说:“‘昆明’人是内含极广的氐羌族群,哀牢是其中的一支,或者说是一支以哀牢山自称的‘昆明’人,是‘昆明’中较为先进的部分。”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亦称“哀牢人是‘昆明诸种’之一”。尤中在《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等著作中说:昆明族出自氐羌,哀牢部落是滇西昆明部落群中的一个部落;昆明族是近代彝族先民的主体,哀牢人是彝族先民中的一部分。闻宥在《哀牢与南诏》一文,列举九隆之“隆”,“怒语称背正若此”,以及怒族文身、衣饰尾、长于编织等特点后,认为哀牢是怒族的祖先。桑耀华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哀牢是现拉祜族的先民。学者潘岳根据哀牢夷熟悉煮盐之业,哀牢地区是产盐之地,哀牢夷语和缅彝语中的“坐”字是同源词,推论得出哀牢夷的族源是古羌人。
2多源说,多源说中主要是二元说
目前有两种观点即昆明—濮人主体说,濮—越人主体说。昆明—濮人主体说,主要代表人物是考古学家张增祺教授,他把哀牢夷与氐羌系的昆明人和古濮人对比,认为哀牢是由昆明和氐羌融合而成。濮—越主体说代表是耿德明先生,他在《哀牢族属百年争议的再认识》通过回顾哀牢族源研究,梳理各族说观点,反思研究方法,比对文化信息,最后认为哀牢族属是濮越为主体。目前还没有学者提出族属三源及以上的论点,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情况古哀牢时期应该是存在的。
二、哀牢族属研究的困难及存在的问题
哀牢族属研究其实就是对古哀牢国先民进行民族识别,就是通过民族自身保留的一些文化特征,结合历史给民族进行归类。对历史时空久远的古代民族进行归类识别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
(一)客观存在的困难
(1)历史久远。哀牢一词,是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 其首领贤栗诣越嶲太守郑鸿“求内属”时才载入中国史册的。《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考—哀牢在战国时已立国,与庄王国为与国—哀牢之先,在战国而已显,至光武而内属, 至明帝而置郡, 世系绵绵数百年哀牢兴盛时内属大汉,应该至少有几百年,由于时间久远,再加上少数民族政权还没有相应的史官记录,口述史传播过程增减和遗忘,实属正常。”
(2)史料缺乏。有关哀牢王国的历史记载首出自汉之杨终《哀牢传》,但《哀牢传》在《隋书》、《旧唐书》不见提及,当是此前已亡佚。古籍记载少之又少,唯见《风俗通》、《后汉书》、《华阳国志》散载有哀牢部分事迹。唐宋后的文献、野史错乱和矛盾更多,加之有些研究者对史籍中的某些文字理解不同,由此引发不少分歧。
(二)哀牢族属研究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主客位互动。记录哀牢的史料基本都是汉文稿本,记录者大多是汉族学者,或者受汉语思维的影响,史料本身就是对少数民族的他观,缺乏少数民族的自观,一些信息是失真的,由于跨文化语言障碍,加上少数民族的心理防范,要弄懂少数民族内部深层文化生活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史料记载的是脚饰、服饰、头饰、发饰、住宅、出行等等。因此高立士说:“外族进入者经观察研究, 凭自己的印象得出结论来划分称谓民族支系,加上汉族官员和商贾的只言片语,导致今天史学界区分古代民族称谓的混乱。”[4]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研究者,要走进少数民族集体记忆及民族社会的田野。
(2)识别标准可商榷性。民族实体论者认为民族是一种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 其基本的研究路径是通过对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和语言材料的考证、排比, 归纳出若干典型的文化特征, 再与某一民族联系起来, 并描述该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进程。为了说明民族的实在性与延续性, 学者常常强化某些文化特征来加强认同, 同时忽略另外一些文化特征来淡化区分。[5]虽然今天的民族由古展而来。民族文化发展变迁过程中数次删除和加入新的信息。正如何明教授所说:“现代的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群体之间, 虽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联系, 但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是说,当我们考察哀牢的族属的时候,不宜使用现代的“民族” 概念。[6]
(3)形而上学的“泛羌论”和“泛越论”影响。商代卜辞中以羌为氐羌的总称,殷商人用来泛指活动于西北高原上的游牧部落。
羌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物质生产主要是以游牧业为主。部分部落有父子联名的命名风俗。社会组织处于酋长部落阶段,且部落众多。兄亡弟娶嫂,弟逝兄娶弟媳的转房制。尚左尚黑,披发左衽。火葬习俗。这些文化特征是对西北地理自然环境适应而产生的。我们习惯把历史时空中所有的羌人文化信息叠加在一起,形成一个“羌”的概念。面对我们要识别的对象存有的文化信息,诸如火葬、转房、游牧、无君长……我们就会草率地认定是羌文化系统,认定为是氐羌。我们看到羌文化的同一性,更应该看到羌文化的区别。陈连开先生认为:“商羌和秦羌都不一样,今之羌与古羌虽然有渊源,但是不能画等号,古羌作为一个族群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则不可。”[7]西羌是以华夏的政治中心来命名,真正含义是羌在华夏之西,王明珂认为,“羌”并不是世代居住于中国西部的某一“民族”, 而是代代存在于华夏心中的, 一种华夏对西方边缘异族的概念。[8]王文光教授认为: “越人从夏、商、西周时期开始就是一个他称, 是指使用‘戉’这种生产工具(或兵器) 的人们。由于内部‘各有种姓’。百越民族的分布从我国的江苏省经浙、闽、桂、黔、滇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到印度的阿萨姆邦, 呈半月形。此足以可见, 百越族群规模之大、人数之众。”[9]越从语言学看,今天他们成了壮侗语族各民族,如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傣族、黎族、仡佬族。 “泛越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把现在壮侗语民族和古越人完全等同起来,把现在的壮侗族各民族文化信息叠加起来认为就是古越人的历史状态。第二就是在把现在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居住地认为是古越人的分布地。因此林惠祥先生认为:“在中国东南、南部直至越南这一越族分布地区, 在西周有杨越, 在春秋有于越, 在秦汉有瓯越、闽越和南越等。将越族分布地区确定在中国东南部和南部, 直到越南的北部, 是大家较一致的、适当的看法。因此, 研究百越民族文化特征, 也应以这一地区的越人为准。”[10]第三“泛越论”还表现在把历史上东南亚古文化与古越人的文化等同起来,忽视了古代东南亚这个区域还有其他族群。凌纯声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包括东南的百越与西南的百濮) 与南洋土著的共同文化特质, 除了扩大到中国西南部地区外, 有些文化特质如铜鼓, 却是东南越族所没有的。[11](P25)文化是古代民族识别的标准。而文化的多样性, 决定了其作为标准的非单一性。[12]
三、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哀牢族属研究
历史上的不同文化和社会生活与当代社会处于不同的时空域, 因而其社会及文化的整体自然与当代社会截然不同。要真正弄懂其社会及文化含义, 绝对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加以解读,而必须借助那个时代的观念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13]虽然各个社会可以有不同的时间表述与记录的方式,但各个社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建构其历史。简言之,世界没有“无历史”的民族[14]所幸在人类学的反思中,人类学者逐渐认识到,在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他者”的范围内,也包括数量众多的个别历史( separate histories) 。[14]因此我们需要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致力于走进那个时掘出新的历史信息。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 即人类学的“历史”(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15]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16]批评传统史学中的“中心论”。它自觉发掘没有被官方或正统史家记载的历史,即由没有发言权因而不能成为正统史学模特的人所创造的历史,亦即下层民众的历史,让“沉默者”发言。[17]
(一)把史料他观与民族自观结合
尽管人类学界对派克主位/客位(emic/ etic) 的描写理论存在不同的理解与看法,但这一新的认识论所表现出的力量却在推动人类学朝着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18]早在马林诺斯基的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当地人的想法(native think),在60年代认知人类学中曾经引出很多辩论的主位(emic)和客位(etic)研究法,至今仍然是一代代学者讨论的东西。[19]现存的少数民族史料,大多都是边疆内地化过程中记录下来的,后来研究者也是用仅有的汉文记录本来推断哀牢文化,因此看不到哀牢文化最初的状态。我们需要从哀牢有关的现存民族中去寻找哀牢文化信息。
(二)把精英历史向大众历史转变
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19] 除显要人物的历史外也应给小百姓历史一个地位,“年鉴学派观念的更为深刻之处,是将历史研究建立在一种从多种范围研究社会现实的观念之上。”[20](P235~236) 哀牢族属研究离不开对女性、边缘人,以及“无声”民众的关注。如果哀牢族属研究还局限在上层统治者,探索不到哀牢文化的民众或中下层部分,哀牢族属混乱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三)把民族文化研究从表象向深层民族文化核心推进
广义的民族文化特征应包括生产文化、社会文化与精神文化三方面:所谓生产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生产部门和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中的特征; 社会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丧葬等社会生活中的特征; 精神文化则指一个民族在艺术、歌舞、民间文学、等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中的特征。 [21]这些文化特征都是我们走入民族社会的钥匙,了解了民族文化的结构、表层与核心,就能把研究向历史纵深处推演。
(四)科学对待民族口传文化及文献资料
民间口传文化作为人们民间活动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洞察一个民族丰富的文化生活。族源传说将一群人凝聚起来,以这种选择性的历史记忆, 强调他们部分的文化特征。[22](P137)学界认为, 历史记录、传说、故事、象征、仪式等成为人们传递异己、感觉的重要文本。传说是一个族群(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对相似性认同的一种主观的信念, 一种在特定聚落范围内的共同记忆[23]。尤其是西南民族的洪水神话,祖灵观念下的指路仪式,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忆,而且把这个强大的历史记忆一直指向遥远的历史时空。[24]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的先辈用傣文、彝文、东巴文、古壮文或汉字记录社会信息形成很多文献典籍,包括占卜、医药、天文、历法、宗教、民族迁徙、祭祀、庆典等内容,是研究民族历史,探究遥远时空先民活动的重要典籍。诸如彝族《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六祖史》,白族《南诏野史》,纳西东巴经,傣族贝叶经等。
(五)民族田野需要推进
“田野作业”(field work) 方法的引入,使学者们在看待和确认事物的表象和意义时, 有一个基本的“历史现场感”。它意味着要回过头去了解人们的饮食起居、姿态服饰、风俗习惯、技艺文化以及它们所建构的历史语境。[25]它改变传统史学只重视精英文本的倾向,田野研究和田野文本是对历史重新解读的重要方法,也是理解平民史、连续史和当事人想法的主要研究手段。哀牢族属研究我们必须认识到哀牢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首先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地点是古哀牢国,古哀牢不等于现在的保山地区,古哀牢人也不等于就是目前保山市地域范围的几个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不局限在保山辖区,也不能局限于百越、氐羌、百濮系统,还应该有古夷人,包括现在藏缅、壮侗、孟高棉及苗瑶语族的族群个体及他们的文化世界。
小结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自然气候,使云南成为历史上少数民族迁徙的理想家园,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自北向南的走向,使得横断山成为民族迁徙的文化长廊,红河、珠江流向东南,为古代的民族迁徙提供了自然地理基础。客观上中原文明不断地向周边推进,战争、自然灾害,使得华夏边沿的族群需要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云南开始成为民族迁徙的理想空间场域。因此古哀牢族属之争背后是云南古代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由于与中原文明联系较紧的羌、濮、越三大族群都被史料所记载,而云南古夷人却没有被记录,导致哀牢族属研究中的单一濮人说,泛羌说、泛越说。传统的历史研究在哀牢族属研究上有着种种缺陷,缺民族自观、缺下层群众、缺民族口传、缺民族古籍、缺民族田野等,导致我们现在哀牢族属研究继续历史误读、强加。导致我们现在哀牢族属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待进一步梳理和厘清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象,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来观照和审视哀牢族属研究,给民族学、历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另外一种看的视角,将会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哀牢族属问题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1]白寿彝.座谈会上的开场白[J].史学史研究,1985,(2).
[2]张舜徽.大名府志序.中国古代史籍举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3]耿德明.哀牢族属百年争议的再认识[J].保山学院学报,2010,(1).
[4]高立士.傣族支系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6).
[5]陈心林.历史人类学研究典范之作——评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1).
[6]何明,李东红.哀牢文化的性质与开发研究[J].学术探索,2006,(10).
[7]陈连开.夏商时期的氐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93,(4).
[8]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上海:中华书局,2008.
[9]黄现璠.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J].思想战线,1982,(1).
[10]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1]陈国强.东南越族文化特质与铜鼓[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2]刘仲华.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3).
[13]杨庭硕.从文化人类学到历史人类学[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1).
[14]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15]王铭铭.历史人类学[M].中国人类学会通讯,1998.
[16] P.1Hastrup,Kirsten.Culture and History in Medieval Ice land :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e and Change[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5.
[17]保罗·利科. 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M]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8][美]郝瑞.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A].巴莫阿依,黄建明.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19]张晓军.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1,(7).
[20]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A].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1]陈国强.论百越文化特征[C].中华文化论坛,1999,(1).
[22]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8-0046-02
作者简介:袁莉萍,女,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专业搜索引擎、教育资源建设和网络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1XJJC710001)和塔里木大学高教研究项目“我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实效性研究”(项目批注号:TDGJ1118)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2007年《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正式成为新疆高校各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的通用教材。这本教材共十章,其中历史观教育的内容占三章,主要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地区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占五章,主要说明民族与民族问题、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占二章,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该课程在加强大学生历史观等方面教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这门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为此,我们进行《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对加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极为重要。
一、改革教学内容
首先,教育部门要联合少数民族学者和汉族学者共同编纂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许多学者提出了该课程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上的不足。例如,宗永平认为:“教材内容的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教材某些地方重复现象较多”。吴恒同、陶小平认为该课程存在六个问题。例如:“《教程》目的与内容的矛盾;《教程》的政治性与内容广博性的矛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矛盾;部分章节篇幅与逻辑问题;《教程》与《中国近代史》的衔接问题;民族学生、民族教师语言障碍与教辅资料不足问题。”尽管自2000年以来学术界出版社了诸多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比如厉声先生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余太山先生主编《西域通史》、马大正先生著《新疆史鉴》、李树辉先生著《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等。然而,与悠久历史、民族多样和文化多元的新疆相比,这些分量仍然较少。尤其是被民汉学者一致称道的书籍更少。鉴于以民族划分新疆大致存在两种学术圈:一是汉语言学者学术圈,二是民语言学者学术圈。民汉学者沟通相对较少、民汉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汉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民语言、民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古汉语、民族与族群概念的混用等导致民汉学者对新疆历史的某些问题他人非5存在诸多争议。因此,我们必须出版民汉学者公认的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工程,“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实际情
况……编写一套分别适用于学校、工厂、农村、干部教育的教材。而教材作为使用量较大、发行面广、内容最成熟最基本并用于教学的一种有形载体,具有社会性、基础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学习性等特征。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需要,不仅要编写视觉教材,还要与之相配套编写听觉教材、视听教材。”这样能为新疆和谐发展奠定持久而坚实的基础。
其次,将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作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新世纪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加紧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大肆宣传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导致部分高校学生国家观念出现偏差,国家认同出现动摇。”新疆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维吾尔传统医药现已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维族传统药材主要是按照阿拉伯字母的顺序和药物功能等来分类,并且药材的名称是从维语直译为汉语。从中看似维药不同于中药,其实不然。维吾尔族传统医药材仍延续我国中医药材的传统,它们由矿物、植物和动物药材组成。‘植物药分为花、叶、皮、根、汁、果实、油、子等;动物药有毛皮、角、乳、油、粪便、蹄、血、蛋、皮、骨髓等;矿物药分为盐类、石类、金属类、宝石类、石油类、土类等。’据此,维吾尔族传统药材的起源和发展均与中华传统中医药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以中华文化反击所谓的“泛伊斯兰主义”、“共同突厥文化论”。 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文化馆和“博物馆作为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所以,我们要在全疆范围尤其是南疆每个县市建立中华文化的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以实物、遗址、遗迹等展示中华文化在新疆的悠久历史,以此对抗境内外分裂势力。只要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实践教学课程中参观该馆就被灿烂的中华文化、厚重的西域历史感染,那么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会形成比较正确、客气和全面的历史观。因此,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是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基地。
二、改革教学手段
首先,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的一堂课是否符合创造性教学的思想,最主要有两个特征:问题性和探究性。每一次授课形式上保持讲授法、讨论法交替使用,突出问题性和探究性。问题式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作为载体,把教学内容问题化,通过问题来展开探究,以问题解决来建构知识的教学模式,操作策略是:创设情境,提出问题,研究假设,自主探究,解决问题,应用一般。这一过程伴随着师生互动,合作交流,相互学习。对于探究法,教师应注意讨论的前期准备、讨论内容选择、讨论氛围把握、讨论过程调控等环节的驾驭。”总之,只有以多种教学手段才能达到教学效果。
其次,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教学方式,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课题曾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组织了问卷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最受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的依次为‘看电教片’、‘社会实践、演讲、辩论’、‘专题报告’和‘传统授课’,比例分别为43.2%、35.7%、16.3%和4.8%。可见,前三种教学方式因能调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在参与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受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青眛。”目前我们的教学方式绝大多数以“传统授课”为主,还要增加学生辩论、专题报告和电教片的力度。比如,我们针对新疆曾创造灿烂的丝绸之路文明,让学生讲述新疆丝绸之路印记的主题报告,以增加学生对新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认识。
三、改革教学考核
首先,高校要逐渐改革考核方式。《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该课程的教育,“通过外在的思想交流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观念,变他律为自律”,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因此,考核方式主要是对学生思想观念、学习过程、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考核。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是以考试为主。考试作为最后的评判标准,在某种情况下是很难准确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我们可以推行如下考核方式:即平时成绩(30%)+试卷成绩(50%)+课外实践教学(20%)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为课堂表现、上课出勤、平时作业等。试卷成绩按照民汉学生采取不同方式即民族学生采取开卷考试,汉族学生采取闭卷考试。试卷题型一般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课外实践教学主要为读后感、观后感、讲课成绩、演讲比赛成绩、调研报告等。这样的考核方式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情况。
其次,高校要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切实增强学生的认同感,使学生主动认识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环节的安排,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口头交流以及写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要做好《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工作,就必须长期坚持‘三结合’原则,即与课堂理论相结合,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课堂的教学、校园文化的活动以及学生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总之,《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上都需要进行创新,增强课程的实效性,让它成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课程。
参考文献:
[1] 宗永平.关于新疆高校“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教材及教学存在的问题[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3).
[2]吴恒同,陶小平.《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中的问题和对策[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1).
[3]徐杰舜,徐桂兰.加强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的现状考察与对策[J].西北民族研究, 2004,(3).
[4]杨丽,黄艳.新疆高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教育的历史沿革与经验总结[J].新疆大学学报,2013,(1).
[5]张玉祥,廖肇羽,陈晓艳.论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J].兰台世界,2014,(5).
[6]李瑞君,郑昆亮.《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教学设计创新探析[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3,(5).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7
杜赞奇在其力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开宗明义,首先从西方哲学根源方面对传统的“线性进化史”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历史当作认知的透明媒介,以它讲述过去和昭示未来,殊不知人们时刻依赖的历史是“一种使历史人物(包括历史学家)得以用来阻碍、压制、利用其他讲述过去和未来的方式”。也就是说,此种历史一旦被视为杜赞奇所说的“话语”,人们即发现传统历史的建构多以“线性进化”观为外壳。杜赞奇重温欧洲近代哲学传统,目的就是从中探究线性的、进化的历史的哲学根源。
19世纪,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要属“生物进化论”,这种原属生物界的理论后来被借人人类社会而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演变或者说契合,首先可以“与保罗・李科尔有关历史时间的哲学阐释挂上钩”。在无限的宇宙层面上人们的生命周期微不足道,但在人们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理解无限呢?因为“历史时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了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人们由此可以将生物进化的思维移植和应用于对人类发展进程的认识。在这一层面上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认识论找到了契合点,“进化叙述结构”由此形成,“它通过历史主体为未来增加了一层稳定感”。李科尔关于历史时间的哲学论述或许值得商榷,但其强调历史主体作为稳定性的进化载体,为人们由此可以将生物进化的思维移植和应用于对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在这一层面上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认识论找到了契合点,基于此种历史时间观的“进化叙述结构”由此形成,并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接下来的成果之一便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它“是我们了解线性目的论的、进化论的历史的最重要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目的……不过是精神即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展现”;只有个人与精神的浑然一体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历史的终结。在黑格尔的哲学命题中,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普遍化的历史观是凌驾于其他时、空体验形式之上的,它不但否定了“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可理解性,而且“理性”尺度可以把民族与国家之间人为地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甚至“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去启蒙之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圈形成之后,“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角录,19世纪帝国主义被美化成现代文明与野蛮状态、民族国家与封建帝国之间的原则斗争”。杜赞奇对“线性历史”观的批判从李科尔“历史时间观”所倚载体(历史主体)――民族――开始讨论,因为“民族存在于历史之中,又在其终结处”,它游离于历史的控制之外,而作为历史主体又不得不每时每刻被复制,以至于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因为其本身的可塑性或可创性不能完全消除李科尔所叙之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困顿。简言之,民族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时代变异很大,围绕民族出现了诉诸于文化、阶级、宗教等的民族主义。
在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民族意识通过战争和自由贸易经济纽带在国家的盾牌下得以强化,其民族的内涵与现时代民族的内涵大相径庭。尽管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下,诸如梁启超、雷海宗等中国知识分子发展了一部“线性”的、“进化”的中国史,但正如杜赞奇所指出的,雷海宗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欧洲史学解构历史的霸权手段;而另一位史学大家顾颉刚则揭示了正统学术是怎样淹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替代性的或对立性的潮流与传统。这也正是杜赞奇所极力倡导的一种精神,他提出了一种“复线”的历史观点,“一种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传播(transmission)的历史”,从而把存在的多种叙述结构从主流话语中解放出来。
作为对“线性历史”的批判,杜赞奇在对中国历史的个案研究中运用了“复线”历史观,他尝试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尤其在晚清中国社会对政治群体的表述的研究中,杜氏认为至少有两种表述:一种是建立在先天性原则之上的、排他性的、以汉族为中心的表述,一种是建立在中国精英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念与学说基础之上的表述。也就是说,“文化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纠缠在一起,对清朝以前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群体进行规范与界定。当中原王朝鼎盛之时,“文化主义”(或“中国文化主义”)把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而每逢另族入侵时,汉族与国家的观念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述会强烈凸显出来。中国历史中的政治群体是以“文化主义”与“种族主义”两种或多种叙述结构交叉、波动地界定的;后来的“民族”亦是一样,尽管其构成实体经历史绵延而形成,但其群体边界的界定多半是多种话语“磨合”的结果。与那种认为群体是稳定的、像物种进化一样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自觉的观念不同,“复线历史”首先肯定了群体的构成可以通过改造群体界限而有所变化,从而否定了“线性历史”中历史主体的稳定性。
二、时代的中轴――“民族国家”
既然“复线历史”观寓意着“群体”本身具有流动性,我们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围绕“民族”产生了以语言、宗教、文化等为核心纽带的诸多类型的民族主义。但是,为什么当民族主义的政治性色彩愈来愈浓时,其本身会倾向于与国家形式相结合而形成“民族国家”呢?
首先,多元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及其对“国家”形式的“缠绵”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自决”哲学传统的传承,这种以“民族”作为历史主体,以理性精神为指引的、残缺的哲学缔造了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的、动荡的但同时相对和平、稳定的时代格局。黑格尔坚信:“只有具有充分历史意识的国家才能实现自由。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组织和帝国之类,既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是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哲学 探讨的主题之一。另一位哲学家康德对个人自由意志给予了肯定和发挥,认为“道德从自我立法出发,并且不能被原来的事物所束缚”,其他的限制对自律的人没有任何意义(意志自律学说)。之后,费希特发展了康德的此种学说,相信“只有依靠公民间的联系,人才能获得某种格局中的确定位置和在自然界中的稳定性”,“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完全融于普遍的意识。……只有当他和国家成为一体时,个人才能实现他的自由”。④在费希特看来,国家由此与个人、民族紧密相联,国家的职责是使用可以被理性决定的手段,为版图内的居民带来最大的幸福而实行统治,突出了国家与国民(nation)的关系。“nation”一词起初指一群人,这些人由于有相同的出生地而被归为一类,大于一个家庭小于一个民族;后来“nation”一词代表多种大小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的群体。直至国家与民族被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加之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国家与民族在哲学上的“暧昧”关系才逐渐转为清晰,民族主义学说同时亦得到了发展。
其次,“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产生并且成为当今时代主要的政治组织形式有其具体的历史渊源。“民族”概念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是建立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新政治实体形式的需要,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一类群体和身份认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资源共享和市场统一,“工业化创造了流动多变的、文化上同质的社会”,这些必然在上层建筑中反映出来。马克斯・韦伯说道:“在显然是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的背后,都总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很清楚地根植于政治的领域里,‘民族’的概念导向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愈受重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似乎愈紧密。”即使“民族主义”被粗略区分为“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四大类话语或叙述结构,但由于“民族”本身与生俱来受政治目标的影响,诸种“民族主义”话语或思潮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基本的政治诉求,并且与建立“民族国家”密切相联。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诉求,在欧洲各地建立的第一批以“民族”为基础的“原生型”的“民族国家”中表现得很为明显:新生的资产阶级力争建立“本民族”的政治实体即“民族国家”,以保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资本、劳力和产品市场。“而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为其合法性基础的‘民族国家’之后,这样的国家模式必然会对周围各国,甚至殖民地的知识分子造成影响。”“民族国家”模式的成功后来转变为一种无形的思维惯性,使周围各国及被压迫民众的精英们以此为导向,在政治上努力争取本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之后,世界人类史上出现了多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民族”的政治性诉求借助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的传播,变为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现象。
此外,伴随“民族国家”产生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世界被粗略地划分为“文明”和“野蛮”的对峙,弱肉强食成为时代的潜规则。人们看到“民族国家”模式催生出强大的帝国及其带来的对世界的强大震撼力,在自我所处历史境遇中找不到除此模式之外拯救民众的第二种方式,在其他范式缺失的情况下,只能将“民族国家”模式奉为正统,从而争取“立国图强”,跻身于世界。
这种缺乏反思的对建立“民族国家”的狂热追求在中国晚清之后的各种话语中也有体现。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把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置于“复线历史”观的视野之下,把形形的话语和多种叙述结构并置于一个历史境遇中进行比较研究。在中国学者中梁启超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描写中国历史,其在中国语境里复制了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梁氏还批评中国传统史学按王朝纪年划分历史忽视了对国民历史的描述。在“”失败之前,梁氏主要倡导“封建”式变法观念以救国图强,但这种“封建”叙述结构的渐进主义话语很快即涉性很强的国家政权所消灭。在“”失败以后流亡日本期间的数年之中,梁氏思想观念转向国家主义,最终相信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历史进化的必然结果。在孱弱的中国,梁氏最后转为诉诸“民族国家”叙述结构和民族的统一来抑制历史的动荡。另一种话语的代表人物在《民族的国民》(1905年)一书中认为,单一“种族”组成的国家要好于多“种族”组成的国家,为了汉民族的纯洁性,必须同化其他种族。正像杜赞奇所指出的:“汪氏的文章表明,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使他们对民族的想象合法化,而且对其世界观起了结构性的作用。”后来,孙中山接受并发展了汪氏的这一学说,但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在面对蒙古、的分裂运动时,又不得不改为“五族共和”。这种话语的转变或许是一种政治策略,但其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有民享”的共和国的目标没有改变。诸多话语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最终殊途同归,把“民族国家”的建立作为一个宏伟的目标。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多种话语的主题是如何构建民族主体以建构“民族国家”,这正是“复线历史”观所蕴含的内涵之一――主流话语追逐着时代的主题。
三、“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磨合”
“复线历史”观的第二层内涵是多种话语和叙述结构并存,力求展现主流话语以外的其他话语,从而发现真正的历史。在“民族国家”话语占据主流地位之前,中国存在着列文森所讲的“文化主义”的传统认同观念。中国文化传统中处理族群关系的国家目标,就是维护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天下”和“子民”,并以各种方法来努力向四周“蛮夷”施以“教化”,使他们接受中原王朝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秩序。但是,中国这一以“天下”为认同范围、以“文化”为认同核心的传统,在近代遇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之后不得不发生变化,以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只有当19世纪晚期面对着‘他者’的挑战,文化价值不得不寻求合法性时,我们才开始看到‘文化主义’的衰弱并迅速向民族主义发展。”杜赞奇主张从一种“复线”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复杂历史进程,他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的观念与思潮当中。当中原王朝强大时,汉族人会表现得宽容和开放,以“天下”为视野,以“文化”为核心的族群观成为主流;当中原王朝衰落和外敌压境时,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关于“民族”的内容和界限多通过历史精英分子在“民族主义”与“文化主义”的相互补充下得以确定。
“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交替出现,亦即“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磨合”,在现时代同样继续着并未走出中国历史。这首先得从对“民族国家”观和“民族主义”的反思谈起。“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作用。“民族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出现的意识形态,它推动了第一批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在其萌发的初期,有利于打破当时多民族封建帝国的统治及对生产力的束缚。在实行封建统治的多民族帝国时代和 殖民地时代,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进步意义。但是,随着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结束和世界范围内国家的普遍建立,分裂现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不论是以语言还是以别的属性作为衡量民族文化的标准,“地球上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民族……无论如何不可能使所有的民族主义同时得到满足”。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民族自决权是国际生活中的无序状态而不是有序状态的主要创造者”。黑格尔以“民族”这个不稳定的共同体为历史主体建立起来的进化哲学,其阴暗面正逐渐显现出来。哲学上的这种残缺被政治家利用之后,“民族”的政治性便越来越浓。人们发现,民族主义者的理想与现实可能性之间、与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进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为了改变“民族”与“国家”之间畸形的关系和淡化“民族”的政治性,学者们换了一个思路,开始讨论如何使“民族”逐步实现“非政治化”的问题,同时“族群”和“族群‘文化化”’的提法也相继出现。“族群‘文化’化”的提出是由于意识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族群”和“民族”两个核心的认同意识层面可能会发生相互之间的转换。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族群”,当其与社会主流族群发生矛盾并考虑以独立政治实体的形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时,就可能会通过“民族主义”运动来争取族群的政治独立而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从而转变为“民族”。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8
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许多特色,为今日许多号称文明先进的国家所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四千六百余年,自《竹书纪年》以来,约三千七百余年;(二)无间断,自周代共和行政以后,有年可考,自鲁史公元纪年以下,有月可查;(三)详密,就史书体裁而言,主要有三,一为编年,二为纪传,三为纪事本末,其他不胜枚举。
而且,就时间悠久且无间断而言,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中国历史则数千年来,虽有朝代的变革,但前一朝代的历史为后一朝代所继承,所以历史和文化连续一贯,未曾间断。中间虽有少数民族和域外文化的进入,但都与主流文化融和而成为新血脉,考古发掘证明,中国历史之悠久,远超过了文献的记载,例如西安半坡和河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远超过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便是史学发达,史籍丰富。远在殷商时代,就已经设置了史官,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近代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信。殷商以后,历代以来除了史官负责记录当代的历史外,史学名家辈出,自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后,这种体例为班固《汉书》所沿用,成为此后专记一个朝代“断代史”通用的体例。其他史书的体裁还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也有专记典章制度的文化史,历代累积的史籍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仅一部二十五史,就有令人“蔚为大观”之叹!中国史籍之丰富为今日各国所不及。梁启超曾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可见并非自夸之词。
二、历史的功用与历史认同
历史是否有用,在现代某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受到了怀疑,但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功用是被肯定的,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历史具有“垂训鉴戒”的功用。例如,西汉贾谊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唐太宗的名言:“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近代学者,则深知,历史具有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操的功用。“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有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
除了上述以外,历史显然有保留“集体记忆”及逻辑思维的功用。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历史的功用,所论甚多,有关这方面的名言名句根本无须赘述。我们需要注意的应是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
现代许多人质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概源于对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功能不够了解。笔者以为,就历史学的教学而言,它的性质至少具有以下三项特征。
1、它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科。清人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出自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历史学科与民族精神教育的关系,是毋须多言的。有关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性,论者颇多,但在实施上,我们必须从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奋斗的艰难历程以及文化上辉煌的成就,近代中国的忧患和挫折,以及当今应有的警示和努力。这样,民族精神的教育培养才能落到实处,我国的的历史教学宗旨即特别强调这一点。
2、历史是民族文化陶冶的学科。西方学者指出:“人类是文化的动物”。作为一个现代的国民,除了具备世界的眼光和胸怀以外,更要有中华文化的气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诸如忠恕仁爱之道、四维八德的精神,都需要透过学习历史加以陶冶,使历史知识和民族气质内化成人格的特质。
3、历史教学具有公民素质教育的性质。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应为世界各国教育的主要目标。我们常说教育乃百年大计,那么健全的公民教育不啻是实现此百年大计的总目标。各国的公民教育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公民教育不能从国外移植,它必须在本国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生根,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的密切关系,也就可以想见了。
历史学科的性质既如此,那么各级学校实施历史教育,显然是属于国家的责任。这与数理或技艺科目相比,在性质上也就迥然不同。历史的认知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数理或技能科目一般,超然于国家民族的界线之外的,也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传统而不顾。总而言之,它是有主观性、有特定立场的一门学科。因为历史不是技艺或实用的学科,我们如以“实用”要求它,质问历史有什么“用”(这里的“用”人们通常指的是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效用”),当然是错误的。据学者归纳,“历史”这一概念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广义上,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
(二)狭义上,指人类社会史,只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水平。
(三)习惯上,对历史的记载和阐述也称历史。如正史、野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
就“历史的记载和阐述”而言,很显然,着者是避免不了主观立场的。例如以三国的历史来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对于诸葛亮北伐之事则记载为“诸葛亮寇边”。但是南宋朱子的《通鉴纲目》因以蜀汉为正统,所以对诸葛亮北伐这同一件事,则记载为“丞相讨贼”。同样的历史事件,出现完全不同的记载,并不是着者任意歪曲历史的真相,而是由于立场不同的缘故。历史的记载和阐述固然应力求客观,但同一史事,涉及两国之间的关系,则立即出现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便是由于有特定的立场之故。“历史认同”,实则以“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为基础,一旦记忆消失,“历史认同”也就会随之改变,爱国情操、民族精神也就会随之消失或改变,清人龚自珍指出“灭人之国,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沈论》),其道理就在于此。影响一个时代人群的政治观、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时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与青年早期(约当11-25岁之间),因此青少年(甚至年轻成人)的社会记忆成为受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
三、民族凝聚力与历史认同
“民族”一词的概念,学术界似乎还没有一致的共识,中文“民族”一词,乃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年(1903)把欧洲政治理论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民族”一词才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欧洲政治理论认为民族有八种特征:1 .同居一地;2.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经济生活)。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形成民族的五个因素: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孙先生对“民族”一词所提的概念,影响颇为广泛。
今日的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据芮逸夫先生在《中国民族》一文统计,中国民族可分七个宗支,七十五族,共56个民族,其中最大多数为汉族,其他为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其中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最多。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如同江河,河流越长,汇集的支流也就越多,中国民族的情形正是如此,它在悠久历史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新的成分,吸收了新的血液。例如春秋时代的“蛮夷戎狄”、魏晋时代的“五胡”、宋元时代的契丹、女真、蒙古等,即是明显的例子。今日我们习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固然以汉族为骨干,但也已成为各族的共称。梁启超在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是指汉族,但也包括中国各民族。他说:“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见《饮冰室文集》第41页)
“历史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异常的作用。春秋时代的“诸夏意识”为先秦时代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基础,但其时的历史认同并不十分强烈;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历史系统逐渐形成,这一系统的主干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帝喾、尧、舜、夏、商、周。此后,凡是被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或边疆民族,他们除接受了汉式生活方式之外,便是在精神上认同了这个历史系统,而自认为这一历史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例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族建国的国名有采用“夏”与“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宇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而“鲜卑族”为黄帝少子“昌意”之后。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这是一种从历史意识中所产生的历史认同之表现,实则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变成了汉人、汉人变成少数民族的事例也并非一二。所以,历史认同应为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
四、结语
民族的构成要素有物质基础和精神积淀,前者如体质、经济生活,后者如语言、风俗和等,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其精神基础的深层结构应是“历史的认同”,关于这一点似乎被历来的中外学者所忽略。
中国自古以来有敬天尊祖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相对较淡薄,所以“历史认同”对于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其作用远大于以上所列诸要素。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体质相同、经济生活相同者,未必就能凝聚成一个民族而不分散,语言相同、生活习俗相同、宗教相同的民族,走上分裂之途者也不乏其例。“历史认同”的先决条件是保留“历史记忆”,一个失忆的民族,也就无从产生历史认同。所以保留历史记忆应是近代国家各级学校中设置历史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保留“历史记忆”必须通过一种历史意识,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或“这是他们的历史”,才能产生“历史认同”;有了“历史认同”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警语。历史失忆必会产生“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结果而不自知,“历史认同”发生错乱,必然会产生对民族或国家的疏离感,逐渐地也就不认为是这个民族的一份子了,可见“历史认同”之于“民族认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几年前台湾当局在初中一年级实施“认识台湾”新课程,令人担心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会发生错乱,最近几年,又在草拟九年一贯课程,欲以社会科“合科”的名义,将历史、地理等学科消失于国民教育之中,并于2001年付诸实施,如果其企图得以实现,则势将造成下一世纪台湾的青少年历史失忆。一旦“历史失忆”,自然就不会对中国历史认同,当然也就不会对中华民族认同了,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深刻的历史性思考。
参考资料: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6月。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③ 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④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9
一、达斡尔历史研究现状述评
达斡尔族的研究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成果丰硕,在语言、艺术、宗教、风俗等方面的研究百花盛开,相形之下,政治学、史学领域则显得寂寥许多。很多情况下,达斡尔族史学研究成为民族学研究的背景和注脚,很多专著仅仅是把达斡尔族历史进行线条化的简单描述,其中也不乏以讹传讹之举。
在史学研究方面,专著有限。关于族源问题是一大热点,陈述、孟志东、巴图宝音等学者均做过论述。2011年出版的《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论》一书收录了不同时期的相关论文。通史方面成果较少,信史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达斡尔族简史》以及新近修订出版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后者篇幅主干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历史研究只是枝节。新近出版的《达斡尔族百年实录》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历史风云、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人物、文化风情等五部分,从多方面、多层次介绍了达斡尔族的百年发展变化及民族特色,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中国达斡尔族史话》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
在论文方面,关于清代早期达斡尔族历史,已有若干篇论文。如莫日根迪《十五至十七世纪达斡尔族历史概述》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03);亨利・G・施瓦茨、 冬瑛译《达斡尔族的早期历史》(民族译丛1993,03);吴扎拉・克尧《清代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研索――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05);乌卫斯・卫戎《黑龙江领土的陷落与黑龙江将军衙门移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01)等等。关于达斡尔族的经济文化变迁,论文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代表作如陈烨《达斡尔族经济变迁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2(2)),孙东方《达斡尔族的文化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06)等等。
总而言之,对于达斡尔族历史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仍有所欠缺。主要缺憾有以下几点:
1.历史著作中注释不详,无法确认文献出处,致使论述遭到真实性和可靠性质疑。
2.研究时段多集中于清末以前,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仍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3.v史研究多集中于族源、教育、文化等方面,政治和社会方面成果较少。
4.单纯的历史研究较多,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很少。
二、民族国家视阈下政治与社会的互动
在历史研究当中,若单纯以历史学科的概念、范畴来研究民族史,做考证性的文章是可以的。但若要重新描述和解释过往的历史,得出新认识,则非采用多学科的方法不能奏效。达斡尔历史的研究,要借助民族学的视野、范畴和方法来使研究更加深入。民族国家是民族政治学的常用概念。从实质上看,民族国家就是以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国家。近现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度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活剧,时至今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仍然没有完成,中国境内任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宏观背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尤其是民族史需要在民族国家视野下拨清云雾,还原本真。
在研究民族史的某一方面时,还应借助该方面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如研究民族政治史、社会史可以借鉴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产物。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威的产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的社会根源、社会结构与政治、社会与政治变革、政治精英和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反作用等。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会发现少数民族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很强的。以达斡尔族为例,清末至民国时期,达斡尔族地区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由旗制向民治转变,自然是大势所趋,但是民族地区往往经济落后,民族传统根深蒂厚,社会惰性强大,骤然使之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必然无法适应,因而产生诸如匪患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我们研究民族史帮助很大。
在对民族史的研究过程中,近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相错杂,改革与起义此起彼伏,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期,政治与社会发生着巨大的转变,此时期各个民族的历史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以达斡尔族地区为例,达斡尔人世居的西布特哈地区在近代处于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第一,由混合制经济形态向单一制经济形态转变。如上文所述,在清朝乃至民国初期,当地人经济生产方式多样化。而在大量移民迁入,土地大规模放垦之后,当地土著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第二,由不承担国家赋税转变到承担繁重捐税。清朝时期,旗民不纳赋税。民国时期,当地为筹措警察、教育事业经费,开始征收繁重捐税。第三,由民族聚居向民族杂居转变。清朝时期,西布特哈境内聚居民族是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各民族之间基本和谐共处。民国时期,西布特哈地区迁入汉族移民。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不同,当地土著与汉族人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现象。第四,当地土著的生活由衣食无忧变为饥馁交加。在清朝时期,当地土著作为旗民领有国家俸饷,衣食无忧;而在民国时期,当地土著必须自谋出路,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困顿。对这一时间段的民族史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得出规律性认识。
在进行民族史研究时,还应注意对民族世居地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以达斡尔族为例,黑龙江地区是达斡尔族的世代居住地区,清朝统治达斡尔族的衙门便设在这一地区。这一地区较好地保留了达斡尔族的历史传统,较之其它达斡尔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达斡尔族文化更具有原生性和典型性,因而非常有必要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历史进行深度挖掘。
三、 达斡尔族近代政治与社会史研究的方向
通过对达斡尔族近代政治和社会变迁的研究,还原近代民族历史,找出影响和制约民族发展的因子,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着力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黑江地区达斡尔族政治变迁过程。研究内容包括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的重大变革,行政区划的沿革,民族统治政策的变化,以及达斡尔民族政治觉醒与斗争的历史过程。
政治变迁对民族发展有重大影响,在研究时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清末民初民族统治政策有很大变化,探究国家民族政策的变化对达斡尔族的影响。
2.清末民初的“移民实边”和放垦政策对达斡尔族社会的影响。从民族国家视野来看,无论是民族政策的转变,还是“移民实边”和放垦政策,均是清末民初国家整合,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措施,只不过政府举措失之操切,因而不得民心。
3.清末民初动荡的政治局面对达斡尔族的影响。
4.努力理清达斡尔族乡村政治的兴革发展线索,探究达斡尔族乡村政治对民族的影响。
5.对这一时期达斡尔族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活动以及对本民族的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
6.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达斡尔族重大政治事件对达斡尔族的影响。
(二)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政治变迁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对政治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力。可以重点探讨以下几方面内容:
1.社会结构变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探究社会功能性结构以及社会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2.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的互动。
3.政治社会化。探究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达斡尔族政治社会化的实施过程及效果,搞清楚当时人们是不是认同和接受当时的政治文化。
(三)黑龙江地区达斡尔族社会变迁过程。具体研究包括经济发展、灾荒情况、外地移民与民族迁徙、人口变迁、教育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等几方面内容。清末民初处于历史转型时期。这一时期,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族社会踏出了较为缓慢的近代化步伐,在教育、文化等方面有了可喜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清末民初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黑龙江地区的达斡尔族社会饱受战乱、土匪抢劫、军阀盘剥之苦,近代化进程不免受挫。同时,封建、保守的观念和势力对达斡尔族的近代化进程构成掣肘,致使达斡尔族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这部分研究内容的难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析社会变迁的类型:是整体变迁还是局部变迁;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
2.分析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影响。分析自然环境、人口变化、经济变迁、价值观念变迁、教育、文化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其中经济变迁对社会变迁有很大影响。教育既是社会变迁的原因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分析社会变迁对政治的影响。
参考文献: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10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R.Wolf)和敏兹(Sidney W.Mintz)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功能论、平衡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强调阶级冲突和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对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几乎视而不见。英国曼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强调社会冲突,但从整体上讲他从没有采纳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题为《号角即将吹响》(1957年)的一项研究中,强调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广大地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利用,才日渐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1973年,由阿萨德(Talal Asad)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已经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对以往英国人类学静态的、和谐的、无历史的功能论展开严厉批判,揭示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功能论者用“原始人”来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个对殖民情境的整体性概念,没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去;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更是与“间接统”、“殖民地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作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殖民制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他们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为代表),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y,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自此,以功能论、平衡论为特色的英国人类学逐渐改观,开始注意“他者”的历史,关注隐藏在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R.H.Lowie)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11
民族认同是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民族认同是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思想政治教育统一在一起的,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民族认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要求。
一、民族认同教育的内涵
在社会主义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综合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属性、教育内容、教育目标,规定了民族认同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和教育实践的内涵。
“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在民族问题上,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它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内核,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制度设计,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宗旨的一系列看待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
在民族认同教育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一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确立了民族认同的方法论,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认同观点和看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民族问题世界观,规制了民族认同的实事求是精髓。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民族认同的手段才是民族平等基础上的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而不是民族歧视下的被迫民族认同,也不是社会强制措施下的民族融合式认同。三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民族认同的目的才是经由各个少数民族的认同来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式认同,而不是敌对势力宣扬的民族分离、分裂或是民族解体式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引导人们的政治态度,解决各类思想问题,提高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完善人格和调动积极性”,邓小平将其概括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标准和目标[1]。民族认同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相连,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所谓民族认同教育,就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全体民族成员,通过民族文化的纽带作用激发民族成员的族群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进而将民族认同转化为个人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完善人格,使民族成员在民族问题上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
民族认同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少数民族族群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教育;民族认同教育的核心是将民族认同转化为民族成员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
二、高校民族认同教育的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通常上叫“三观”教育,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五观”教育,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文化观、历史观教育。而民族认同教育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根基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是民族认同教育的内核。民族认同教育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教育、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教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观教育。
(一)基础: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观、阶级观、社会观、平等观、团结观、互助观、和谐观、融合观、发展观等。从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主要是进行历史观教育、平等团结观教育和发展观教育。通过历史观教育,我们看到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民族认同同样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确立民族认同教育的长期性、复杂性理念。通过平等团结观教育,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认同必须是建立在民族的平等、团结基础之上的,民族认同教育必须要始终秉持此理念。通过发展观教育,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根本任务,民族认同教育应成为促进各民族发展、繁荣的阶梯。
(二)要求: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教育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12
作者试图驳斥近现代中国的反现代性是遭受苦难的根源的论调,以阐发作者“把历史凌驾于其他体验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之上导致双重封闭,否定了没有历史的人们的可理解性”的观点。他在阐述线性历史的困境与民族主义的政治蕴涵时首先承认:“东亚诸社会比任何其他非西方社会都更成功地接受了这种启蒙历史观。虽说此种历史观对于实现某些现代化目标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为了摧毁和驯化‘他者’,也带来了极权与封闭。”他反复强调:“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在东亚及世界各地,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但与此同时,采用此种启蒙历史就必然要以现代性为其最终目标。”作者认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叙事是在时代和话语的张力下被“制造”出来的,历史文本是在民族主义话语利用或掩盖与线性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生产”出来的。杜赞奇自己也承认:“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无论历史活动的普遍主体还是从事历史文本塑造的史家,其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杜赞奇无疑把饱含满腔民族主义情绪的历史叙事当做后进民族反抗强势民族的有力武器。
解读杜赞奇,我们需要与其他相关著述结合来看。同样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与历史叙述的认识,美国哲学家、史学家德里克曾说:“对于理想政治而言,统治者的品德并不如组成国族的人民的团结重要;国族的强盛之路是进步而非对于永恒准则的忠诚;历史学对于达到国族富强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223近代国家以意识理性、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民族国家的集体人格性理所当然地扮演这种角色。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陈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3〕737反映出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和民族主义史学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具有历史正当性。
再来看“现代化范式”。现代化叙事以现代化为现实依托。关于现代化的认识,施耐德引用David Apter的话说:“现代化过程的特征是个别传统的逐渐没落,以及一种具有普遍性、以西方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之形成与发展。”〔4〕1“现代性是一个理性进步或是其他绝对性的观念逐渐被打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曾被认为是永恒与普遍的规则和价值被历史化的过程。在现代性内部存在着固有的紧张,一方面,试图重新建立一些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源自尼采论断上帝死了的后果,人类获得了解放但同时受到惩罚而丧失了生活的坚实基础。”〔5〕242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居于现代化的主导地位,亚非拉史家则主张现代化是多元化发展。东西方近代分野后的不同境遇是他们阐发现代化理论差异的历史根源。延续数百年的“欧洲中心论”依然是一个很强的话语场,欧美学者天然拥有这种话语权,总是居高临下地审视亚非拉后进地区,他们所指斥的“不与国际接轨”实质上是不与他们用野蛮手段建立的世界秩序接轨。杜赞奇显然是试图冲破牢笼者,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民族主义话语主导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叙事背景是列强肆虐、清廷腐朽、生灵涂炭的历史境遇。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统治者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满足不惜损害中国人民的正当利益。正是举国的悲愤强化了精英之士的激切,民族主义话语应用到中国史撰述中是必要的。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更坚定地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关于历史、民族和种族的封闭的、相互定义的话语,其中民族合法性的唯一根据是这个种族是否能像赫布斯保姆所论述的那样,适应或推进历史的进步”,“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角录”。这就把带有殖民话语色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鬼魅伎俩揭穿了。对民族主义史家来说,“革命范式”实在是一种正当且有效的武器。者鼓吹的“与国际接轨”、“告别革命”、“唯现代化论”、“补课论”等论调实在是在蔑视历史主义原则。何谓“合法”?国家遭践踏、民族遭虐杀合乎侵略者的什么法?如果合法,也只是“存在即合理”、“强权即公理”的法。在他们眼中,列强践踏一个国家国土才是“与国际接轨”。“革命范式”“不合国际法”的论调表面看是为“与国际接轨”,实质是自卑的中国人为虎作伥。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忧国忧民者有之,奴颜婢膝者有之,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是有益尝试,但认为唯有走西方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实在是大错特错,反映出国人的大国国民心态尚未树立。弥漫在史学界的绝不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也不是对现代化的推动,而是一种无视和嘲讽。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铁律。唯有在民族独立的前提下,现代化才能真正推行。历史书写归根结底是强者对弱者的审判,近现代中国历史真相早已被邪恶的胜利者们涂抹得面目全非。历史学不断遭受厚黑学的侵蚀,愚昧史家不自知而去助纣为虐,中国近代史翻案成风就是明显例子。有人声称辛亥革命是反动的,革命党武装起义和孙中山当选总统是不合法的,袁世凯代表所谓进步的生产方式,因此应当贬孙扬袁。乍一听,貌似以先进生产力的维护者自居,实际不过是新时代迷失自我的高级牢骚罢了。革命党和孙中山当然是不合法的,也正因为其不合法才显得那个时代稀缺罕见的伟大。导致国家残破衰败、民族几于灭种的旧秩序就是需要这种伟大的“不合法”行为打破。袁世凯卖国求荣、`颜复古,作为民族公敌理应受千夫所指、万众唾弃。所谓能否代表先进生产方式根本不能作为主导标准做出合理的历史评价,能否维护并发展人类数百万年积淀下来的文明水准才是超拔于庸俗之上的合理标准。否则,卑微难以遏制,“侵略有功论”、“汉奸光荣论”等更会甚嚣尘上,人类的最终文明成果将会毁于朝夕。假使我们真的“告别革命”,那我们的子孙真的会被永远误导。从这点讲,革命化叙事维护了历史的正义和史家的良知,对殖民话语支配下的历史叙事起到“祛除巫魅”的作用。历史评价是死人与活人的交易。活人利用自己活着的既得地位,依靠给阴司的死者正名,获取自己在阳间的权利。历史学如何调试、规范无知利己存在者的行为?是服膺于既有的生死格局,还是维系人类文明的水准?20世纪前期有良知的史学家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并最终找到了解决的钥匙: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从事历史叙述。民族主义史家巧妙地运用叙事技巧促使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坦途,这也意味着:“中国历史只要写得好且分期得当,中华民族就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延续不绝的历史性的民族。”国内外反动者给中国社会带来灭顶之灾,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没有议会斗争的基因,那就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扫清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也许某些论调所宣称的让列强殖民500年,这片土地上就能够矗立高楼大厦、亭台楼阁,但是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却是那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而不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民族主义话语主导中国近现代史叙事具有历史正当性,我们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而不是抓住“一切真历史皆是当代史”的救命稻草武断地否定“革命范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注释
〔1〕[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民族与历史论文篇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75―06
杜赞奇是当前美国中国学学界十分有影响的学者。他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之后,他转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同样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尤以他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下简称《拯救历史》)中建构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最为突出。杜赞奇对复线历史范式是这样解释的:“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解释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出,杜赞奇建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是通过解构线性历史范式,并针对线性历史的弊端而提出,进而揭示了其对于历史及历史撰述的认知。
一、多元的历史主体
线性历史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进化史观为其主要理论基础。1822-1825年黑格尔写下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的目的,即其进步方式,是精神即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展现。杜赞奇认为:“黑格尔强调精神的特殊性总是体现在民族中,只有当一个民族完全摆脱朦胧暗淡的历史感悟,如神话传说诗意理想并在历史中彻底意识到自我,才能够获得成数的个性。”所以,在线性历史视野里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表征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样在线性历史中同样也就构建了一个主体――民族。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理念通过其后的马克斯・韦伯等人逐步成为西方对于历史理解的主流观念。
但是,在杜赞奇看来,线性历史对于历史的这种理解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为西方国家入侵其他地区、为西方中心历史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杜赞奇认为:“进化论历史一直是优越种族进步的角录。”线性进化历史意味着停滞、落后的种族是没有历史的,而先进的民族国家由于其先进性必然要征服落后地区。“只有具有充分历史意识的国家才能实现自由,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的部落组织和帝国之类,既不能要求也没有权利。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这样民族国家又变成帝国”。在线性民族历史中落后地区必然要被西方所征服,而落后地区要是避免被征服就必然要以西方为发展目标模式,走向民族国家。这样线性历史在非民族国家又建构了民族,这里的民族就是以西方为模式的,于是“西方中心论”也就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据。“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在东亚及世界各地,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有利于民族国家以历史主体的资格进行自卫,但与此同时,采用此种启蒙历史就必然要以现代性为其最终目标。”
其次,线性历史造成了历史的压抑与遗忘。在线性历史中,杜赞奇认为由于它建构了民族这一单一的主体,那么在线性历史观里除了民族之外,其他的都将被边缘化甚至压抑与遗忘化。杜赞奇强调,线性历史不仅通过提供西方发展模式的方式建构民族,而且使得民族成为线性历史必不可少的主体。“没有主体,现代历史将毫无意义;主体在变,但不会消失。”“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身份认同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参照系总是民族。……民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暗示专业与通俗的历史:它才是历史的支配主体。”然而,民族一旦成为历史的主体带来的缺失是民族之外历史的遗忘。“即使最优秀的社会史和地方史专家也不去质疑这个前提或在理论上探求这个无时无刻不在的民族以外的选择。”因此,“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其它历史就没有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构于线性历史理念上的历史是只有民族这一个主体的。而这又直接影响到历史的撰述,即历史撰述中除了民族、民族主义之外其他皆被压抑、遗忘,被排除在历史考量和撰述之外。
为了克服线性历史的问题,复线历史首先从历史横断面的认知上进行了新的建构。杜赞奇认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历史中的主体并不只有民族一个,而是多样的,即有多个身份认同的。他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指出:“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相互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无论是在印度历史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不仅如此,在杜赞奇看来就是民族、民族主义同样也是多样的,而并非如安德森等人认为的是统一的或者具有统一功能的意识。“民族主义虽然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含差异的现象。”而且,杜赞奇还认为,在近代中国伴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还同时存在着超民族主义意识,这就意味着民族、民族主义并非是近代中国惟一的认同。那么民族和民族主义在复线历史中被认为是怎样的呢?杜赞奇并不否认民族、民族主义是身份认同,但是他认为,“使用身份认同来指称由某些表述在与其他表述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主置。”也就是说,身份的认同是在关于自身的表述与其他的表述的关系网中才得以确认的,并且在复线历史研究范式中还强调,由于民族主义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定性,那么最好把民族主义看做相对性的身份。至于民族的形成,杜赞奇依据社会学理论认为,它依赖于群体刚性边界的形成。社会学理论把群体看做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动的边界以限定其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边界可以分为柔性的和刚性的。那种代表着一个群体但又不阻止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分享或不自觉地采纳其他群体实践的一种或多种文化实践,就可以被看做是柔性的边界。“当群体界限的观念被改造,即当柔性的界限变成刚性的界限时,新的民族已经开始形成。”
由此可见,在杜赞奇看来,民族的形成是依赖于群体认同的刚性边界的形成,而在民族、民族主义内部却又是相对的、变动的、不稳定的。与此同时,与民族同时存在是其他大量的身份认同。民族、民族主义是处于这样多种认同网络中的一种,它也只有在这种网络关系中才得以存在。因此,在复线历史中就不仅要考察民族、民族主义这个对象,同样也必须从线性历史的单一性中解放出来,而顾及到其他的群体,并且要在这样复杂的网络中考察各种认同间相互竞争的关系,等等。所以,杜赞奇强调:复线历史要“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复线的历史观揭示了启蒙历史范畴之外的历 史,即被压迫者的复归。”
二、历史是复线时间中现在与过去的交易
杜赞奇通过对线性历史关于时间和因果性认识的解构进一步阐述了复线历史观。复线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复线时间中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交易。
第一,复线的历史时间。
时间对于历史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历史存在的途径和方式。然而,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中的时间观造成了无法克服的悖论。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最重要的手段是进化的叙述结构,它通过历史主体为未来增加了一层稳定感:进化的事物(不管道德上是进步的还是中性的)在变化中保持不变。历史主体是一个形而上的统一体,用来对付线性时间经验的困境,即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之间的脱节。”在线性历史中,它建构了民族这一惟一主体,而民族、民族主义的返祖现象和它的现代化目的又是悖论的(即一方面民族要在自身的传统(祖先)那里找到自己,但同时又要求与之决裂)。与此同时,杜赞奇认为,线性历史还无法克服时间上流动和永恒的悖论,即现象学时间观念是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进而产生“有限之悲哀”,“在宇宙层面上,我们的生命周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周期里所有有意义的问题都被提了出来。”虽然这两个问题在线性历史中通过建构民族这个主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加以克服。杜赞奇通过李科尔的时间哲学观点解构了线性历史在时间上的困顿。在李科尔看来,“有限之悲哀”是不能用哲学的手段克服的。由于现象学时间观念是把时间看成是无限个“现在”的连续,虽然,历史时间提供了一种连续的感觉,减轻因时间流动如一系列的现在而带来的焦虑。“然而历史连续性是靠建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来实现的,而这个统一体绝非是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民族自身并不是一种普遍性的东西,而且其无法克服在传统与现代的悖论,实际上就无法由它来解决时间上变动与永恒的悖论。相反,线性历史暴露了其在时间问题上的困顿。
对时间的理解决定了线性历史在认识和撰述历史的时候常常采用单一的分期方法,于是在线性历史中往往就能够看到诸如:古代、中世纪、现代,前现代、现代等等的分期模式。杜赞奇认为,这样单一的分期会进一步造成对民族历史之外的其他历史的压抑。不仅如此,他还分析了由于在历史时间理解上的困顿造成的线性历史叙述上的其他问题:线性历史时间上的困顿往往被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所利用;民族时间中的裂隙有时被表达为特殊与普遍的对立,在亚洲研究领域则表现为东、西方的对立;在叙述结构上的失败表现为强调民族古代本源者与强调新鲜的现代性者之间的政治冲突,既一方面要歌颂古老的永恒的特性,但同时又要强调民族的空前现代性;在“人民”的观念中也包含时间性分裂的政治蕴涵,即人民既是一个古老的但是又是民族的基础,在民族主义线性历史的框架内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那么在民族主义历史中往往就要面对这样一个分裂:一方面承认人民的基础性、现代性,但是面对着的却是古老性,于是人民的塑造与再塑造就成了时间问题在政治上的表达:历史的形而上学等同于统一体的进化。于是唤醒人民便成了众所周知的话题了。
为了克服线性历史时间观的困顿,杜赞奇在建构复线历史时就强调要对于时间问题进行反思。他认为,作为研究者主观的历史分期实际上会反过来建构客体的,“如果追问的客体被当做一个线性的实体而建构出来,那么制定分期的方法必然会决定这个客体的建构。”他以近代中国历史中通过历史分期而建构民族的现象论证了这一点。他认为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分期方法一方面直接受到西方线性历史分期的启发,另一方面他们的分期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如何建构民族这一中国历史的主体而展开。虽然像雷海宗、顾颉刚等人对欧洲史学的分期原则霸权提出挑战,但是,“雷氏始于解构历史,却归结于我们熟悉的复建民族的工程,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普鲁士王朝换成了中华民国而已。”“顾颉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属于民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杜赞奇强调:“我们处在现代历史学家的主置上,线性历史所假定的透明性使我们看不到它为了包含这些压制,为了阻止民族体内部的分裂所采用的战略。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反省像历史分期、特殊时代之类的基本范畴,认识到它们并不仅仅是阻止材料的便捷方法,也不仅仅是通向现代性的目的论大道,而是为了隐匿断顿与压抑的修辞战略,因为这是主导叙述结构所需要的。”
鉴于线性历史在时间上的困顿和对历史主体是变动的、相对的、复杂的网络关系的理解,杜赞奇提出了关于复线历史时间的思考:“出路何在?我们是否需要将时间过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类?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流动的时间分层?”“确实,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依赖于我们要如何构想历史的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地认识到历史塑造个人认同和排除多元文化主义的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怎样才能用历史――它不仅仅是人类用来对照自身的一面镜子――扩展人类对自我的了解。历史作为过去的时间,不同于人的死亡或物种的绝迹,正如谚语所说‘你就是历史’。这是对一个时代孕育的多种可能性的探寻,寻找其中的发生、压制、紧张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时代的主导趋势是如何建构,这种建构不一定是通过强迫手段,也可以通过对其他发展可能的道德化和标准化来完成,这样我们就将获得一个承认其自生权力模式的分期图式。”杜赞奇在这里对时间的思考主要有:时间的分期是建立在人们对历史作用认识的基础上的;在线性历史中由于服从于强势的分期原则就造成了对其他历史的压制;而复线历史就是要在时间的分类和分层上进一步多元化,从而有助于揭示历史。
 购物车(0)
购物车(0)